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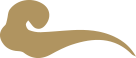
老子认为,一个人为了服从天地之道而修身,首先要收敛感官系统。我们刚刚讲过的第十章“天门开阖,能为雌乎?”就是以发问的方式主张,应付外界的感官系统,要柔静、低调、省俭。现在他要专门来讲这个问题了,仍然是以“天门”的几个要素,即视觉、听觉、味觉作为起点话题。
请看原文——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
在这里,老子用了峻厉的决断之语,让人读了一惊,然后感到痛快。我在《〈老子〉今译》的小序中曾经指出,有些研究者把这些句子的峻厉程度降低了,变成了平稳而庸常的判断,那就离开了老子的语言魅力。
因此,我不主张把“五色令人目盲”翻译成“五颜六色让人目眩”,把“五音令人耳聋”翻译成“声音太杂让人听不清”,而是希望大家牢记老子原有的句式和语势。因此,我的翻译也就不拉着老人家后退了——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伤。
驰骋打猎令人心狂。
难得之货令人邪想。
因此,圣人只求安饱而不求声色,取舍得当。
锐利的哲人总是会指出某种错误会导致的危机,诚实的向导总会指出迷途的前方是悬崖。看似极而言之,其实是省略了推演过程而直示最坏结果,让人惊醒。固然,五颜六色的极度缤纷不会立即让人目盲,但是,这种状态的持续一定会让人们的视觉敏感渐渐麻木、疲顿。时间一长,不再对色彩有什么敏感,成了在美学意义上的“睁眼瞎”。这种“睁眼瞎”,就是老子所说的“目盲”。同样的道理,大轰大嗡的群体噪声和锣鼓喧闹,也会让人们丧失精妙的音乐欣赏能力,成了“另类聋子”。
可见,即使早在老子的时代,人们已经在视听感官上折腾得非常过分,逼得老子只能动用厉言疾句。但是,由于视听感官人人都有又很难把守,所以老子的劝告在民间基本不起作用。我曾经记述过自己在法国巴黎的一段经历,那儿有一位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与我聊天,他反复为精雅的中国文化常常被涂上大红大绿、大金大银的色彩而深表遗憾。他的证据,是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色彩泛滥,而且他也到过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不少地方。他问:如此聪明的中国人难道不知道,这种艳俗的外表会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形象?
由于他把事情说大了,我也不得不回答: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一位思想家就提出过“五色令人目盲”的哲理,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关色彩的哲学判断。而且,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实例跟随,那就是,横贯漫长历史的最高艺术形态书法,基本上只以一色完成,而且是最单纯的黑色。
话虽这么说,我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位法国学者的批评并没有错。大概从清代开始,中华民族的集体审美等级,从皇家到民间,都出现了滑坡的现象。自然美、单纯美、简约美渐渐被相反的形态所替代。直到现代,为了特定目的所张罗的所谓“色彩的盛宴”、“音响的盛典”,实在是伤害了人们的视听感官系统。如果大家习惯了,那实在会让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老子深深长叹。
这一章中的“五味令人口爽”,会使现代读者迷惑,因为在一般口语中的“爽”是指畅快。但在这里,爽的含义是丧失和败坏。“口爽”的含义是味觉败坏,我在翻译时为了与原句对应,用了“口伤”。
另一点,结语所言“圣人为腹不为目”,初一听有点低下,我翻译成“圣人只求安饱而不求声色”,大致回到了老子的原意。也有的研究者在“腹”和“目”上做起了更深的文章,认为“腹”是指一种真实的内在需要,而“目”是指自我的外向张望。林语堂以英文写《老子的智慧》,为了让外国人易于理解,就有类似的解释。
这样引申也未尝不可,但我又觉得老子未必在这两个字中有此种埋伏。如果有,他一定会明白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