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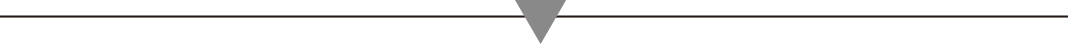
我们可能通过判断别人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情感是否一致,来判断它们是否合宜,这需要考虑以下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激起这些情感的客观对象与我们自己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第二,激起这些情感的客观对象与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有特殊关系。
客观对象与我们自己或者当事人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情况。只要对方的情感与我们自己的情感完全一致,我们就认为他品位高雅,鉴赏力高超。比如说,平原的秀美,山峰的巍峨,建筑物的装饰,图画的意境,文章的结构,第三方的行为,各种数量和数字的比例,宇宙展现出来的千姿百态,以及构成宇宙这一宏大机器的各种玄奥部件,等等。科学以及审美方面的一般性题材,就是我们和同伴认为与我们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特殊关系的那些客观对象。对于这些客观对象,我们观察的视角基本相同。而且,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在感情和情感方面与客观对象达到最完美的一致,从而对它们表示同情;也没有必要对激发同情心的环境变化加以设想。尽管如此,这些客观对象经常会带给我们不同程度的感受,这是因为我们在面对复杂的客观对象时,我们各自的生活经历和习惯不同,我们关注的落脚点会有区别,关注的重点会落在该对象的各个不同部位上;这些客观对象还会给不同的人带来大不相同的感受,这是因为我们感官意识的敏感度各不相同。
面对这类客观对象,很显然,我们同伴的情感和我们的情感很容易达成一致;而且我们可能从没发现哪个人的情感会与我们的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认同这种情感,然而我们似乎也不必因此而赞扬和佩服那个人。但是,如果他们的情绪不仅与我们的情绪一致,还能引领和指导我们的情绪;如果他在形成自己的情绪的过程中似乎注意到了很多我们忽略的细节,而且会随着这些客观对象的不同而对自己的情绪进行相应的调整;那么我们不仅会赞同他们,而且会觉得他们的敏锐和悟性非同寻常、出人意表,真是令人极为惊讶、诧异不已,从而认为他真是令人钦佩万分,值得高度赞扬。因为令人感到惊异,这种赞许得到进一步提升,所产生的情感可以被叫作钦佩。要表达钦佩之情,赞美就是最为自然的方式了。标致的美人远胜丑陋的畸形儿,二乘以二等于四,做出这类判断当然会获得世人赞同,但肯定不会赢得世人的钦佩。品位高雅之士具有高度的敏锐性和精确的洞察力,方能明察秋毫,方能辨别美丑之间细微的差异;资深的数学家具备了综合理解力和超高精准度,才能轻而易举地解答错综复杂令人困惑的比例问题;科学和审美领域的领军人物,方能引领和疏导我们的情绪。这些杰出人士才华横溢、不同凡响,实在是令人赞叹不已,诧异万分,他们激发我们的崇敬之情,自然值得我们高度赞美;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们才会对所谓明智睿见大加赞美。
有人觉得,起初是因为这些才能具备实用性,才赢得我们的称赞;毫无疑问,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开始关注其实用性,并赋予其一种新的价值。然而,我们最初赞同别人的观点,并非首先想到它有用,而是因为它恰当正确、判断精准,符合真理,符合实情;显而易见,我们认为别人的观点明智,是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和我们的观点一致,而不可能因为别的原因。同理,我们认同别人的鉴赏力,也不是因为它有用,而是因为它精准恰当,完全符合客观事实。觉得这些才能有用,完全是事后的想法,并非起初就赢得我们称赞的原因。
在客观对象以某种特殊方式影响我们或当事人的情况下,要想保持上述那种和谐一致就非常困难了,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又极为重要。对于落在我身上的不幸或伤害,我的同伴自然不会采用和我相同的观点来看待它们。这种不幸或伤害对我产生的影响要大很多。我们并非站在与鉴赏一幅画、一首诗或一种哲学体系时相同的立场来看待它们。因此我们就容易受到极其不同的影响。但是,对于与我和同伴都无关紧要的一般客观对象,如果我和同伴持有不一致的情感,我多半不太计较。但是对于落在我身上的不幸或伤害这类与我关系直接的事情,如果我的同伴持有的情感与我的不一致,我就不那么容易接受了。虽然看不起我赞赏的那幅画、那首诗,甚或那个哲学体系,但是我们为此而发生争执的危险却微乎其微。我们双方都不会对此太在意,所有这些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无关紧要。所以,我们的观点也许相反,我们的情感依然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但是,涉及那些对你或我都能产生特殊影响的客观对象时,则另当别论;理性上的判断,情感上的爱好,这些方面我们可以存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可以不去计较;我心情好的话,我们还可以就这些话题探讨一番,说不定我还觉得趣味盎然。但是,如果你对我遭受的不幸,既不表示同情,也不分担令我愁苦不堪的悲痛;对我受到的伤害,既不义愤填膺,也不分担我因此而产生的怨恨;那么我们就绝不可能就这些话题再行探讨。我们甚至无法相互容忍,进而可能老死不相往来。你对我的狂热和激情困惑不解,而我则对你的反应迟钝和冷漠寡情深感恼怒。
在所有这类情况下,旁观者与当事人之间还是可能存在某些一致的感情,不过旁观者首先尽量换位思考,从每一个细节处深切感受令当事人苦恼的每一种细微情况。他必须全盘接受同伴的相关情况,力求不折不扣地重现他的同情赖以产生的那种变化了的处境。
然而,即便做了这样的努力之后,旁观者的情感仍然不易达到受难者所感受的激烈程度。虽然人类天生具有同情心,却根本无法想象当事人遭受不幸时自然激发的情感究竟会强烈到何种程度。而且那种激发旁观者产生同情心的想象也只是暂时的。他们大脑里会频繁地、下意识地提醒自己:自己是安全的,自己并不是真的蒙受了不幸。虽然这样的想法不至于造成旁观者想象的感受与受难者的感受有质的区别,但是却会造成程度方面的严重不同。当事人对此当然十分敏感,同时还期待能够获得更加充分的同情。他渴望得到的那种宽慰,唯有在旁观者与他的情感完全一致时才能提供。看到旁观者内心的情绪在各方面都与自己的内心情绪相符,受难者内心那剧烈而又令人不快的情感才能得到安抚和平息。但是,他只有把自己的情感降到旁观者能够接受的程度才有希望得到这种安慰。也许我可以这样说,他必须抑制自己本能的尖锐语气,降低语调,以便和周围的人保持和谐一致的情绪。的确,旁观者和受难者的感受总会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对于悲伤的同情与悲伤本身从来不会完全相同。因为旁观者会隐隐觉得:令自己产生同情之心的处境变化只不过是出于想象。这不仅会降低同情感的程度,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同情感的性质,甚至使它与所同情的悲伤迥然不同。但是很显然,这两种情感相互之间可以保持某种一致,足以促进社会和谐。虽然它们绝不会完全协调一致,但是它们可以和谐一致,这正是人们所缺乏、所需求的。
人类的天性会促使这种一致的情感的产生,天性总是教导人们换位思考,让旁观者去设身处地考虑当事人的处境,也会让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去设想旁观者的处境。正如旁观者不断地设想当事人的处境,由此想象后者所感受到的相似情绪那样,当事人也不断地将自己置身于旁观者的处境,因此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旁观者的那份冷静,觉得旁观者也会如此看待他的命运。旁观者会经常考虑:如果自己就是实际受难者会有什么感觉?同样,受难者也会经常设想:如果自己就是旁观者之一,眼看自己的遭遇发生在别人身上,又会作何感受?旁观者出于同情之心,或多或少会以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同样,当事人出于同情心,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以旁观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处境,尤其是旁观者就在现场而且自己的举动正处于旁观者的观察之下时,情况更是如此;而且,如果做了如此设想,他的情绪就会有很大程度的减弱。所以,在面对旁观者时,他会设想旁观者实际上已经被他感动,而且会以公正的、毫无偏见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处境,那么他最初感受到的那种强烈的情绪必然大幅降低。
因此,不管当事人的心情多么混乱和激动,朋友的陪伴总会使他恢复几分安宁和镇静。一同朋友见面,我们的心情就会稍稍平息和安静。同情的效果是瞬间起作用的,所以我们会立即想到他即将观察我们的处境,那我们也会开始以相同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处境。我们并不期望从泛泛之交那里得到的同情会比从朋友处获得的同情更多;我们不可能把只会对朋友公开的所有细节,一股脑地向泛泛之交倾诉。因此,我们在朋友面前会更加平静,而且会尽量整理自己的头绪,以便把朋友愿意考虑的有关我们的情况向他做个简要说明。我们更不会期望从一群陌生人那里得到更多的同情,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们会显得更加镇静,以便将自己的情绪控制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应有的程度。这种镇静并非装出来的样子,因为如若我们能全面掌控自己的情绪,则仅仅一个熟人在场也比一个朋友在场更能令自己平静下来;一群陌生人在场也比一个熟人在场更能令自己平静下来。
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如果情绪失去控制,与人交往和谈话是帮助我们恢复平静的灵丹妙药;同样,交往和谈话也是心情平稳和情绪愉悦的最佳保护伞,这对于自我满足和自娱自乐来说不可或缺。隐退和喜欢深思之人,常常闷在家中纠结于悲伤的往事或烦心事,就算他们比别人更仁慈、更宽容,而且具有更为高尚的荣誉感,却很少能拥有普通世人常有的平静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