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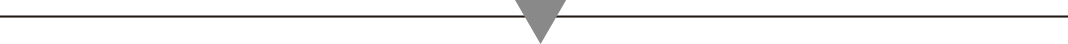
但是,无论人们的行为和意图对受其影响的人(请允许我这样说)是有益还是有害,尚需进一步细察;如果行为人施与恩惠,但是动机不纯,而且我们也不了解影响他行为的情感,那么我们几乎就不会体谅受惠者的感激之情;或者,如果他的动机似乎并无任何不当,但是相反,我们会不可避免地完全理解影响其行为的那种情感,我们就无法体谅受害者的怨恨之情。在前一种情况下,似乎不该心怀感激之情;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满怀怨恨则是不恰当的。前一种行为似乎并没有什么值得感激的功劳,后一种行为似乎也没有什么应该遭受惩罚的罪过。
首先,我认为,只要我们不了解行为人的感情,只要影响其行为的动机不纯,我们就不太可能同情受惠者对其行为带来的好处所表示的感激之情;出于最微不足道的动机却将最大的恩惠施与他人,似乎并不需要给予什么对等的报酬,比如说,仅仅因为某人的名字和姓氏恰好与施恩者的名字和姓氏相同,就将一大笔财产赠予他,这种愚蠢的慷慨行为,似乎只应得到微小的报答。我们蔑视行为人的愚蠢行为,以致我们完全无法认同受惠者的感激之情,感觉施恩者似乎不值得感激。一旦我们设身处地站在感激者的角度,我们感觉对这样一个施恩者无法怀有多大的敬意,因此我们很可能会消除对他的尊重,因为恭顺和尊敬应该给予更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只要他总是以仁慈的态度对待比他软弱的朋友,我们就会赞同他对一位比较可敬的施恩者少给予一些关注和尊敬。那些毫无节制地在他们的宠臣身上滥施财富、权力和荣誉的君主,很少会有人真的对他们本人满怀爱戴和敬意。大不列颠的詹姆斯一世性情温和,但挥霍无度,似乎没有人亲近他;这位君主,尽管他乐善好施、与人无害,但似乎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赢得爱戴者来追随他。但他的儿子查理一世,虽然比较节俭却智慧卓越,尽管平常的态度冷淡而严肃,但英格兰所有的绅士和贵族都愿意为他的事业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富。
其次,我认为,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是出于我们完全体谅与赞同的动机和情感,那么无论落到受害者身上的伤害有多大,我们都不会对他的怨恨之情表示同情。当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如果我们支持其中一人,并且完全体谅他的怨恨之情,我们就不可能体谅另一人的怨恨之心。我们赞同那个人的动机,就会同情他,并因此把他看作是正确的一方,但我们对他的同情只能使我们对另一方显得更加冷酷无情,而且必然会认为他们是错的一方。因此,无论后者可能遭受什么痛苦,只要它不超过我们希望他遭受的痛苦限度,换句话说,只要它不超过我们出于同情的义愤而促使我们强加于他的痛苦,它就既不可能使我们不快,也不可能使我们恼怒。当一个惨无人道的杀人犯被送上断头台时,虽然我们对他的不幸有些同情,但是如果他竟荒唐到对他的检察官或法官表示出任何愤恨之情的话,我们对他的怨恨绝不会产生同理之心。对如此邪恶的罪犯,检察官和法官出于义愤,自然而然会倾向于给他最致命和最具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他们的这种感情倾向,我们却不可能感到不满;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些被罪犯所加害的受害者,就不可能对罪犯对检察官和法官的怨恨之心产生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