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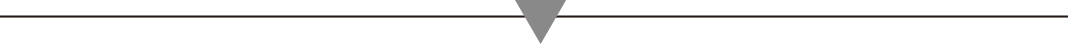
对于那些因身处某种特定环境或因欲望而产生的各种情感,表达得非常强烈就显得不得体,因为同伴的身体并没有感受到相同的处境或欲望,不可能对这些情感表示理解和同情。例如,在很多场合,表现出强烈的食欲不仅是自然流露,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讲却很不得体;暴饮暴食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失态。然而,即便如此,人们对强烈的食欲仍会抱有一定程度的体谅之情。看到同伴食欲大开,能够尽饱口福,岂非乐事一桩;此时如果流露出厌恶之色,则令对方气恼了。健康之人有其习以为常的身体需求,使得其饮食习惯有规律,如果说得粗俗些,就是说他的胃口和食欲可能与一些人一致,但却与另一些人不一致。当读到被困日记或航海日志上有关极度饥饿的描述时,我们会很容易对此类痛苦深表同情。我们想象自己置身于受难者相同的处境,就很容易理解受难者当时备受折磨,是多么的痛苦忧惧、惊恐不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也可以感受到这些心情,因而加以同情。不过,当我们读到这些有关饥饿的描写时并不会真的感到饥饿,因此如果说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的饥饿能够感同身受,则并不恰当。
这样的情况也可以用来解释情欲这种情感。情欲是造物主借以将两性得以结合的一种情感,也是人类天性中最为炽热的情感。但是,在任何场合都强烈地表达情欲则有失体统,哪怕是两个相爱的人,即使世俗和宗教的法律都允许其纵情相爱,亦不可如此。不过,对于这种情感,我们似乎也能够给予一定程度的体谅。像对待一个男人那样去与一个女士交谈,那是不得体的:与女性相处,我们应表现得更为令人轻松愉悦,更为诙谐有趣,对她们呵护有加。如果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表现得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从某种程度上讲,会使他显得极其可恶,甚至是男人都会讨厌这样的家伙。
这就是我们对身体需求所产生的各种欲望都抱有的反感之情:觉得任何强烈表达这些欲望的行为,都是令人恶心、令人不快的。根据一些古代哲学家的见解,这些原始欲望是野兽也有的,算不上人类特有的高贵的天性和品质,因而表达这种欲望实在有损人类的尊严。但是,还有许多我们和野兽共有的其他情感,诸如愤恨之情,天然的感情,甚至包括感激之情,却并不因此而显得令人难受。我们看到别人表现出肉体的欲望都特别反感,真正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对引起其欲望的对象产生同感。甚至感受到那些欲望的人,一旦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就可能丧失对激发其欲望的对象的冲动,甚至开始厌恶它。他茫茫然想搞清楚一瞬间之前使他兴奋莫名的那种魅力,却发现自己也像别人一样,对自己刚刚的情感表现都无法理解了。我们吃过饭后,就会吩咐撤掉餐具。同样,对待那些激发我们肉体最炽热最旺盛的欲望的客观对象,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的方式。
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为节制的美德,存在于对这些肉体欲望的控制之中。把这些欲望约束在健康和财富所限定的范围内,是审慎的职责。但是,将它们控制在优雅、得体、体贴和谦逊所要求的限度之内,则是节制发挥的作用。
正是由于同样的理由,肉体的疼痛无论多么难以忍受,大喊大叫总是显得既缺乏男子气概且有失体面。然而,即使是肉体的疼痛,依然会引起深刻的同情。如前所述,当我看到有人想要猛击别人的腿或手臂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蜷缩自己的腿或手臂,当这一击真的落下时,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感同身受,也会像挨打者那样受到伤害。可是,我所受到的伤害无疑是极其轻微的。正因如此,如果那个人大喊大叫的话,我无法体谅他,甚至会看不起他。因肉体的需求而产生的情感大抵如此:它们要么根本无法激起同情,要么激起的同情有限,与受难者所感受到的剧烈程度不成比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那些因想象而产生的感情则应另当别论。我的身体可能受到我同伴身上发生的变化的影响,不过只是微乎其微;但是我的想象力却很容易受到对方的影响,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我的想象力很容易使我设身处地地设想我所熟悉的人们形形色色的想象。正因如此,与身体所遭受的哪怕是最大的伤害相比,失恋或者壮志未酬容易引发更多的同情。而这些感受完全出自想象。一个倾家荡产之人,如果身体健康无恙,就不会感到肉体上有何不妥。他所感受的痛苦只是源于想象,他通过想象感受到即将面临的种种惨境:尊严的丧失、朋友的唾弃、敌人的蔑视、寄人篱下、贫困潦倒和痛苦凄惨等;我们因此会对他产生更为强烈的同情,因为与我们的肉体因对方的肉体上的不幸而可能受到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想象也许更容易因对方的想象而受到影响。
失去一条腿与失去一个情人相比,通常会被认为是一种更为真切的灾难。但是,一出悲剧如果以前一种损失作为灾难性的结局,则会显得十分荒唐;而后一种不幸,无论它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却能打造许多精彩的悲剧。
疼痛,比任何东西都更容易被人遗忘。疼痛一旦消失,痛苦也立马随之而去,即使再回想起当时的痛苦,也不会觉得有任何不快。于是,我们连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此前产生的焦虑痛苦。但是,一个朋友不经意说出的一句话,却会令我们久久不能释怀,由此产生的苦恼绝不会因为这句话说完了而消失。最先令我们心烦的并不是我们感觉到的客体本身,而是我们想象出来的那个概念。正因为令人烦恼的是一种概念,除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忘,或在某种程度上受其他事情牵扯而冲淡,一想到它就会一直令我们心烦意乱。
疼痛,除非伴随危险,否则根本无法引发强烈的同情心。虽然我们不是同情受难者遭受的痛苦,却同情他因此而产生的恐惧。然而,恐惧只是一种源于想象的情感,这种想象变化无常,能够加剧我们的焦虑,这并非我们现在真正体验到了痛苦,而是对我们此后可能遭受的苦难的一种担忧。痛风或牙疼,虽然疼得钻心,人们却不会对其抱有多少同情;有些更加危险的疾病,虽然病人没有什么疼痛,却容易引起人们最为深切的关心。
有的人一看到外科手术就会头晕恶心;撕扯皮肉引发的肉体疼痛似乎会在他们心中引发最强烈的同情心。疼痛,有的是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有的是源于身体内部失调;我们对这两种疼痛加以想象时,外部原因造成的痛苦给我们带来的印象更加生动鲜明。我无法因为邻居犯痛风或结石病而形成有关他痛苦的概念;但是他如果因为剖腹手术、受伤或者骨折而遭受痛苦,我却能极其清晰地感受到。然而,这类客观原因之所以能对我们产生如此强烈的冲击,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它们抱有新奇感。如果一个人曾目睹十多次剖腹或截肢手术,以后再见到此类手术时,就会不当一回事,甚至麻木不仁了。我们即使读过或看过的悲剧不止五百部,我们对它们的感受,也不至于麻木到如此彻底的程度。
古希腊的一些悲剧,企图通过表现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来激发人们的怜悯之心。由于极度痛苦,菲罗克忒忒斯大喊大叫并且昏厥过去;希波吕托斯和赫拉克勒斯出场之时,均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其痛苦似乎连赫拉克勒斯这么刚毅的大力神都难以承受。然而,在所有这些戏剧中,令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疼痛,而是其他一些情节。令我们深受感动的不是菲罗克忒忒斯那只疼痛的脚,而是他那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始终弥漫于那部魅力无穷的悲剧之中,弥漫于那片浪漫的荒野之上,令人想象连绵,回味无穷。赫拉克勒斯和希波吕托斯的痛苦之所以打动人心,是因为我们预见到死亡是其必然的宿命。如果那些英雄能够复活,我们就会认为大力描述他们的痛苦实在是荒唐至极。悲剧如果只是以描述肉体的极度痛苦为主题,那还算什么悲剧!然而,再也没有比这更加激烈的疼痛了。凭借表现肉体的痛苦来引发同情,这样的企图可以说是严重破坏了希腊戏剧所建立的规则。
由于我们对肉体遭受的痛苦很少表现出同情之心,所以人们认为忍受痛苦之时应该表现出坚忍和克制这种合宜性。如果一个人备受折磨仍然毫不软弱,咬紧牙关,决不呻吟,坚忍不屈,没有丝毫令我们无法体谅的情感表现,我们会对这样的人产生由衷的钦佩。他的坚忍不拔与我们对痛苦表现出来的无动于衷毫无二致。我们钦佩并完全赞同他为此目的所做的高尚的努力。我们在赞成他的行为之余,发现他居然能做出如此令人高度赞赏的壮举,出于我们对人类天性中共同弱点的深刻体会,我们会对他的行为深表惊奇和诧异。这种高度赞赏与惊奇和诧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们恰如其分地称之为钦佩的情感;显而易见,赞扬就是表达钦佩最自然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