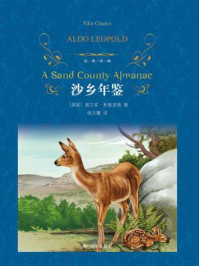我的两位侍女艾伦和伊丽莎白·泰勒妮女士陪我站在窗前,等候与我成婚仅八个半月的丈夫的死讯。她们抓着我的肩膀把我从窗边拉走,好像我还是个孩子,好像我不应该见到事情的真相。掌管伦敦塔的中尉约翰·布里奇斯站在门边,面容坚毅,试着不去感受任何情绪。
我挣脱了她们:“让我看,我对死亡毫不畏惧。”我想让他们知道,就算自己身处被死亡阴影遮蔽的幽谷里,我也毫不畏惧。
虽然有上帝支持我,但当板车从我窗下经过,又从塔山隆隆地回来时,我依然被吓得不轻。我知道他是被斩首的,可我从未想过他的尸体会比我记忆中的他少了整整一个头的长度。沾满血污的尸体边有一个篮子,随着板车的颠簸,他的头颅就在篮子里打滚。可怜的家伙,这场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屠夫推着死去动物的残肢,它们不再是美丽的野兽,而是被人去皮剖肚后的肉块。他是唯一与我同床共枕过的男人,曾经也试图胁迫和控制我。可如今他倒在板车上,身首异处,像被扯下了几章书页的禁书。没了脑袋的他看起来怪异至极。那些人把他英俊的头颅放进篮子里,把他的尸体抛在染血的稻草秆上,这种恐怖的场面让我始料未及。我一直觉得死亡应该如同阳光中的河滩般壮丽,而不是像被屠宰的野兽一样,任由自己熟悉之人的尸体慢慢变硬,被抛在一辆肮脏的板车上。
“吉尔福德。”我轻声说,仿佛在提醒自己他真的死去了,而不是什么伶人的把戏。
刽子手身着一身黑色的长袍,头上罩着黑色的兜帽,这让他的脑袋看起来高得异常。他步履沉重地跟在板车后面。那车驶向教堂,刽子手站在绿塔新建的断头台边,斧子插在地上,低着头,双手抱胸。我猛然间意识到,他在那里并非因为他是吉尔福德送葬队伍中的一员,而是为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他下一个要斩首的人是我。尽管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还是震惊得难以自持。我的行刑之日到了。不论这一切是如何不公,如何不合逻辑,如何自相矛盾,我的存在仍会被抹消,我也终将身首异处。
我停下了笔,不再往约翰·布里奇斯的祈祷书中写东西。之前写的那么多内容在这一刻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只是单独的个体,文字却能永不消逝。我想到:
在起初已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
 。我想自己理解了这句话:肉身易朽,但文字永存。虽然吉尔福德沾满血的尸体把我吓到了,但我依然相信这一点。我的导师和良师益友凯瑟琳·帕尔也笃信不疑。她面对死亡毫无惧色,我也将如此。
。我想自己理解了这句话:肉身易朽,但文字永存。虽然吉尔福德沾满血的尸体把我吓到了,但我依然相信这一点。我的导师和良师益友凯瑟琳·帕尔也笃信不疑。她面对死亡毫无惧色,我也将如此。
“敬爱的中尉先生,既然你祈望一个单纯的女人在如此无价的书页上写下祷词,” 我这么起了个头。
我用了“祈望”,因为它本身就带着庄重和肃穆之感。一段写完后,我又补了一段,随后署名,费克纳姆兄弟看着我,平和地说:“时辰已到,该停笔了。”
我已经准备好,也必须准备好。我已无须再写,因为我已写下了和费克纳姆讨论内容的概要,还有自己想和女王、父亲以及凯瑟琳说的话。在结尾,我写下了自己对狱卒的《圣经》的告别之情。这份活计业已完工,我便身着黑色长裙,把自己的祈祷书打开,捧在手上。
“我准备好了。”我说,记下了心中那可怜的局促不安,这感觉让我忍不住想大声喊道:“等等!就等一会儿!我还要做件别的事!就等一下,一下就行,再给我一秒……”
约翰·费克纳姆在前面带路,我抓着自己的英文祈祷书,想试着在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下去,穿过小花园的门,慢慢走向绿塔刑场的那段路上读一读书上的内容。当然了,不论是走下楼梯还是走在花园小径上我都不能真的看清书上的字,没人能做到。不过这样就能让所有人看到,我在走向刑场的时候手里捧着托马斯·克兰默的《公祷书》。凯瑟琳·帕尔王后写下了这些祷词,并将它们从拉丁语翻译成了英语。我现在手捧这本能证明我正确性的书,这是我们的成果,我已经准备为它而死,拿着它而死。
我身后的侍女们不断地抽泣,好像连气都喘不上来,我心中希望别人都能看到我并没有像她们那样哭。我期盼每个人都能看见我边走边捧着书祈祷的样子,我的样子如此虔诚,让人一眼就瞧出我肯定能获得来生。我们走上断头台的阶梯,在平台上集合。来看我殉教的人很少,这让我很是惊讶,便对他们朗声开口。
我担心自己的声音会发颤,幸好没有。我祈求上帝的怜悯,随后对众人说自己会蒙受上帝的慈悲而得救,而非依靠牧师的祷告,或教堂里的弥撒。我请求众人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为我祈祷,因为我死后将直接进入天堂。“这世上没有炼狱”,我想加上这句话,不过大家都明白我的想法。
我用英语朗读了《求主垂怜诗》
 ,上帝是懂英语的,认为只能向他用拉丁语祈祷纯粹是迷信。约翰·费克纳姆也跟着我一起读,只不过他用的是拉丁语。我今天才发现这种语言听起来是如此优美,如此悦耳,与我读出的英语和谐相配。我们的声音回荡在河面上方腾起的潮湿薄雾中,与海鸥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如钟磬和鸣。直到现在我才记起,自己原来只有十六岁,却再也没法见到那条河了。我也不敢相信自己会与布拉德盖特的山丘诀别,与凯瑟琳和我在林中走过的小路诀别,与我那匹在田野上的老马诀别,与熊苑中的老熊诀别。祈祷的时间久得难以置信,时间似乎也失去了概念,突如其来的结束令我惊讶,我得把自己的手套、手帕以及祈祷书都交出去。侍女们需要把我最后的王家仪容准备好,她们脱下了我的滚边兜帽,取下了我的衣领。时间突然间便如白驹过隙,我想说的话还未出口,想用双眼真切确认的事物还未来得及细细端详。我肯定自己还有遗言要说,还有往事要回想,但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上帝是懂英语的,认为只能向他用拉丁语祈祷纯粹是迷信。约翰·费克纳姆也跟着我一起读,只不过他用的是拉丁语。我今天才发现这种语言听起来是如此优美,如此悦耳,与我读出的英语和谐相配。我们的声音回荡在河面上方腾起的潮湿薄雾中,与海鸥的叫声交织在一起,如钟磬和鸣。直到现在我才记起,自己原来只有十六岁,却再也没法见到那条河了。我也不敢相信自己会与布拉德盖特的山丘诀别,与凯瑟琳和我在林中走过的小路诀别,与我那匹在田野上的老马诀别,与熊苑中的老熊诀别。祈祷的时间久得难以置信,时间似乎也失去了概念,突如其来的结束令我惊讶,我得把自己的手套、手帕以及祈祷书都交出去。侍女们需要把我最后的王家仪容准备好,她们脱下了我的滚边兜帽,取下了我的衣领。时间突然间便如白驹过隙,我想说的话还未出口,想用双眼真切确认的事物还未来得及细细端详。我肯定自己还有遗言要说,还有往事要回想,但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我跪了下来,耳中还能听见费克纳姆平稳的朗读声。他们用蒙眼的绑带包住了我的双眼,最后映入我眼帘的事物是那些海鸥,我本该看着云朵,本该保证自己最后一眼看见的是天空。我在阳光下被蒙住眼睛,所见只是茫然一片,我突然明白了恐惧的滋味。
“我要做什么?这是哪儿?”我惊慌失措地尖叫道,有人抓着我的手,让我摸到了那块坚实的方形木桩,我知道自己命数已定。这的的确确是有形的世界,这是我触碰过最真实的东西。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死前所摸到的最后一件物体,便紧紧抓着它,指尖甚至可以感觉到木头的纹理。我把头低下来靠在上面,才发觉蒙眼的绑带已经被泪水打湿,它变得又潮湿又温热,紧紧贴在我闭着的双眼上。我肯定一直在哭吧,但至少没人能看见,不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我都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