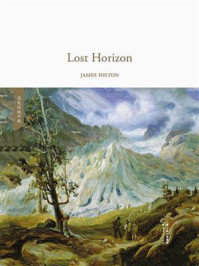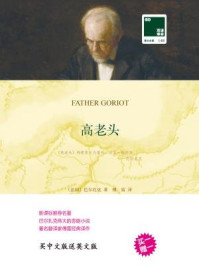我是个天生的冒失鬼,从小就总是吃亏。上小学时,曾从二楼教室一跃而下,摔伤了腰,痛了一个星期。也许有人问,何苦如此胡来,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理由:我从新建好的二层楼上探头下望,一个同学开玩笑,说我再逞能也不敢从上边跳下来,还大声起哄笑我是胆小鬼,仅此而已。事后工友背我回家,父亲瞪起眼睛,说:哪有你这种家伙,从二楼跳还能摔坏腰!好,我说,下次跳个不摔腰的给你看。
我从一个亲戚手里得了把进口小刀,把光闪闪的刀刃冲着太阳晃给同学看,其中一个说:亮倒是亮,只怕切不了东西。笑话!我应声答道,没有不能切的!对方随即提出:那就切你的手指好了。手指?这还不容易,你看着!我对着大拇指斜切下去。幸好刀小,指骨又硬,大拇指至今还连在手上,只是那伤疤此生此世算消不掉了。
往院子东边走二十步,尽头偏南有一小块菜园,正中长着一棵栗树,结着对我来说简直是命根子的栗子。栗子熟时,我一早爬起来就跑出厨房后门,拾来那些掉在地上的,带到学校受用。菜园西端连着一家叫“山城屋”的当铺,当铺老板有个儿子叫勘太郎,十三四岁。不用说,这家伙是个胆小鬼。人虽胆小,却偏要跳过方格篱笆,到这边偷栗子。一天傍晚,我躲在折叠门后,终于逮住了勘太郎。这家伙见无路可逃,恶狠狠猛扑过来。他比我大两岁,胆子虽小,可力气蛮大。将那颗肥肥大大的脑袋,一头顶住我的胸口,步步加劲。不巧那脑袋一偏,竟溜进了我的袖口,害得我手在里边派不上用场,乱挥乱抡起来。勘太郎在袖口中的脑袋,便随之左右摇摆。最后忍耐不住,在袖筒里一口咬住我的手腕,痛得我一股劲把他推到篱笆墙根,一个扫堂腿,绊他个跟头。“山城屋”的院子比菜园低有六尺,那勘太郎把方格篱笆压倒半边,“扑通”一声,大头朝下栽到他自家领地去了。这当儿,我的一只夹袄袖也不翼而飞,手一下子自如起来。当晚,母亲到“山城屋”道歉,顺便把袖子带了回来。
此外我还干了不少坏事。一次,领着木匠兼公和鱼店的阿角,把茂作家的胡萝卜苗圃毁坏了。当时芽尚未出齐,铺着一层草。我们三人在上边整整摔了大半天跤,芽苗给踩得一塌糊涂。还有一次把古川家菜地里的井填上了,结果闯了大祸。按通常做法,本应拿根粗大的孟宗竹,掏空竹节,深深插入井内,把水引出,浇灌附近的菜地。但当时我不晓得个中奥妙,只管将石头、棍棒投入井内,塞得满满的,见水再也出不来了,才回家吃饭。刚端起饭碗,古川满脸涨红,叫骂而来。记得好像赔钱了事。
父亲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母亲一味偏向哥哥。哥哥脸皮白得出奇,喜欢模仿舞台上旦角的动作。父亲一瞥见我,张口就骂我一辈子也出息不了。母亲也说我胡作非为,日后不叫人省心。事实也真是这样:我没出息,也没叫人省心,只差没进班房。
母亲病死前两三天,我在厨房翻跟头,给锅台磕了肋骨,痛不可耐。母亲大为恼火,说再也不想见我这种人,我便跑到亲戚家去了。不想竟传来了母亲的死讯。我没料到母亲死得这么快,早知病成这样,也该老实一点才是。我一路后悔,赶回家里。刚一进屋,那混账哥哥劈头一句,说我不知孝顺,母亲是因为我才早死的。我又气又恨,上去给他一记耳光,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
母亲死后,我和父兄三人度日。父亲整天无所事事,见面就说我不行,直成了口头禅。我至今也弄不明白我到底什么不行,天底下竟有这样的老子。哥哥声称要当什么企业家,抓住英语不放。他原本就是女人脾性,加上狡猾,两人关系很僵,差不多十天就吵一次。一次下棋时,他卑鄙地设一伏子,堵住我老将的去路,见我发窘,便笑嘻嘻地冷嘲热讽。我一气之下,将手中的“车”朝他眉间掷去,打得他眉间开裂出血。他向父亲告了我一状,父亲便宣称要同我断绝父子关系。
于是,我只好横下心,静等被扫地出门。这时候,一个在我家干了十年的叫阿清的女佣,哭着替我向父亲求情,父亲才好歹息怒。可我并没因此惧怕父亲,反而对阿清的举动大为不忍。听说这女佣本来出身名门,明治维新时家境衰微,才落到为人做佣的地步,此时已经是老婆婆了。不知什么因缘,这阿婆十分疼爱我。母亲死前三天放弃了我,父亲一年到头看不上我,街坊邻居指脊梁骨叫我混世魔王,然而这阿婆却对我百般疼爱。我自知自己压根儿不是讨人喜欢的人,因此对遭人白眼早已不放在心上,而对阿婆这番亲热,反倒莫名其妙。没人时,阿婆几次在厨房里夸我为人正直,品性难得。但我不晓得阿婆话里的含义。心想,若是品性难得,其他人也该对我和善一点才是。每当阿婆提起这话,我差不多总是顶她:我不要听这个!于是阿婆愈发笑容满面地盯着我的脸,迭声说道:这才是,这就叫作品性难得。那神情,似乎在炫耀我是她制造出来的一件产品,叫人心里有些不悦。
母亲去世后,阿清婆对我更加疼爱起来。我每每以小孩之心揣度受此厚爱的原因,但不得其解,心中暗想:讨厌,多事!又觉得她可怜。但阿婆仍然喜爱我,不时用自己的零用钱买豆沙糕、梅花煎饼给我。寒冷的夜晚,悄悄买好荞面,做成面汤,神不知鬼不觉地放在我枕边。有时还买来砂锅面条。不光吃的,还有袜子,有铅笔,有练习簿,后来有一次竟借给我三元钱。我并没向她开口,而她拿钱走进房间:“没零花钱不方便吧?”说着把钱塞进我手里。我当然摇头不要,她非叫我拿着不可,我便收了下来。其实我高兴得要死,把三元钱塞进小钱包,揣到怀里,转身去上厕所,不料一下子掉到便池里去了。无奈,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跟阿婆实话实说。阿婆立即找来一根竹竿,说给我捞上来。不大工夫,井台传来“哗哗”的水声。跑去一看,见她正用竹竿尖挑着钱包,用水冲洗。之后打开钱包,里面的三张整元纸币已经变成茶青色,图案模糊不清了。阿婆用火烤干,递给我说:“这回行了吧?”我嗅了嗅:“呀,臭。”“那么再给我,给你换来。”不知她去哪里搞了什么名堂,换成了三枚银币。我忘记这三元钱干什么用了,口称马上还而没还。如今即使想还以十倍,也无法做到了。
阿婆给我东西,每次都趁哥哥不在的时候。我说:“这哪好,不要!”我最不喜欢瞒着别人独占便宜。虽说同哥哥合不来,也不想瞒着他拿阿婆的糕点和彩色铅笔。一次我问阿清婆:“为什么只给我一个人,不给哥哥呢?”阿婆一本正经地说:“不用管哥哥,他有爸爸给。”这不公平。父亲虽然固执,但并非那种偏心眼的人。可在阿婆眼里却不是这样,全是她太疼爱我的缘故。尽管她过去是有身份的,但毕竟没受过教育,叫人毫无办法。偏心无药可医。这还不算,她还认定我准能出人头地,而断言哥哥只是脸皮白,成不了大器。遇上这样的阿婆,真令人头疼。在她眼里,自己中意的人一定升官发财,而讨厌的人保准一无所成。本来那时我并没有当官做事的打算,但经不住阿婆再三鼓吹,便也自命不凡起来。现在想来,实在好笑。一次我问阿婆,自己能当上什么,不料她也好像没认真想过,只是说,肯定出入有车坐,住宅有威风的大门。
从这以后,阿婆便打算等我自立门户后随我住在一起,几次求我务必收留她才好。我也模糊觉得自己可能会拥有住宅,便随口答应下来。不想这阿婆想象力强得很,什么你喜欢哪里,曲街
 如何啦,什么院子里要挂个秋千、洋房一间足够啦,只管自作主张,一厢情愿。那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要什么房子,每次都回答阿婆:“管它洋房日本房,我才不稀罕呢?”结果她又夸我不贪财,心地干净。反正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少不了夸奖一通。
如何啦,什么院子里要挂个秋千、洋房一间足够啦,只管自作主张,一厢情愿。那时我根本就没想到要什么房子,每次都回答阿婆:“管它洋房日本房,我才不稀罕呢?”结果她又夸我不贪财,心地干净。反正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少不了夸奖一通。
母亲死后的五六年时间里,我就这样过着。被父亲训,和哥哥吵,吃阿婆的糕点,时受夸奖,别无他望,心满意足。我想别的小孩大概也同样如此。只是阿婆每遇什么事,就絮絮叨叨说我可怜、不幸,于是我又以为自己是真的可怜、不幸。此外没有任何恼人的事,只是对父亲不给零用钱有些不快。
母亲去世后第六年的正月,父亲也中风死了。那年四月我从一所私立中学毕业,三月哥哥走出商业学校。他在一家公司的九州分公司找到了工作,要去上任;而我还得留在东京继续求学。哥哥提出要卖掉房子,处理财产,然后动身去九州。我说怎么都行。反正我不想端哥哥的饭碗,即使他要照顾我,也还是要吵架,免不了给他吹毛求疵。况且若真的受他这种应付了事的保护,就不得不向他低三下四。我都想好了,就是当小工,给别人送牛奶,也要自己挣口饭吃。哥哥找来旧家具店老板,把世代传下来的杂乱家具、古董,三捆两捆,换了几文钱。房子经人周旋,卖给了金满家。这大概得了不少钱,详情我一无所知。我在一个月前就搬到神田区小川街寄宿,以待决定去向。阿婆见自己住了十几年的房子一朝转卖于人,甚感可惜,但不是她自己的,自是奈何不得。她在我面前絮絮不止,说要是我再长大一点,把这份家业继承下来该有多好。实际上,倘若我大一点便可继承的话,那么现在也不是不可以,而阿婆全然不晓,以为我只要年龄再大些,便可接收哥哥的家业。
和哥哥就这样分开了。难办的是阿清婆的去处。哥哥自然无法带她前去,而且她也根本不想跟哥哥远下九州。我又整天闷在四个半榻榻米大的寄宿间,而且连这么个住处到时候也必须退掉,实在一筹莫展。我问阿清婆,是否想在哪里当保姆?阿清婆想了想,定下决心说,在我成家以前,只好打扰外甥了。她这位外甥在法院当书记员,生活尚好,这以前几次劝阿婆去住,阿婆都没有答应,说自己虽是当佣人,但多年来已经住习惯了。而眼下,阿婆大概觉得,与其到素不相识的大户人家小心服侍主人,不如在外甥身边好些。这么拿定主意后,阿婆嘱咐我快点找房子,快点讨老婆,她好去帮忙。看来,同作为至亲的外甥相比,她似乎更喜欢我这个外人。
哥哥动身去九州的前两天,来到我的住处,递给我六百元钱,说,是当资本经商,还是作学费读书,尽管随便,只是以后不再管我。就哥哥来说,这一举动已相当慷慨了。我本来觉得即使不靠那六百元钱也混得下去,但我高兴他这种从未有过的淡泊态度,道谢接过。随后他又掏出五十元钱,叫我顺便交给阿清婆,我满口答应。两天后,在新桥车站同哥哥分手,此后再未见过。
我躺在床上,考虑这六百元钱的用法。做买卖吧,麻麻烦烦的,我又不是那块料,况且这六百元钱也做不成像样的买卖。退一步说,即使做得成,我现在这两下子,都无法理直气壮地在别人面前说自己受过教育,还不是只有吃亏赔本的份。算了,买卖不成,就用来当学费读书好了!六百元钱分成三份,一年花二百,可以学三年。三年时间里若拼命用功,总可以学点东西,于是我就开始考虑哪所学校合适。然而学问这东西,我生来就一样也不喜欢,特别是语言学啦,文学啦,一看就头晕。还有什么新体诗,二十行中连一行都看不懂。既然哪样都不喜欢,那么学哪样都是一回事。幸好路过物理学校门前时,见有一张招生广告,真是缘分!我领了份招生简章,很快办好了入学手续。如今想来,这也是我那天生的鲁莽性格造成的失策。
在校三年,我也差不多同别人一样用功,但由于素质差,名次总是倒数来得快。三年一过,我也莫名其妙地混得个毕业,自己都觉得滑稽,可又不便说三道四,乖乖跨出校门。
毕业后第八天,校长叫我前去,我当是什么事,到那里一看,原来是四国地区一所中学需要数学教师,月薪四十元,问我是否愿去。说实话,我虽然也吃了三年寒窗苦,但压根儿就没想过当什么教师,去什么乡下。当然,也没考虑过教师以外的任何职业。因此,当校长问到我头上,便当场回答愿去,这也无非是我那天生的鲁莽性格作祟的结果。
既然答应了,就必须赴任。蛰居斗室的三年时间里,我没听到有人说我一句坏话,没吵过一次架,是我一生中颇为悠然的时代。可是,现在这四个半榻榻米大的小房间也得退掉了。东京以外的地方,在校时只跟同学去过镰仓,算是唯一一次出远门。这次则远非镰仓可比,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从地图上看,那地方位于海滨,仅有针尖那么大,反正不会是什么好去处,不知是何城镇,居住何人。不知道也没关系,无须担心,尽管前去,只是有些麻烦。
房子卖掉后我也常跑去阿清婆那里。阿婆的外甥实在是个好人,每次去时,只要他在家,无不设法款待。阿婆当着我面,东拉西扯地把我吹给外甥听。甚至无中生有,说我从学校毕业出来,马上就要在街买一所邸宅,走马上任。她只顾自以为是地喋喋不休,羞得我在旁边满脸通红,而且不止一次两次。还不时把我小时尿床的事和盘托出,叫人哭笑不得。我不知她外甥听后作何感想,只觉得这阿婆到底是旧式妇女,似乎把她自己同我的关系,看成封建时代的主从关系,以为我既然是她的主人,也无疑是外甥的主人,亏她外甥为人和善。
工作最后讲定、动身赴任的前三天,我去看阿清婆。她感冒了,躺在朝北一个三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见我进来,忙爬起身,没等坐稳就问:“小少爷,什么时候买房子啊?”她以为只要一毕业,钱就会自动从口袋里冒出来。既然把我看得如此神通广大,却依旧管我叫“小少爷”,可见愈发傻气了。我简单告诉她,眼下买不成房子,要到乡下去。她显得非常失望,不停地拨弄额角零乱的花白头发。我见她着实可怜,安慰说,去是去,但很快就回来,来年暑假肯定回来。她还是一副茫然的神情。我问她喜欢什么,好买礼物回来。她说想吃越后粽子。何谓越后粽子,我听都没听过,首先方向上就南辕北辙,便说:“我去的那乡下好像没有粽子。”“那,你去的是哪边?”“西边。”“是箱根前边,还是后边?”费了我好多唇舌。启程那天,阿婆一早赶来,这个那个,照料一番。把来时路上在杂货店买的牙刷、牙签、毛巾塞到帆布提包里,我说不要,她不肯答应。我们雇辆黄包车,赶到车站,登上月台。我钻进车厢后,她定定看着我的脸,喃喃道:“也许再也见不到了,可要好好注意身子。”眼里噙满了泪水。我没哭,但眼泪差一点就淌出来了。火车开出好一段路后,我以为她回去了,从车厢探出头,往回一看,她依然站在那里,不知怎么,显得异常瘦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