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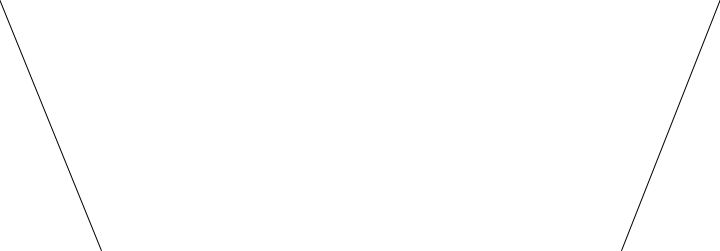
自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在向亨利·基辛格寻求建议,世界各地的许多CEO和政治领袖也在这样做。他在外交政策、治国之道和世界秩序方面的见解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然而,作为一个谈判家,他留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全部记录不知为何没有得到系统的分析。

在研究了基辛格的谈判经历和著作,以及就这个主题对他所做的长时间采访之后,我们在他的谈判方法中找到了惊人的复杂性和一致性。这使得我们想在本书中实现两个目标。
首先,我们会回顾涉及中国、苏联、越南、中东和南部非洲的多起重要谈判。在这些谈判中,作为尼克松和福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基辛格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这种回顾,我们试图描述“谈判家基辛格”的特点。然后,我们会将支持他的谈判方法的一系列特征具体化。
其次,我们将探讨前瞻性:虽然基辛格的有效谈判概念主要来自几十年前的外交活动,但我们会试着对他的谈判方法进行评估,看看这些方法对当今的外交官以及在商界、金融界、公共政策制定领域和法律界从事谈判的人士能否起到指导作用,确定其价值和局限性在哪里。在本书中,我们力求提炼出具有持久价值并且广泛适用的谈判原则和技巧。以下三点表明了读者可以从我们对谈判家基辛格的研究中学到的东西:
第一,“战略”这个术语经常被提及,仔细研究一下基辛格的方法,可以搞清楚战略性谈判在实践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可以成为如此有力的工具。
第二,基辛格的谈判总是表现为一种来回往复的过程,他时而“缩小焦距”,从更广泛的战略视角来观察全局;时而“放大焦距”,对某个特定的对手展现出高度的说服力。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顶级的谈判家在应对具有挑战性的交涉时,已经在战略和人际关系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缩放焦距”的方法。 [1] 对基辛格的交涉手法这一独特方面的揭示,已经使我们的许多学生和执行项目的参与者——他们通常正处于成功的职业生涯中——在他们的公共和私人谈判中取得了更大的成效。
第三,对亨利·基辛格在众多谈判中的行为进行剖析,可以发现他在“谈判桌外”所采取的广泛行动往往是与他在“谈判桌前”所使用的那些为人熟知的战术相配合的,这会显著改善谈判的结果。更简单地说,观察一个特别有成效的谈判者的工作,可以把我们从认为谈判主要是一种说服性人际交往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在面对强大的障碍时,要让对方接受你的提议,需要比通常情况更广泛、更稳健的谈判理念。
当我们写完这本书时,亨利·基辛格已经95岁了,但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全球战略家和活跃的外交事务评论员,他仍然受到全世界的瞩目。除了时常撰写文章,他近年来出版的著作《论中国》(2011年)和《世界秩序》(2014年)都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并且他还在写一本有关政治家才能的新书。
 他也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例如,在基辛格离开政坛大约39年之后,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中,他的历史功过引发了一场“激烈对抗”。希拉里·克林顿对他的赞扬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他的谴责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引起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被冠以《亨利·基辛格:圣人还是贱民?》(“Henry Kissinger: Sage or Pariah?”)的标题刊登出来。
他也仍然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例如,在基辛格离开政坛大约39年之后,在201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首场辩论中,他的历史功过引发了一场“激烈对抗”。希拉里·克林顿对他的赞扬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他的谴责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中引起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被冠以《亨利·基辛格:圣人还是贱民?》(“Henry Kissinger: Sage or Pariah?”)的标题刊登出来。
 在这场公开冲突发生前一年,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基辛格写的一部两卷本传记的第一卷出版了,这部传记对基辛格主要持赞同态度;与之相对,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Grandin)写的一本新书则对基辛格的履历做了极为尖刻的评价。
[2]
在这场公开冲突发生前一年,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为基辛格写的一部两卷本传记的第一卷出版了,这部传记对基辛格主要持赞同态度;与之相对,历史学家格雷格·格兰丁(GregGrandin)写的一本新书则对基辛格的履历做了极为尖刻的评价。
[2]
从20世纪70年代起到现在,无数前辈为基辛格写书撰文,但这些书籍、相关文章和媒体报道(不论是赞赏的、中立的还是批判的)普遍没有突出基辛格的谈判方法,虽说他的谈判经历往往被当成了重要的背景。相反,这些论述倾向于强调基辛格对国际关系所做的复杂分析,以及他作为一名传统的现实主义治国之道的践行者所留下的广泛记录。 [3]
在基辛格参与的事件中,他的谈判主要是被放在特定事件的背景中来论述的,而没有跨各种情况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基辛格自己的作品充满了对谈判艺术和谈判科学的观察,不过也主要是针对特定的例子。在基辛格的工作生涯中,这个重要但相对被忽视的方面应该得到明确的关注和分析,而且应该被视作他身为一个谈判家具有非凡力量的一种体现。
虽然基辛格几乎被普遍认为是卓有成效的,但他的经历也招来了许多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在人权、秘密行动、不民主的保密以及对独裁政权的支持等方面,批评尤其集中在他在柬埔寨、老挝、北越、阿根廷、智利、东巴基斯坦(即现在的孟加拉国)和东帝汶采取的行动上。因此,我们对他的谈判方法的分析,可以马上转化为对他在职期间的行为的评价。然而,判断他是圣人还是罪人(实际上,这就是在重新挑起陈腐的争论)并不是本书的目的。此外,对这样一项任务而言,我们是没有什么比较优势的(不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他的批评者和捍卫者之间的各种激烈争论)。 [4]
我们的目的既不是评判一个人,也不是直书历史。相反,我们想要对基辛格在一些世界上极具挑战性的谈判中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进行探究和评估,尽可能多地从他那里了解这个重要的主题。如果成功了,那么我们将会从最高层次的谈判艺术和谈判科学中提炼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见解。
基辛格的生平和职业生涯,一般人都很熟悉。
 他于1923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觉察到纳粹即将发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们一家人在1938年移民到美国,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暴力事件。1943年,基辛格归化为美国公民,1943—1946年在欧洲战区服役于美国陆军。在哈佛完成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后,他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师,并升任终身教授。1954—1969年,他活跃于哈佛大学的政府学系和国际事务中心。
他于1923年出生在德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由于觉察到纳粹即将发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们一家人在1938年移民到美国,几个月之后就发生了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暴力事件。1943年,基辛格归化为美国公民,1943—1946年在欧洲战区服役于美国陆军。在哈佛完成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后,他被任命为学校的教师,并升任终身教授。1954—1969年,他活跃于哈佛大学的政府学系和国际事务中心。
基辛格曾担任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的外交政策顾问,洛克菲勒曾三度寻求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是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对手。尽管基辛格支持洛克菲勒,但尼克松还是选择了这位哈佛教授作为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担任这一职务的同时,基辛格又于1973年9月22日宣誓成为美国第56任国务卿。在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下台之后,基辛格继续在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的政府中担任国务卿,直到1977年1月20 日。
虽然在写作本书时(2018年)基辛格的公众形象仍然很好,但要回想起他当年在国内外声望的隆盛,还是很难的。在任职期间,他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的次数不少于15次,1972年还和理查德·尼克松一起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
[5]
1973年,他和黎德寿(Le Duc Tho)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们两人完成了为结束越南战争而进行的谈判(不过基辛格后来试图退还这一奖项)。
 他还在1977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他还在1977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这是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从国务卿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基辛格创办了一家全球咨询公司,并在一些著名的公共及私人董事会和委员会任职。
 到了90多岁的高龄,他依然是一位多产的评论员和分析家,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到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习近平,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仍在咨询他的意见。
到了90多岁的高龄,他依然是一位多产的评论员和分析家,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到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到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习近平,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仍在咨询他的意见。
除了拥有良好的公众形象,基辛格还是17本书以及无数论文、演讲词和评论文章的作者。
 他早期的两本书,《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和《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都出版于1957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学者,这两本书被广泛认为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它们的政策含义上,都是开创性的。
他早期的两本书,《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和《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都出版于1957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学者,这两本书被广泛认为不论是在概念上还是在它们的政策含义上,都是开创性的。
 他在离开政坛后写的三卷本回忆录特别有名,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他的职业生涯。1980年,回忆录的第一卷《白宫岁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Award)。
他在离开政坛后写的三卷本回忆录特别有名,这部回忆录记述了他的职业生涯。1980年,回忆录的第一卷《白宫岁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Award)。

他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大外交》,对国际关系和外交提供了一种全景式的观察,并特别关注了20世纪和西方世界。这本书阐明了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取向,论证了权力平衡和“国家利益”概念的重要性。在这本书里,基辛格批评了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外交政策,同时坚持认为在国外的行动必须至少符合一个国家的道德观。
[6]
《论中国》探讨了中国的历史和基辛格长期与这个国家进行谈判的经验,特别是与其领导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所进行的那些谈判,并对21世纪的美中关系做了远期评估。
 他最近的一本书《世界秩序》从更加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对一些传统主题进行了论述,包括战争、和平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
[7]
他最近的一本书《世界秩序》从更加全球性和历史性的视角,对一些传统主题进行了论述,包括战争、和平和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
[7]
鉴于基辛格的经验和广泛的著作,研究他的外交政策思想和治国方略具有显著的意义。但是,究竟为什么应该对谈判家基辛格进行分析?他参与的主要谈判到底展示或实现了什么,以至于在这么多年之后还值得我们去仔细分析?还有,除了历史趣味性之外,我们能从这些事件中学到什么对今天和未来的谈判有价值的东西?
对这些问题作答,需要回顾一下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以及后来的杰拉尔德·福特)所面对的世界——主要是在1969—1976年期间。为此,我们特意提供了下面的简介,它们不是这一时期全部事件的记录,但它们应该能够帮助读者回忆起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关键挑战,正是这些挑战引出了我们将在后面讨论的那些重要的谈判。
 这些简介只突出了基辛格和他的同事们在每次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成绩的,以及读者从中能获得哪些更广泛的经验,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
这些简介只突出了基辛格和他的同事们在每次谈判中所取得的成绩;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成绩的,以及读者从中能获得哪些更广泛的经验,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探讨。
在1969年被尼克松总统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时,基辛格面临着一个潜在的存在性威胁:几十年来,美国和苏联陷入了一场逐渐升温的、危险的冷战。超过37,000件核武器瞄准了彼此,大部分处于一触即发的警戒状态。正如被分割的柏林一样,欧洲也被分成了东方和西方两个集团,它们分别与两个敌对的军事联盟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系在一起,处于相互僵持的局面中。与此同时,苏联向北越提供了大量的军备,在令人痛苦的越南战争中,这些军备杀死了成千上万的美国人。
在这一险恶的背景下,基辛格利用“缓和”政策为改善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也就是说,他缓和了美国和苏联在广阔阵线上的紧张气氛,并促使这两个超级大国签订了第一份重要的核武器控制协议。
20年来,美国既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与它进行过任何有意义的接触,中国军队曾经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士兵打过仗,后来中国又以军用物资和军事顾问支援北越。正如基辛格所说:“20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总是把中国看成一个令人不安的、混沌的、狂热的、陌生的国度,难以理解,无法动摇。”
 而中国也经常用喷火一般的言辞来证实这种印象。例如,1969年5月,在尼克松执政的头一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篇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文章。
而中国也经常用喷火一般的言辞来证实这种印象。例如,1969年5月,在尼克松执政的头一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一篇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文章。

在尼克松总统的密切配合下,基辛格在1971年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秘密地展开了谈判。虽然此事在当时引起了激烈的争议,尤其是在美国的保守派当中,但它成为美国在1972年向中国敞开大门的关键一步,为美国承认这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并与之不断增进关系铺平了道路。
到1969年,发生在越南的这场血腥的战争已经夺去了大约36,000名美国人的生命,而在战争中死亡的越南人更是远远超过这个数量。这场战争还断送了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总统生涯。整个美国都爆发了校园示威活动和反战抗议活动,有时还引起了暴力冲突,这凸显了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在1968年8月投票时的观点,他们认为派遣军队到越南去是一个错误。
[8]
迫于强大的国内压力,尼克松决心迅速撤出印度支那的美军。他上任时,大约有55万美军在越南,而在1969—1970年,有超过20万美军撤离了越南。1972年,美国在越南的总兵力与其峰值相比,减少了95%,只有不到2.5万人了。
[9]
当基辛格开始与北越谈判时,美军加快了撤退的步伐——北越也明白这一点。在1969年开始的谈判进程中,北越坚持不肯退让的立场是,美国要自行推翻南越政府(它被普遍认为是美国的盟友),并从越南撤军。在谈判期间,美国陆军将军弗农·沃尔特斯(Vernon Walters)看到北越的主要谈判代表黎德寿“站在(巴黎的)别墅台阶顶端,带着胜利的微笑俯视基辛格,(对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和你谈判。我刚刚和(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参议员共度了几个小时,你的反对者会迫使你给我我想要的东西’”。
 与此同时,南越领导人坚决反对任何有关美军回国的协议。
与此同时,南越领导人坚决反对任何有关美军回国的协议。
是一系列因素的综合导致了越南战争的结束,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和理查德·尼克松精心策划的外交行动,我们在分析中将其称为“多边谈判战役”。在巴黎,基辛格和他的北越对手黎德寿直接交锋。他还通过谈判来改善美国与苏联、中国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抑制这两大共产主义巨头,以削弱它们对北越的支持。这些会谈也涉及西德和西欧。1973年达成的《巴黎和平协定》意味着实行停火,释放战俘,美军撤离,而南越政府将被保留到举行新的大选时。[当然,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辞职以及美国不愿和(或)无力执行,北越很快就撕毁了这一协议,南越于1975年4月落入北越之手。]
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在犹太人一年中最神圣的一天(此时也正是穆斯林的斋月)对以色列发动了出乎意料的突然袭击,这次袭击显示出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脆弱。阿拉伯军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其中包括埃及军队跨越苏伊士运河。以基辛格为国务卿的美国采取了紧急行动,重新恢复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力量,使以色列恢复了军事平衡并进行了反击。那个时候,苏联在中东享有非常稳固的地位,重要的阿拉伯国家都是它的盟友,其中就包括埃及和叙利亚。苏联也向它的盟友提供了援助,威胁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向开罗和大马士革进军的话,它就会进行直接干预。这使得危机急剧升级,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呼之欲出。
1973年年底和1974年年初,基辛格大展身手,通过持续的穿梭外交,让埃及和以色列、叙利亚和以色列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脱离军事接触协议。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协议一直到今天还在起作用。基辛格在进行这些谈判时,有意识地削弱了苏联对中东的影响,这一成果基本上被保持了40多年(直到2015年9月,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为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接受苏联援助和古巴军队拥入安哥拉的情况下,南部非洲那些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似乎有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变成冷战的重要前线的危险。鉴于在越南的痛苦经历,美国没有兴趣采取对抗性军事行动,甚至连提供援助都不愿意;国会很快就宣布美国对古巴和苏联的行动所采取的一项秘密回应是不合法的。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在对抗苏联和古巴的行动方面可能很重要的两个国家——罗得西亚和南非,都处于明显得到美国政治支持的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下。在美国,保守派控制的地区尤其支持这两个政权。1965年,罗得西亚非法宣布脱离英国独立。在那之后,英国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说服罗得西亚白人少数政权的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想让他哪怕考虑一下由处于不到30万白人控制下的600万非洲黑人来实行多数统治,却彻底失败了。(例如,罗得西亚宪法规定立法议会由50名欧洲裔成员和16名非洲裔成员组成,只有一半成员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 [10] )
1976年,亨利·基辛格采取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主动行动——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它进行相当详细的分析——他与一系列非洲国家进行了谈判,不论它们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最后,他通过这次行动说服了极为顽固的罗得西亚,使它同意在两年之内接受黑人多数统治的原则。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说服了南非对罗得西亚施加强大的压力,尽管南非实行的也是白人少数统治,对罗得西亚施压无疑会反过来对它自己造成影响。这些谈判的开展明显牵制了古巴和苏联在安哥拉的行动,为罗得西亚最终赢得独立铺平了道路,帮助这一地区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种族战争”;还可以说,也使南非朝着实现黑人多数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回顾这份充实的外交成就记录(缓和政策、军备控制,中国、越南、中东和南部非洲),我们不禁感到好奇,如果对它进行一次更为详细的考察,会揭示出什么:基辛格是怎样准备、设计和执行这些复杂的、举步维艰的谈判的?他的谈判方法中,有哪些方面对于应对今天的谈判挑战——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是有价值的?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只靠谈判本身——就谈判这个词的狭义而言——就能产生这些结果,还有许多互为补充的政策和行动牵涉在内。我们也不认为有任何一个人能对这些结果负完全的责任。其他各方——还有机会——都对结果有明显的影响。
[11]
在考虑到这些应该注意的地方后,我们探索基辛格的行动和著作,以寻求能帮助我们克服艰难险阻,达成理想协议的见解。有了这些见解,我们打算进行更好的分析,开发更有效的药方,以帮助每个谈判者取得更好的结果。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国际关系背景中的双边或多边“谈判”描述为外交和外交政策的交易子集。既然被归入这一类别,那么,在通常以不同方式看待事物并且有利益冲突的各方中周旋,一名谈判者在心里必须至少有一个目标协议。
在此预先声明一点:对“谈判”一词的普遍用法和大部分关于谈判的当代学术研究往往都只狭隘地关注谈判进程中纯粹的“会谈部分”,或是主要发生在“谈判桌前”的人际关系变化。这通常包括面对面的交流、移情、魄力、有说服力的论证、肢体语言、处理跨文化和个性差异问题、讨价还价的模式等等。 [12] 然而,基辛格的谈判战略和战术还包含在“谈判桌外”采取行动,以提高获得更好的结果的可能性,这与更为广泛的谈判研究的传统是一致的。 [13] 举例来说,这样的行动可能是采取措施将某方纳入或赶出谈判进程、建立或打破联盟,以及强化或削弱陷入僵局的后果。
把这一更广泛的谈判概念与“治国之道”或“外交”明确区分开来的尝试,只会变成毫无意义的语义学练习。这些密切相关的活动之间即使有界限,也是模糊不清的。因此,我们根据基辛格的著作和实践,始终坚持采用一种宽泛的“谈判”观点,把谈判桌前和谈判桌外的行动都包括进来,而采取这些行动的目的是让谈判者能够以称心如意的条件达成协议。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基辛格参与的谈判只是一个更大的关于治国之道的故事中的一段重要插曲;但在本书中,我们把视角颠倒过来,重点关注他参与的谈判,对其进行宽泛的解读,而把更大的故事当作背景。
我们的追求就是阐明、学习基辛格的谈判方法,并评估其实用性。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会根据需要对上面做过简单介绍的事件进行叙述,利用这样的叙述来补充背景,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做详细的案例分析。
然而,为了传达一种亨利·基辛格作为谈判家的更为细腻的感觉,我们将以探究1976年他在福特政府中的任期行将结束之际,在南部非洲所进行的谈判作为下一部分的开始。虽说我们在这里简要提过的这些复杂的谈判在当时也得到了许多赞美,但是在今天,它们的知名度远比他与苏联、中国、北越或中东的各大势力所做的交涉低得多。基辛格在南部非洲开展外交,起初是受到了苏联和古巴进驻安哥拉的刺激,但他的目标是在后来成为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地区结束根深蒂固的白人少数统治——这一行动对共和党政府来说可能是出乎意料的。
在南部非洲所进行的这些谈判本身确实很有趣,但我们是想利用它们来引出和说明基辛格的战略和战术所体现的一些规定性见解。在接下来的三章中,我们将用包含了对基辛格谈判方法的更广泛观察的文本框(用双横线来标示)来跳出叙述。在分析完南部非洲的会谈之后,我们会在单独的章节中发展和概括这些见解,并从基辛格的一系列其他交涉中找出例证来说明它们。最后,我们会对这些概括性见解进行评估,看看它们对当前发生在外交和其他领域的谈判有多少实用价值。
到本书结尾之时,读者将见识到一系列极其复杂且往往非常有趣的谈判。了解基辛格是如何破解这些难题的,能为我们提供在极具挑战性的情况下显著改善谈判结果的见解。这些见解包括:
·在谈判中,“战略”实际上意味着什么。
·如何现实地评估一个协议是否有达成的可能。
·“广角镜头”和改变游戏的行动是如何在谈判桌外为达成交易创造空间,并使得在谈判桌前获得有利结果成为可能的。
·确定行动顺序、建立联盟以及应对那些阻碍交易的人是有效地进行多方谈判的关键。
·真正地理解、看懂你的对手并与他建立融洽关系的重要性。
·强势和移情是如何有效地结合起来的。
·怎样在保持战略视角的同时,随形势的变化采取机会主义式的行动。
·为何成功的必要因素往往是坚持不懈,而不是出色的洞察力。
·不论有效与否,都要提出建议,表达让步,建立信用,利用“建设性模棱两可”;在各方之间进行穿梭,而不是把他们聚在一起来讨论;根据情况选择公开会谈或秘密会谈。
在本书中,读者将会看到基辛格这一实践的价值:不断缩小焦距关注战略和放大焦距关注人际关系。然而,支撑我们对谈判的诸多方面进行探索的是一个朴素的真理:不论达成协议的技术多么有创造性,人们最终能否取得成功,都取决于他们关于世界的基本假设的准确性、对有关各方真正利益的判断,以及对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了解。对谈判进程的洞察力若是服务于有缺陷的目标或是脱离对真实情况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多大的价值。然而,通过研究像基辛格这样的伟大的谈判家,我们可以学会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更有效地进行商业、法律和政府谈判。
[1] 虽然最初我们认为是我们创造了“缩放焦距”的术语,但其他人也有权声明自己创造了它。特别是我们哈佛商学院的同事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她用这些术语构建了一篇重要论文的框架,参见她的《放大焦距,缩小焦距》(“Zoom In, Zoom Out”),《哈佛商业评论》(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第89卷第3期(2011年),第112—116页。也是在2011年,吉姆·柯林斯(Jim Collins)和莫滕·汉森(Morten Hansen)在探讨战略时用到了这个短语。参见吉姆·柯林斯和莫滕·T.汉森,《做出选择,变得伟大》( Great by Choice ),纽约:哈珀商业,2011年,第113—121页。我们可能还遗漏了其他许多在不同语境中使用过这个短语的人。
[2] 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 Kissinger: Volume 1, 1923-1968: The Idealist ),纽约:企鹅图书,2015年;格雷格·格兰丁,《基辛格的影子:美国最具争议的政治家及其遗产》( Kissinger's Shadow: The Long Reach of America's Most Controversial Statesman ),纽约:都市图书/亨利·霍尔特公司(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and Company),2015年。
[3] 除了刚才提到的书,还可参考这些传记作品:艾萨克森,《基辛格》;马文·L.卡尔布(Marvin L.Kalb)和伯纳德·卡尔布(Bernard Kalb),《基辛格》( Kissinger ),波士顿:利特尔&布朗(Little, Brown),1974年;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基辛格:1973,关键的一年》( Kissinger: 1973, the Crucial Year ),纽约:西蒙和舒斯特,2009年;罗伯特·达莱克(Robert Dallek),《尼克松与基辛格:权力伙伴》( Nixon and Kissinger: Partners in Power ),纽约:哈珀·柯林斯,2007年。弗格森的《基辛格:理想主义者》一书的导论部分对有关基辛格的著作做了一个有趣而广泛的导读。阿利斯泰尔·霍恩提供了一份强有力的“亨利·基辛格案例”,参考和引用了许多批评者对他的评价,可以作为弗格森的“概览”的补充。参见阿利斯泰尔·霍恩,《亨利·基辛格案例》(“The Case for Henry Kissinger”),《独立报》( Independent ),2009年8月17日,基于他2009年出版的书《基辛格:1973》。基辛格坚定的批评者及其著作包括: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对基辛格的审判》( 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 ),纽约:韦尔索(Verso),2001年;西摩·M.赫什(Seymour M.Hersh),《权力的代价:尼克松执政时期的基辛格》(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 House ),纽约:高峰图书(Summit Books),1983年;威廉·肖克罗斯(William Shawcross),《政治杂耍:基辛格、尼克松与柬埔寨的毁灭》( Sideshow: Kissinger, Nix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 ),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79 年。
[4] 正如前面提到的,著名的贬低者及其著作包括:格兰丁,《基辛格的影子》;赫什,《权力的代价》;希钦斯,《对基辛格的审判》;以及肖克罗斯,《政治杂耍》。在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基辛格》中可以找到许多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章节。近年来,扎克·比彻姆(Zack Beauchamp)等批评者的文章又附和了这些分析,参见扎克·比彻姆,《奥巴马政府今日表彰亨利·基辛格。不应该》(“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Is Honoring Henry Kissinger Today.It Shouldn't Be”),Vox网站,2016年5月9日,http://www.vox.com/2016/5/9/11640562/kissingerpentagon-award。基辛格的赞赏者(虽然没有谁完全不批评他)及其著作包括:尼尔·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霍恩,《亨利·基辛格案例》;罗伯特·D.卡普兰(Robert D.Kaplan),《基辛格、梅特涅和现实主义》(“Kissinger, Metternich, and Realism”),《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1999年6月;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为亨利·基辛格辩护》(“In Defense of Henry Kissinger”),《评论》( Commentary ),1992年12月1日。奥巴马总统的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亨利·基辛格……简直就像写了一本关于外交的书,这位国务卿的功绩和专长教给我们许多现代外交词语,尤其是‘穿梭外交’和‘战略耐心’;他对历史的特殊洞察,对他离开之后的每一位国务卿来说都是无价之宝。”参见约翰·克里,《在美国外交中心奠基仪式上的讲话》(“Remarks at the U.S.Diplomacy Center Groundbreaking Ceremony”),新闻稿,2014年9月3日,https://2009-2017.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4/09/231318.htm。
[5] 弗格森,《基辛格:理想主义者》,第2页。1973年,基辛格在盖洛普的“最受人尊敬的人”调查中名列第一。在国务卿中,他单独出现在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电视访谈节目中的次数就有大约40次[更不用说他在《豪门恩怨》( Dynasty )和《科尔伯特报告》( The Colbert Report )里的客串了,他还以卡通人物的形象出现在《辛普森一家》( The Simpsons and Family Guy )中]。
[6] 《大外交》,纽约:西蒙和舒斯特,1994年;尤西·M.汉希梅基(Jussi M.Hanhimäki),《有缺陷的建筑师:亨利·基辛格与美国外交政策》( The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6页。
[7] 特别是,这本新书探讨了“世界秩序”的不同概念的演变、相互作用和可能的未来。其中包括所谓的威斯特发里亚模式——起源于欧洲,由名义上平等的主权国家构成;伊斯兰教关于世界共同体的一种广阔的理念,或者说是穆斯林公社( ummah );以及一种深深地浸润在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口中那据称是普遍的理想中的美国秩序,这一秩序既支配着世界,又受到世界许多地区的攻讦。
[8] 亚历克·盖洛普(Alec Gallup)(2006),《盖洛普民意调查:2005年公众意见》( The Gallup Poll: Public Opinion 2005 ),罗曼&利特菲尔德(Rowman & Littlefield),第315—318页。
[9] 人口调查局(Bureau of the Census),《越南冲突——美国驻越南军队及其伤亡人数:1961年至1972年》(“Vietnam Conflict—U.S.Military Forces in Vietnam and Casualties Incurred: 1961 to 1972”),表590,《美国统计摘要,1977年》(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 ),华盛顿特区:美国商务部,1980年,第369页,https://www.gilderlehrman.org/history-by-era/seventies/resources/vietnam-war-military-statistics。
[10] 细节请参见A.B.穆蒂蒂(A.B.Mutiti),《罗得西亚及其四项歧视性宪法》(“Rhodesia and Her Four Discriminatory Constitutions”),《非洲存在》( Présence Africaine ),新系列,第90号(1974年第二季度),第261—275页。
[11] 我们的叙述之下潜藏着一个长期存在的方法论问题,国际关系学者以及其他观察和分析谈判的社会科学家经常提起这个问题:个别谈判者的行为对最终结果是否有——或者说,能否造成——重大影响?最终结果难道不是“结构”或“更大的力量”(制度、经济、文化、历史或其他什么)的产物吗,它们无情地自行运作,以人类为代理不过是一种“副现象”罢了?或者说得更富有诗意一些,最终结果难道不是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吗?对这一困境问题的经典陈述可参见亚历山大·E.文特(Alexander E.Wendt),《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代理—结构问题》(“The Agent-Structure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第41卷第3期(1987年),第335—370页。在我们的分析中,我们回避了这个深层次的问题,简单地采用了这一观点:个别代理者对结果和塑造结构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很显然,既有的结构也会约束和塑造代理者。有关讨论请参见下一条注释;奥迪·克洛茨(Audie Klotz)等,《超越代理—结构争论》(“Moving Beyond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国际研究评论》(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第8卷第2期(2006年),第355 页。
[12] 对各种行动及其心理层面做讨论的例子,可参见利·L.汤普森(Leigh L.Thompson),《谈判者的头脑与心灵》( The Mind and Heart of the Negotiator ),第5版,波士顿:培生,2012年;玛格丽特·安·尼尔(Margaret Ann Neale)和马克斯·H.巴泽曼(Max H.Bazerman),《谈判中的认知与理性》( Cognition and Rationality in Negotiation ),纽约:自由出版社;多伦多,1991年。
[13] 托马斯·C.谢林(Thomas C.Schelling),《冲突的战略》(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剑桥(Cambrid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托马斯·谢林,《军备及其影响》( Arms and Influence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戴维·A.拉克斯(David A.Lax)和詹姆斯·K.塞贝纽斯,《三维谈判:在至关重要的交易中扭转局面》( 3-D Negotiation: Powerful Tools to Change the Game in Your Most Important Deals ),波士顿:哈佛商学院出版社,2006年。关于谈判分析的更多技术基础,包括“谈判桌外”的行动,请参见詹姆斯·K.塞贝纽斯,《谈判算术:增加和减去问题和当事人》(“Negotiation Arithmetic: Adding and Subtracting Issues and Parties”),《国际组织》,第37卷第2期(1983年春季),第281—316页;詹姆斯·K.塞贝纽斯,《国际谈判分析》(“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nalysis”),载于《国际谈判:分析、方法、问题》(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Analysis, Approaches, Issues )第2版,维克托·克列梅纽克(Victor Kremenyuk)主编,圣弗朗西斯科:约塞-巴斯(JosseyBass),2002年,第229—252页。对这类行动的大量解说性案例研究,可参见迈克尔·沃特金斯(Michael Watkins)和苏珊·罗斯格兰特(Susan Rosegrant),《突破国际谈判:伟大的谈判家如何化解世界上最严酷的冷战后冲突》( Breakthrough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How Great Negotiators Transformed the World's Toughest Post-Cold War Conflicts ),圣弗朗西斯科:约塞-巴斯,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