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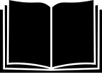

借用我最不热衷的体育项目里的比喻
 ,这本书要做的,是直面科学能遭遇的最广泛议题之一——历史本身的性质——将它一把“擒抱”住。我采取的策略,不是直奔议题核心,而是从外围迂回,将一个精彩纷呈的案例研究的所有细节一一展现。这也是我在一般性写作中一贯采用的策略。细节本身并不能走多远,它最多只能与一首我吟诵不出的诗句放到一起,成就令人倾慕的“自然写作”作品。但是,若从一般性原则的正面进攻,只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冗长的篇幅,或者带上强烈的倾向。自然之美表现在细节之中,启示则蕴含于一般性的原则里。最理想的鉴赏之道,细节和原则皆不可缺。以精心挑选的具体案例阐明激动人心的原则——除了这样,我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
,这本书要做的,是直面科学能遭遇的最广泛议题之一——历史本身的性质——将它一把“擒抱”住。我采取的策略,不是直奔议题核心,而是从外围迂回,将一个精彩纷呈的案例研究的所有细节一一展现。这也是我在一般性写作中一贯采用的策略。细节本身并不能走多远,它最多只能与一首我吟诵不出的诗句放到一起,成就令人倾慕的“自然写作”作品。但是,若从一般性原则的正面进攻,只会不可避免地形成冗长的篇幅,或者带上强烈的倾向。自然之美表现在细节之中,启示则蕴含于一般性的原则里。最理想的鉴赏之道,细节和原则皆不可缺。以精心挑选的具体案例阐明激动人心的原则——除了这样,我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策略。
我的主题有关最重要、最令人珍视的化石产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伯吉斯页岩。围绕着发现它以及诠释它的人的故事,时间跨度已有近 80年。以一个被滥用的词语的字面义形容,这个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查尔斯·都利特·沃尔科特是美国首席古生物学家,美国科学界权力最大的行政管理者。1909 年,就是他发现了这保存极为完好的动物群——最古老的软体构型动物群。但是,几乎是出于他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立场,一种常规的诠释被强加到这些生物之上,新的生命历史观没能形成。正因为如此,那些独一无二的生物不为公众所知(尽管它们潜在的生命历史教育价值远胜过恐龙)。但是,有三位来自英格兰及爱尔兰的古生物学家,在后来开展了 20 年严谨的解剖学特征描述研究。起初,他们丝毫未意识到工作的颠覆性。最终,他们不仅推翻了沃尔科特对这些独特化石的诠释,还挑战了生命历史的传统观点——进步及可预见性。取而代之的,是历史学家提出的偶然性——演化的“行进”过程是由一系列令人极其难以置信的事件构成的。事后回顾,这些事件的发生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可以得到强有力的解释。不过,它们的发生完全不可预测,也不具可重复性。如果能把“生命记录带”倒回伯吉斯页岩早期的日子,自历史的同一起点重新开始一次,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具备类似人类智能的生物难以形成,产生的机会小得几近为零。
不过,与人的付出和被订正的诠释相比,伯吉斯生物本身甚至更加精彩。尤其是对它们的最新合理重构,显露出的,是超然的奇象异景——有长着五只眼和一管前端“长鼻”的欧巴宾海蝎;有骇人的奇虾,它们有长着一圈“牙齿”的大口,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动物;还有解剖学结构与名字般配的怪诞虫。
至于本书标题,它表达了我们对两件物事的叹服——一来是为生物本身的美妙,二来是为随之形成的全新生命观。欧巴宾海蝎和它的同伴们一道,构成一幅来自那个遥远过去的生命群像,奇异而美妙,同时也把历史偶然性的伟大主题注入对这类概念反感的学科之中。《生活多美好》是一部在美国深入人心的电影,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情节,就以该主题为中心。在片中,吉米·史都华(所扮演角色)的守护天使为其重演“生命记录带”,让他体会没有了这个角色之后,他原先周围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重演的结果显示,历史中貌似无足轻重的细节有着令人敬畏的威力。偶然性的概念不受科学待见,但电影和文学总能发现其迷人之处。电影《生活多美好》既是本书核心主题的一个象征,也是我所知的最好阐释——我以本书标题向克拉伦斯·奥德博迪(天使)、乔治·贝利(史都华扮演的角色)、弗兰克·卡普拉(导演)致敬 [1] 。
对伯吉斯页岩生物重新进行诠释并由此形成新观点,有关它们的故事错综复杂,有一大群人的共同参与。但是,站在这个故事舞台中心的,是三位古生物学家。一位是世界级三叶虫专家——来自剑桥大学的哈利·惠廷顿。另两位起初是他的研究生,从那时起,他们就将伯吉斯页岩研究当作自己的事业,成绩非凡。他们是德里克·布里格斯和西蒙·康维·莫里斯。三位古生物学家之所以位于舞台正中,是因为他们完成了有关解剖学描述和分类界定的大部分技术工作。
该以哪种格式来呈现这一工作呢?为此,我在不同的选择之间挣扎过好几个月,但最终认定,只有一种方式能将一切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完备的整体。如果历史对如今秩序形成的影响如此之大,那么,在本书小得多的范畴之内,我也必须对历史的威力抱有敬畏之心。何况,惠廷顿及其同事的工作也构成了一段历史。而在偶然性的范畴里,反映秩序的主要标准形式是——而且必须是——依时序记录的编年史。对伯吉斯页岩生物的重新诠释是一个故事,一个宏大而精彩的故事,有着最高智识价值的故事——在其中,没有人被杀,甚至没有人受伤,连一块皮都没被擦破,但它揭开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除了合理的时间顺序,还有什么其他方式可供我采纳呢?!就像电影《罗生门》里的情形,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事后的陈述各不相同。不过,我们至少可以通过编年来做些准备工作,搭好框架。在这里,我已将这一时间序列视作一出情节丰富的戏剧——我甚至放任自己的这种夸张比喻,将之以五幕剧的形式呈现,作为第三章内的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第一章借用非同寻常的道具——图说,将这个伯吉斯页岩故事要挑战的传统态度(或者说半遮半掩的文化期许)一一摆出。第二章呈现必要的故事知识背景,包括生命的早期历史、化石记录的本质、伯吉斯页岩本身的特有场景。第三章以戏剧的形式,依时序记录这次改变我们对早期生命的观念的伟大修订工作。在该章最后一部分,我尝试将伯吉斯的这段历史放到本故事挑战并修订的进化理论的一般语境中加以讨论。第四章深入查尔斯·都利特·沃尔科特身处的时代和他的精神世界,为的是理解他因何对自己伟大发现的本质和意义的认识错得如此彻底。接着,我将展现一个与传统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看法——历史是偶然性的产物。第五章从两方面入手确立这种历史观。一方面是一般性的论证;另一方面,依时序逐一列举生命历史的主要事件,揭示在发生之始仅做出轻微改动,就会使进化的路径一改再改,转到完全不同但又同等合理的方向——由此将不会产生能写出编年史或解密自身如何自过去“行进”而来的物种。尾声,也就是收场的小节,是伯吉斯呈现出的最后一个惊奇——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好比先知在寸草不生的荒野里的呼喊。但是,这种喜悦之声不会要求将崎岖之路通直,或将坎坷之地展平。因为,真实路径的终点注定有吸引力,身处那坎坷崎岖之途,只会是满心欢喜 [2] 。
我处在常规创作的两极之间。我不是一个记者,或者“科学作家”,不会以公正的局外人自居,去采访其他领域里的人物。我是一名职业古生物学家,跟这出戏里所有的主要参与者是联系紧密的同行,在私下也是朋友。但是,我不具备该研究特需的立体空间思维天赋。尽管如此,惠廷顿、布里格斯、康维·莫里斯的世界,也是我的世界。我了解这个世界蕴含的希望、存在的不足、采用的术语与技术手段,不过,我也能与它的幻想和平共处。如果本书能被读者接受,那么,就说明我把专业的风格和知识,与做出判断所必须保持的距离结合到一起,我的一个梦想——以地质学行内人视角创作一本类似约翰·麦克菲作品的读物 [3] ——就实现了。如果没能被接受,那么,我也不过是加入众多“受害者”的行列,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所有的陈词滥调都能用来自辩,比如说,(读者)众口难调、(我)两头不讨好。〔生活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世界之中,同时又要客观地报道它,常常让我感觉到为难。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发现自己无法解决。我的主人公,名字是(按姓)惠廷顿、布里格斯、康维·莫里斯,还是(按名)哈利、德里克、西蒙?我最终放弃了对称呼的统一,认定两种称呼都是合适的,只是适用环境不同——由我的直觉和感受决定何时采用何种。我还得遵循另一常规,在按时序呈现“伯吉斯之戏”时,依照的时间是各个伯吉斯化石研究成果的出版日期。但是,所有行内人都知道,从手稿的提交到印刷出版,之间的间隔是随机的,可长可短,难以预料。由此,论文出版的顺序与实际工作的先后或许没有什么联系。因此,我请所有的主要参与者检查了我列出的序列。还好,结果让我满意,也让我舒了一口气——在这个案例中,论文出版的时间顺序很好地反映出研究工作的先后。〕
我在每一次撰写所谓“普及读物”时,都极力维护一条个人原则。(“普及”一词的字面义令人向往,但现已被贬损,带有简化或添油加醋的意味,好像这样的读物应该如同轻音乐,读起来无须费神。)我相信——就像伽利略完成他那两部巨著,是以意大利语对话的形式,而不是用拉丁文写就的说教纲要;就像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写出他那高超的文章,不用一条术语;就像达尔文出版他所有的书籍,都是面向大众读者——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一类科学读物,既适合专业人士阅读,也能让感兴趣的非专业人士读懂。尽管科学的概念数量丰富、意义多样,但不必有所妥协,不必经过扭曲的简化,也能以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当然,较之学术出版物,面向一般读者的读物在遣词造句方面必然有所不同,但只限于略去令行外人士感到迷惑的术语和措辞,而概念的深度绝对不可有所不同。我希望本书能使读者获益,不仅仅能用于研究生选修的专题讨论课,如果您去东京出差,不巧途中播放的电影难看,您又忘了带安眠药,本书也可以拿来当作消遣。
当然,“您真诚的”在下的这些期待和私见也需要您有所付出。伯吉斯故事的魅力在于它的细节,与解剖学结构有关。是的,或许您跳过这些内容,仍可以获得大致的启示(天地良心,那启示我会满怀热情地在书中重复足够多的次数),但您千万别这样做——否则,您将永远不能领略“伯吉斯之戏”的瑰丽,也体会不到其引人入胜之处。对于解剖学和分类学这两方面的技术内容,我已尽己所能,使之在尽可能自洽的同时,尽量不显得咄咄逼人。我在正文中加入了插页,作为对这些内容的入门介绍。我将术语的使用频次降到低得不能再低。(幸运的是,我们几乎可以略过专业语汇中所有令人沮丧的术语,只须了解附肢的种类和排列方式,即可抓住节肢动物的要领。)此外,所有关于特征的描述性文字都配有示意图。
我也一度考虑(不过是脑中的恶念在作祟)将所有的描述性文字略去,换上一些伪装得面面俱到的美丽插图,另诉诸权威——拿它当挡箭牌。但是,我不能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在上文中提到的一般性原则,还另有原因——若我略去有关解剖学特征的论证,采用二手信息来源,而非原始专论文献,每一次,都会在真实的美丽之上留下一道亵渎的印记。说起真实之美,一来是因为那些技术性成果是我在专业生涯中所见的最为雅致的一部分,二来是出于伯吉斯动物本身的独特魅力。求人总是显得不体面,但容我恳求一句——请您对那些细节抱有容忍之心,它们不难理解,它们还是进入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要写作这样一本书,最终难免成为一项集体合力的事业。我必须感谢所有人给予的耐心、慷慨、洞见和鼓励。我要感谢哈利·惠廷顿、西蒙·康维·莫里斯,还有德里克·布里格斯,他们容忍我长达数小时的采访、我的追根问底,还为我审读了本书手稿。感谢幽鹤国家公园的斯蒂文·萨迪斯(Steven Suddes)体贴地组织了一次徒步之旅,前往沃尔科特的采石场——没有这次朝圣之旅,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感谢拉斯洛·梅索伊(Laszlo Meszoly)以精湛的技艺为我准备图表。他的这份技艺令我仰慕,也是我近 20年来工作的依靠。感谢莉比·格伦(Libby Glenn),在她的协助下,我得以遍阅藏于华盛顿的海量沃尔科特存档。
我之前发表过的文字从未像本书这样如此依赖插图。不过,对于本书而言,它是必需的。毕竟,灵长目动物精于视觉。尤其是对解剖学结构的展示,图像与文字同等重要。在这项工作一开始,我就决定,本书将采用的大多数示意图,必须是惠廷顿及其同事在原始文献中使用的原图——不仅因为它们在这一类型中出类拔萃,而且,主要是由于我不知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可以表达我对他们工作的无限敬意。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只是扮演一个忠实的历史记录者的角色,而记录的原始信息来源,在我自身行业的历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我也有惯常的无知和偏见,我以为翻拍已出版的图像必定是一个简单的自动过程——随便一照,然后随便冲洗出来。但是,当目睹我的摄影师阿尔·科尔曼(Al Coleman)和我的研究助理大卫·巴克斯(David Backus)的工作之后,我对其他专业的精湛技艺有了很多体会。他们耗费了三个月的时间,使图像的分辨率达到了我在原始文献中都看不到的高水平。我要献上我最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的奉献和建议。
这些图片总共约 100 幅,主要属于两种类型——标本的实物绘图和完整生物个体的复原图。我原本可以去掉实物绘图中特征的指示标签,它们通常标注得十分密集,与文中论证有关的也很少。而且,那些有关的少数,在图题中已有完整的解释。但是,我希望读者看到这些示图在原始信息来源中的样子。顺便说一句,读者应注意,按照科学示图传统重建的绘图,展示出的动物,很少与在寒武纪时期海洋底部可能实际观察到的一致。有两方面的原因,都是为了让更多的结构完全地显现出来。一方面,对一些结构进行了透明处理。另一方面,省略了(通常在身体另一面重复的)一些结构。
既然技术性绘图展示的生物不是其活灵活现的真实形象,我决定,必须另请一位科学艺术家,为本书创作一系列复原图。因为,已出版的标准插图不能让我满意,它们要么不准确,要么缺乏美学质感。幸运的是,德里克·布里格斯向我展示了玛丽安娜·柯林斯绘制的多须虫(图 3.55)。这让我终于见到伯吉斯生物的这样一种形象——它集合了解剖学细节上的严谨与美学上的优雅,能让我想起美国自然博物馆里亨利·费尔费尔德·奥斯本半身像下的铭文——“因为他,骨架才得以活灵活现,远古的庞然大物才回到‘行进’的生物行列中” [4] 。让我十分欣喜的是,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玛丽安娜·柯林斯能为本书特别贡献 20 多幅伯吉斯动物复原图。
这一集体的成果将几代人连到一起。我与比尔·谢维尔及G.伊夫林·哈钦森有过很多交谈。前者曾在 20 世纪 30 年代与帕西·雷蒙德一起(前往伯吉斯页岩)采集,后者在沃尔科特去世后不久,便发表了自己第一篇洞见颇深的伯吉斯化石论文。我对沃尔科特进行了大量研究,了解之深,几乎就像触碰到他本人。之后,我把目标转向当前,与现在所有从事有关工作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交谈。我特别感激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的德斯蒙德·柯林斯。1988年夏季,就在我撰写本书之时,他终于进入沃尔科特最早的采石场。此外,他还在雷蒙德的采石场上方的一处新地点取得最新的发现。他的工作成果在未来将扩充和修订本书一些章节所涉内容——被取代是求之不得的必然结局,这样,科学才不会停滞和消亡。
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沉浸在伯吉斯页岩的世界里,跟来自四面八方的同事和学生一谈起这个问题,便滔滔不绝。他们提出的意见、疑问和告诫,使本书得到了极大的改进。科学欺诈和一般性不良竞争行为是当下的热门话题。这种现象的确很严重,但让我担心的是,它会在学界以外的人士眼中形成一种假象。那些报道太吸引人,以至于每一件平常被认为是正派、光荣的事件,似乎都能让人觉得是心存欺诈,另有所图。事实不是这样,完全不是。悲剧不在于那些行为被视为普遍现象,而是这种不对称产生的后果令人沮丧——偶尔发生的恶性事件让千百种学术常态一文不名,或者将之盖于风头之下。而那些常态从未被记录在案,因为我们将之视作理所当然。古生物学界是一个友善的专业圈子。我不是说我们都喜欢对方,我们之间当然也有很多不同之见。但是,我们互相扶持,避免狭隘。这一伟大传统为本书的完成铺平了道路。本书得益于无数友善的姿态,而我从未记录在案,正因为它们是正派人的——也就是说,谢天谢地,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的——平常举动。这种分享让我感到欣喜。让我感到欣喜的,还有我们对一种历史知识的共同热爱,而那种历史正属于我们美好的生命。
[1] 本书原著标题 Wonderful Life 意为“美好的生命”。有关本书与电影《生活多美好》的渊源,详见本书 307 页脚注b——译者注
[2] 作者调侃《圣经》典故。一方面出自旧约《以赛亚书》(40:3-4)的故事。其中,一个呼喊的声音预示,要为迎接上帝“荣耀”的显现做好准备,得展平坎坷之地,通直崎岖之路等。另一方面,在新约故事〔《马太福音》(3:3)、《马可福音》(1:3)、《路加福音》(3:4)、《约翰福音》(1:23)〕里,施洗者约翰引用了这个典故, 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荒野里的呼喊)即来自相应的拉丁文翻译版本。按现在的诠释,它指的是表达无人理睬的观点。在本书中,那“伯吉斯呈现出的最后一个惊奇”在它的时代籍籍无名,毫无优势可言,没有谁会料到它的传承结果将在未来主导世界——译者注
[3] 据美国《人物》( People )杂志 1986 年 6 月 2 日号刊登的文章《斯蒂芬·杰·古尔德》,本书作者当时在病愈后的愿望之一,是以伯吉斯页岩为题材,写一本类似约翰·麦克菲作品的读物。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1931——),美国著名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将文学手法引入纪实题材。麦克菲的作品主题宽泛,也涉及地质学,深受读者欢迎,本书作者甚至为此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过书评,但麦克菲自身并非“地质学行内人”——译者注
[4] 据作者在《发现》( Discovery )杂志 1993 年 10 月号刊登的文章《解构恐龙》( Dinosaur Deconstruction ),他儿时是该博物馆的常客,每次都会在雕像前驻足,因而将这句话铭记于心。但在刊文时,他认为这句话更适合查尔斯·R.奈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