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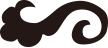

当两大文明或两种文化体系相遇时,无论是采取征服的方式、文化掠夺(如希腊“窃取”埃及)的方式,还是互相尊重、影响的双向流程方式,都是文化交流。

在文化诸层次中,最先相遇、最容易引起彼此兴趣与喜爱的,乃是文化的物质(器物)层面。世界各民族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水准高低,永远是各有所长的。因此,在彼此交往时,这些优秀的异质文化成果,最容易被对方至少出于好奇心和新鲜感而一眼看中。因此,文化交流往往从物质(器物)文化层面开始,而且基本上较少障碍。
在物质(器物)文化层面之上的,乃是制度及精神层面的文化交流。在这一广大的、高层的非物质领域,文化价值系统,特别是其核心宗教方面的交流最值得注意。“宗教信仰为人类心理最深之需要而发生,各种价值往往以宗教为中心而成系统,人生最后价值最后之保障,亦常在乎此。”

这方面的文化交流,在不同层次或者不同质地的文化系统相遇时,往往有不同的规律性表现。
当伊斯兰文明这一文化系统在广大的亚非大陆上展开、流播时,非洲与亚洲大陆上的众多处于较低文明发展状态的邦国、族群,在伊斯兰暴力抑或非暴力的文化推广面前,比较容易全盘接受这一文化系统。这是因为,“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于东方人的,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也就是说,一方面适合于从事贸易和手工业的市民,另一方面也适合于贝都因游牧民族”。
 笔者认为,如果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加以引申,伊斯兰文化系统可以说适合于一切比较简单组织的社会,而亚非大陆许多族群与邦国在它们与伊斯兰文明相遇时大都处在这一社会发展状态。
笔者认为,如果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加以引申,伊斯兰文化系统可以说适合于一切比较简单组织的社会,而亚非大陆许多族群与邦国在它们与伊斯兰文明相遇时大都处在这一社会发展状态。
当中华文明这一文化系统,向着亚非大陆诸邦国与族群流播时,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异。除日本、朝鲜半岛及越南等少数国家和地区以外,其他绝大多数邦国与族群,都较多地接受了中华文化的物质(器物)层面的文化,而对于文化的形而上层面,众多的国族虽然或者心向往之,实际接受的情况却实不多见。这一状况产生的原因大约是,日本、朝鲜半岛与越南由于紧邻中国等因素作用,较早地进入了农耕文明的一定发展高度,国情与社情有类于中国。因而,对于中华文明能够全面汲取,进入了古代的所谓汉文化圈。而对于其他亚非诸国而言,其社会与文明发展尚处于比较简单的阶段。以儒家学说或以儒佛道为核心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体系,内容极为丰富且复杂,不适于这些国家与族群接受。因而常常出现双方交往虽然表面上看似热烈频繁,但中华文化的核心部分却难以在这些国家与地区深入流播。相反,伊斯兰文明虽然传来较晚,却常有后者居上之势。
而当两个处于大体相同水准的文明体系相遇时,其形而上层面的文化交流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汤用彤先生曾历数了外来思想的输入往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即:
“因为看见表面的相同而调和”,“因为看见不同而冲突”,“因再发现真实的相合而调和”。
 这里所讲的规律性现象,实际上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外来较高的文明系统相遇而出现的状况。在古代中国,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自汉代以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第二次是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
这里所讲的规律性现象,实际上是古代中华文明与外来较高的文明系统相遇而出现的状况。在古代中国,这种情况出现过两次。一次是自汉代以来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第二次是明中叶以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
应该强调的是,古代中华文明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农业文明,内容丰富,理念、体制与运行机制皆甚为完备,因而具有很强的相对稳定性,这一文明或文化体系的核心部分,更稳定到带有某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因此,当外来文化系统,特别是异质宗教传入的时候,很容易彼此发生碰撞。因古代中华帝国的富强与文明整体领先,在遇到外来文化系统时虽极具宽容性,却在汲取外来文化体系的核心特别是其宗教思想时,会有一个十分艰苦、艰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着冲突与调和两个方面,冲突的过程很艰难,调和的过程更为艰难。
古代历史上两次流入中华的外来的高水准的文化,都是以世界主要宗教为核心的高度发展的文明系统或文化系统。一个是南亚的佛教文明,另一个是西欧的基督教文明。它们与中华固有的文化传统之间,有着相当深的文化间隔阂与异质,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沟(Cultural Gap)。如何跨越这一深沟,就有了共同的轨迹可寻。
这个共同的轨迹,就是一种文化作伪,即变幻本文化的色彩,甚至披上一层容易与对方文化混同的迷彩服,暗度陈仓,使对方文化本质的固守警觉性神经遭到麻痹,从而达到向对方渗透、流播的目的。不难看到,无论是汉魏以降佛教文化的传入,还是晚明基督教文化的传入,都是采用这种手段。东汉时期中国典籍的记载清楚地告诉我们,初期来华的佛教,将自己装扮得与黄老并无二致,因而获进身之阶,在楚王刘英的上层文化圈内得其所哉,甚至得到了汉明帝的认可。晚明来华的基督教可以说是拿佛教的故伎重演。利玛窦不就是“身着儒装传耶教,口述四书讲圣经”么?

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
事实上,这种麻痹对方的手段,是一种双刃兵器,在麻痹对方的同时往往也会麻痹自己。当你变幻色彩,企图通过混同对方的办法进行渗透时,实际上也在使自己悄悄地发生异化。在适应对方文化环境的同时,自身也在发生某种质的变化。佛教传入中国,特别是传入中原地区以后,逐渐实现了它的中国化,从而展现了它文化系统内核的魅力。它与儒学相互渗透、影响的结果,使之深深进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亿万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灵魂深处,大约既是孔孟弟子,又是佛门弟子。佛教,终于同儒道两家交融一起,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
利玛窦的传教也是成功的。如果没有罗马教廷由于无知与顽愚而挑起的礼仪之争,基督教文化系统或许会在中国扎下更深的根,而不会在康雍乾盛世时一度被连根拔除。然而,从长期的走势看,这一文化系统核心的排他性,使它终将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不可避免的剧烈冲突。佛教那般适应中国情况,尚且遭遇过三武灭佛
 ;基督教在华流播所受阻力,不难想象要大上许多倍。即使利玛窦们一派得势一直稳居上风,基督教在古代环境下,至多如伊斯兰教那样,在中国被宽容,而绝难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
;基督教在华流播所受阻力,不难想象要大上许多倍。即使利玛窦们一派得势一直稳居上风,基督教在古代环境下,至多如伊斯兰教那样,在中国被宽容,而绝难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

中国古书里的“麒麟”形象
在文化交流中,人们还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叫作文明或文化的误读。或也可以称之为文明或文化的错误认同(False Identifi cations)。这种误读或错误认同,一般发生在文化引进的一方。例如,中世纪的欧洲,人们相信有一种“独角兽”的存在,马可·波罗在亚洲各地寻觅,终于在爪哇遇到犀牛,于是怀抱自己文化背景的需求,将其误读为“独角兽”。又如,大明永乐年间,南亚的榜葛拉国与东非的麻林国向天朝朝贡的贡品中,有珍奇异兽长颈鹿(名Gili,后发展为英语Giraff e),被中国人误读为“麒麟”。麒麟在数千年以来被中国人视为祥瑞之物。祥瑞来朝,岂不象征着大明帝国的昌盛?于是长颈鹿竟也被纳入中国文化系统之中,君臣朝野,皆大欢喜!物质文化如此,精神文化亦如此。明晚期由西方佛教士们翻译的儒学以及中国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也在西方启蒙运动先驱们那里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的光环。那些从未到过中国也根本无意来华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无意求取中华文明的真经,却有心编撰一部近代文明的新经。而这部文明新经的编撰,又正是当时剧变中的西欧的一种社会需求,一个时代的呼唤。启蒙学者们将传教士隔雾看到的中华文明之花借来,用自己受当时社会需求所决定的心态与目光,将这一雾中花进一步加以欧式雾化,终于将其误读成自己所需要的精神武器,向着欧洲中世纪的专制、愚昧与黑暗奋勇出击。

穿着蒙古人服饰的威尼斯商人、旅行家和探险家马可·波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