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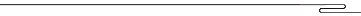
郑师许先生所著《铜鼓考略》《漆器考》二书既付印,郑先生忽以其令堂有贵恙南归,校稿事因嘱余为之。余以馆中作说明及陈列之工作纷繁,致不能精为校勘,今出版后读之,觉尚有讹字,如“钜鹿”之讹作“钜訠”,知校勘之事实难,亦余事忙疏忽之过,此余深感不安,于郑先生及读者殊觉抱歉者也。
自来关于铜鼓之考论,莫详于谢启昆之《铜鼓考》,见《粤西今石略》,然关于铜鼓之史料搜罗,尚未备,论断犹未详尽也。日本鸟居龙藏著《苗族调查报告》,其第八章《铜鼓》,虽较谢氏为备,但其关于铜鼓之来源及其所以埋藏地下之故等等,皆未详,今郑先生《铜鼓考略》此书,于文献之记载既搜罗详尽,于诸家难解之诸问题,论断尤精审,曰“略”者,盖以于花纹之比较研究与化学之分析研究尚有所不及也。
《铜鼓考略》全书都六十余面,未分章节,盖郑先生信笔滔滔写下,一时未计章节,书既成,又为寿县史迹考察团事,匆匆往寿县。自寿县归后,又因其令堂病笃,急急于南归。既归后,郑先生以校稿是嘱余,余不敢贸然代为分章节,而郑先生又远在广州,信只往返费时,博物馆又急急欲开幕,此书为丛书之一,亦急急于出版,因念此书通条连贯,纲目读者自能知之,初不必分章节也。
铜鼓为南蛮之物,经郑先生如是之博征旁稽,可信而有征矣。铜鼓多数有花纹,有铭文者极少,纪年者更不多见,惟英国博物院中藏有“纪年之铜鼓”,其铭曰:“建安四年八月五日制”。此等文字,当亦蛮人从汉人中学得者,当非出于汉人手也。铜鼓固甚早行之于南蛮中,其花纹与中国铜器之花纹相殊异,其非出于同一系统,至为明显。
自来关于漆器之考论,仅明曹仲明《格古要论》中有古漆器论及张应文《清秘藏》论雕刻条。中国考古学尚在幼稚时代,地下之材料不多,晚近朝鲜乐浪之挖掘,汉代漆器固可由此大显,然其演变之历程如何,其传布之历程如何,尤待于论究也。《格古要论》《清秘藏》之论漆器,皆自宋起,宋以后如何之演变亦语焉不详。今郑先生此考,尤多未餍人望,但以地下材料之不多,仅能如此而已。汉代漆器有乐浪之资料,固可恣意检讨。民国十九年间钜鹿故城之挖掘,其漆器出土若何,吾人又不得而详知。我人甚望因此激起国人之注意,于我国特有之艺术漆器特加注意之。
(原刊上海《大美晚报·历史周刊》1937年1月25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