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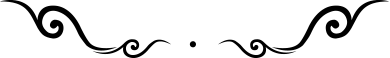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所有莫斯科的亲戚和朋友都在教堂里了。在举行订婚仪式的时候,在教堂里的华烛照耀下,在服饰华丽的太太、小姐和系白领带、穿燕尾服或制服、军服的男人群里,一直有些人彬彬有礼地小声说着话儿,不过多半是男子说起头的,因为女士们都聚精会神地观察着各种细节,因为这种宗教仪式总是能深深打动她们的心。
在离吉娣最近的一小堆人当中,有她的两个姐姐:大姐陶丽和刚从国外回来的二姐、娴静美丽的李沃夫夫人。
“玛丽怎么穿着紫得像黑的一样的衣裳来参加婚礼呀?”科尔松斯基夫人说。
“她那种脸色,只有穿这种颜色才配称……”德鲁别茨基夫人说,“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在晚上举行婚礼。这是商人习气……”
“这样更好些。我也是傍晚结婚的。”科尔松斯基夫人回答说,并且叹了一口气,因为想起那一天她有多么美,丈夫爱她爱得多么痴心,可惜那都是明日黄花了。
“据说,做傧相十次以上,就可以不结婚了;我真想做这第十次,就可以给自己保险了,可是这差事已经有人干了。”西尼亚文伯爵对美貌的查尔斯基公爵小姐说。这位公爵小姐对他是有情意的。
查尔斯基小姐只是以微笑作为回答。她望着吉娣,心里想着,有朝一日她也站在吉娣的位子上,跟西尼亚文伯爵在一起,那时候她要向他提一提他现在说的笑话。
谢尔巴茨基对老女官尼古拉耶娃说,他想把花冠戴到吉娣的假发上,祝她幸福。
“不应该戴假发。”尼古拉耶娃回答说。她早就打定主意,如果她追求的那个老鳏夫和她结婚,婚礼将会是最简单的。“我就不喜欢这种花哨。”
柯兹尼雪夫和达丽雅·德米特里耶芙娜在说话儿,开玩笑说,婚后外出的风俗之所以流行,是因为新婚夫妻总是有点儿怕羞。
“令弟可以感到自豪。她真是可爱极了。我看,您眼热了吧?”
“我眼热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达丽雅·德米特里耶芙娜。”他回答说,他的脸上突然出现了惆怅和严肃的神气。
奥布朗斯基正在对他的姨妹说有关离婚的俏皮话。
“要把花冠弄端正些。”她没有听他的话,却说道。
“多么可怜呀,她消瘦多了。”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对李沃夫夫人说,“不论怎么说,他都抵不上她一个手指头,不是吗?”
“不,我倒很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是我未来的妹夫。”李沃夫夫人回答说,“他的举止多么有分寸呀!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举止得当,不显得可笑,有多么难呀。可是他并不显得可笑,也不紧张,他显然也是很激动的。”
“这事儿您好像是料到的了?”
“差不多。她一直是爱他的。”
“好吧,咱们就看看,他们哪一个先踏上红垫。我对吉娣说过了。”
“反正都一样。”李沃夫夫人说,“我们姊妹都是百依百顺的妻子,这是我们的天性。”
“可是我当时就有意抢在瓦西里前头踏上去。陶丽,您呢?”
陶丽就站在她们旁边,听见她们的话,却没有搭话。她十分动情。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只要一开口,就会大哭起来。她为吉娣和列文高兴。回想起自己结婚的情景,她望了望满面红光的奥布朗斯基,就忘记了当前的一切,想着的只是自己那纯真的初恋。她回想的不仅是她自己,而是和她亲近和她熟悉的所有女子的往事;她回想着她们在她们一生一次的庄严时刻的情形,那时候她们也像吉娣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满怀着爱、希望和恐惧告别过去,跨向神秘的未来。在她想到的这些新娘中,也有她不久前听说要离婚的她心爱的安娜。她当年也是这样戴着香橙花冠,披着白纱这样纯真地站着的。现在又怎样呢?
“简直奇怪。”她说出声来。
仔细注视着宗教仪式进程的不仅是两位姐姐、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那些看热闹的不相干的女人也都屏着呼吸,激动地注视着,生怕看漏了新郎新娘的任何一个动作和表情,有些无动于衷的男人在说笑话或者不相干的话,她们气得不理不睬,而且常常听不清他们说的是什么。
“怎么她眼泪汪汪的呀?是不是不愿意嫁给他呀?”
“嫁给这样的好小伙子,还有什么不愿意的?是一位公爵吗?”
“那个一身白缎子的是她的姐姐吗?哦,你听,司祭扯着嗓子叫呢:‘要怕丈夫呀。’”
“这是邱多夫教堂唱诗班吗?”
“是西诺达里教堂的。”
“我问过仆人。仆人说他就要带她到自己庄子上去。据说他是个大财主。所以才嫁给他。”
“不,倒是挺好的一对呢。”
“哦,玛丽雅·瓦西里耶芙娜,您还说穿裙子不用裙箍呢。你看那个穿深褐色裙子,鞋后跟老高的,听说是个公使夫人……那裙子飘来荡去的。”
“这新娘子多么可爱呀,就像是一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羊羔儿!不管怎么说,还是该心痛咱们女人家。”
好不容易挤进教堂看热闹的妇女群里就是这样纷纷议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