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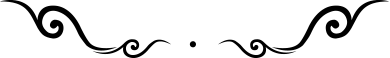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来了!”“就是他!”“哪一个呀?”“怎么,是那个年纪轻些的吗?”“那就是她,我的妈呀,她可是急坏了!”当列文在门口迎住新娘,同她一起进入教堂的时候,人群里有一些人议论起来。
奥布朗斯基对妻子说了说迟到的原因,于是来宾们笑嘻嘻地交头接耳低语起来。列文却什么人、什么事也看不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新娘。
大家都说她这些天来消瘦了不少,戴起花冠远远没有平时好看;但列文却看不出这一点。他看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白色鲜花的高高的发髻,看着那特意像少女一般遮住长脖子的两侧、只敞着前面的高高的带褶领子,还有那细得惊人的腰身,他就觉得,她比任何时候都美,——并不是这鲜花、这长纱、这从巴黎定做的连衫裙为她的美增添了什么,而是因为,尽管她打扮得如此华丽,她那可爱的脸、那眼睛和嘴唇流露的依然是她那种纯洁真挚的特殊神情。
“我还以为你想逃走呢。”她说过,对他嫣然一笑。
“我出了一点事儿,太荒唐了,简直不好意思说!”他红着脸说过这话,便不得不和走到跟前的柯兹尼雪夫打招呼。
“你的衬衫故事太妙啦!”柯兹尼雪夫摇着头,笑着说。
“是的,是的。”列文回答说,虽然他不明白,别人对他说的是什么。
“哦,康斯坦丁,现在要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奥布朗斯基故作惊惶地说,“正是现在你能充分估量这问题的重要性。他们问我:是点已经点过的蜡烛呢,还是没有点过的蜡烛?相差十个卢布。”他补充说,一面让嘴做好笑的准备。“我已经解决了,就是怕你不同意。”
列文懂得这是开玩笑,但是他不能笑。
“到底怎么办?点没有点过的还是点过的?问题就是这样。”
“对,对!点没有点过的!”
“哦,我很高兴。问题解决了!”奥布朗斯基笑着说,“不过,人处在这种情况下有多么糊涂呀。”等列文六神无主地看了他一眼,走到新娘跟前之后,他对契利科夫说。
“注意,吉娣,你要第一个站到红垫上。”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走过来说,“您倒是很好!”她对列文说。
“怎么样,不害怕吧?”老姑母玛丽雅·德米特里耶芙娜说。
“你是不是觉得冷呀?你的脸好白呀。等一等,把头低下来!”吉娣的姐姐李沃夫夫人说着,弯起一双丰润的玉臂,给她理了理头上的鲜花。
陶丽走过来,想说点什么,可是说不出来,哭了起来,又很不自然地笑起来。
吉娣也像列文一样,用视而不见的眼睛望着大家。不论别人对她说什么,她只能报以幸福的微笑,这样的微笑现在在她是极其自然的了。
这时候神职人员都穿起法衣。司祭带着助祭朝教堂入口处的读经台走去。司祭转身对列文说了一句话。列文却没有听清司祭说的是什么。
“您挽住新娘的手,领着她走。”傧相对列文说。
列文有好一阵子不明白,他们叫他做什么。有好一阵子他们一再纠正他的动作,并且已经想不再管他了,因为他不是伸错了自己的手,就是挽错了吉娣的手,最后他才明白了,应该是不变换位置,用右手挽她的右手。等到他终于照规矩挽住新娘的手,司祭在他们前面走了几步,在读经台前站了下来。一大群亲友跟在他们后面移动起来,只听到嗡嗡的低语声和衣裙窸窣声。有人弯下腰,拉了拉吉娣的拖地长裙。教堂里顿时鸦雀无声,连蜡烛滴油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司祭小老头儿头戴法冠,那银光闪闪的白色鬈发在耳后分成两股,穿着笨重的银色法衣,背上系着金十字架,他从法衣下伸出小小的老手,在读经台旁翻着什么。
奥布朗斯基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小声对他说了句什么,朝列文使了个眼色,便又退到后面。
司祭把两支描花的蜡烛点着了,用左手斜拿着,让烛油慢慢往下滴着,便转脸朝着订婚人。司祭就是听列文忏悔的那个小老头儿。他用疲惫而忧郁的目光看了看订婚人,叹了口气,便从法衣里伸出右手,为列文祝福,又照这个样子,但带点儿小心温柔的意味,把撮起的手指头放在吉娣垂下的头上。然后他把蜡烛交给他们,拿起小香炉,慢慢从他们身旁走开。
“难道这是真的吗?”列文在心中说,并且转头看了看新娘。他的目光微微向下,就看清了她的侧面,他从她那嘴唇和睫毛的轻微动作上看出来,她感觉出他在看她。她没有转头,但是那带褶的高领子动了起来,不住地朝那粉红色小耳朵耸着。他看出来,她在胸中憋着呼吸,那拿着蜡烛的戴长手套的玉手也抖动起来。
衬衫和迟到引起的手忙脚乱,和亲友们的交谈,他们的抱怨,他的可笑处境——这一切顿时消失了,于是他高兴起来,也害怕起来。
身穿银色法衣、鬈发梳向两边的又英俊又高大的大辅祭很麻利地跨到前面,熟练地用两个手指提起肩衣,站到司祭对面。
“我主……赐……福……吧!”那庄严的声音慢慢地、接连不断响起来,震得空气都颤动起来。
“我主是仁慈的,千秋万代,永远一样。”司祭小老头儿温和地用唱歌般的声音回答说,一面继续在读经台上翻着什么。于是,那看不见的唱诗班的各种各样的嗓门儿齐声唱了起来,那声音又和谐又洪亮,从窗子到圆顶,响彻整个教堂,越来越响,在空中回荡了一会儿,就慢慢消失了。
大家像往常一样,祈求上帝保佑平安,祈求拯救,祈求主教公会,祈求皇上;也为今天订婚的上帝的奴仆列文和吉娣祈祷。
“祈求我主恩赐他们完美的爱和平安,帮助他们吧。”大辅祭的声音在整个教堂里回荡起来。
列文听着他的祈祷,感到惊讶。“他们怎么猜到我需要的是帮助,正是帮助呢!”他想起不久前的恐惧和疑虑,便在心中说,“我懂得什么呢?如果没有帮助,遇到这种可怕的事儿,我怎么办呢?现在我就是需要帮助。”
等助祭念完祈祷词,司祭便手捧《圣经》对新郎新娘念起来:
“永恒的上帝呀,你让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吧。”他用亲切的唱歌般的声音念道,“让他们结成爱侣,永不分离;你曾赐福于以撒和利百加,并依照圣约赐福于他们的后代,你就赐福于你的奴仆康斯坦丁和叶卡吉琳娜,让他们从此走上幸福之路吧。仁爱的上帝,大慈大悲,光荣归于圣父、圣子、圣灵,千秋万代,永无穷尽。”“阿门!”那看不见的唱诗班的合唱声又回荡在空中。
“‘让分离的两人合为一体,让他们结成爱侣,永不分离,’这话的意义多么深刻呀,多么符合我此刻的心情呀!”列文想道,“她的心情也和我一样吧?”
于是他转头看了看,就碰上她的视线。
于是他从她的眼神断定,她也有和他一样的体会。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祈祷词她几乎一句也不懂,甚至在举行订婚礼时间里她连听都不听。她无法听,也无法听懂,因为充溢在她心中的一种感觉异常强烈,而且越来越强烈。这种感觉就是高兴,高兴的是,一个半月以来萦绕在她心头的事,六个礼拜时间里使她又高兴又苦恼的事,现在完全实现了。那一天,她在阿尔巴特街自己家的客厅里,穿着自己的咖啡色连衫裙,默默无言地走到他跟前,以身相许之后,在她心里从那一天那一刻起,就和过去的生活告别了,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她还完全不清楚的生活,虽然事实上旧的生活并未停止。这六个礼拜是她最幸福也是最苦恼的时期。她的整个生活、所有的心愿和指望都集中在一个她还不理解的男人身上,而使她和他结合的是一种比男人本身更难理解的、时而使人亲近、时而使人疏远的感情,同时她又继续在原来的生活环境中生活着。她一面过着原来的生活,一面对自己感到害怕,害怕自己也无法克制的冷漠,因为她对自己过去的一切,对一切事和习惯,对过去和现在爱她的人都冷漠了,对母亲也冷漠了,母亲因此十分伤心,对亲爱的父亲也冷漠了,以前她可是觉得他是天下最可亲可爱的慈父呀。她时而对这种冷漠感到害怕,时而对造成这种冷漠的原因感到高兴。除了和这个人在一起的生活以外,她什么也不能想,什么愿望也没有了。然而这种新的生活还不曾过过,所以她还想象不出是怎样的。对于未知的新生活,只有等待,只有害怕和高兴。现在这种等待,这种不知道,这种告别原来生活的怅惘状态——这一切就要结束,新的一切就要开始。这新的一切,因为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不能不是很可怕的;但不管可怕还是不可怕,六个礼拜之前在她心中已经形成了,现在不过是让她心中早已形成的一切神圣化罢了。
司祭又转身朝着读经台,好不容易捏住吉娣的小小的戒指,要列文伸出手来,把戒指套在他的手指的第一个关节上。“上帝的奴仆康斯坦丁与上帝的奴仆叶卡吉琳娜永结同心。”司祭把一个大戒指套在吉娣那细小得可怜的粉红色手指上以后,也说了同样的话。
订婚人想猜到他们该做什么,可是每一次他们都错了,于是司祭就小声叫他们改正。终于,司祭完成了应有的仪式,用他们的戒指画过十字之后,又把大戒指交给列文,把小戒指交给吉娣;他们又迷糊了,在手里把戒指来回倒换了两回,结果还是做得不合乎要求。
陶丽、契利科夫和奥布朗斯基都走上前来纠正他们的动作。教堂里乱腾起来,又是低语,又是微笑,但订婚人脸上那种庄严和感动的表情并未改变,相反,他们的手虽然不知所措,他们的神情却比以前更严肃和庄重,奥布朗斯基本来笑着小声提醒他们各人戴上自己的戒指的,这微笑也就不由地从他嘴唇上消失了。他觉得,任何微笑都会使他们不快的。
“你开天辟地创造了男人和女人。”司祭在交换过戒指之后紧接着念道,“你让他们结为夫妻,让他们生儿育女。主啊,我们的上帝,你把真理和幸福赐予你所选择的奴仆,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未曾中断,今天你赐福于你的奴仆康斯坦丁和你的奴仆叶卡吉琳娜吧,让他们在信仰、思想、真理和爱情中永结同心……”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的一切有关结婚的想法,怎样安排自己生活的梦想,都是孩子气的,他觉得这是一种他至今不理解、现在更加不理解的事儿,虽然他正做着这事儿;他的胸中颤动得越来越厉害,不听话的泪水涌上他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