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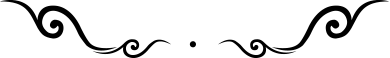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列文遵照风俗(公爵夫人和陶丽坚持要遵守一切风俗)不和未婚妻见面,而是在自己的旅馆里和偶然来到他这儿的三个单身汉一起吃饭。一个是柯兹尼雪夫;一个是卡塔瓦索夫,是他大学里的同学,现在是自然科学教授,是列文在街上碰见他,把他拉到这儿来的;还有一个是契利科夫,是莫斯科的调解法官,列文的傧相,也是他猎熊的伙伴。这顿饭吃得非常快活。柯兹尼雪夫情绪极好,听到卡塔瓦索夫别出心裁的说法非常开心。卡塔瓦索夫感觉到他的说法得到看重和理解,就尽情加以发挥。契利科夫又快活又和善,不论别人谈什么,他都要凑热闹。
“你们可知道。”卡塔瓦索夫依照讲堂上养成的习惯,拉长声音说,“我们这位朋友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当年是一个多么有才华的年轻人呀。我说的是过去,因为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当初他刚刚离开大学的时候,还是热衷于研究学问的,他的兴趣也是正常人都有的。可是现在呀,他的才华却一半用于欺骗自己,另外一半用来为这种欺骗作辩护。”
“比您更坚决反对结婚的,我可是没有见过。”柯兹尼雪夫说。
“不,我并不反对。我是赞成分工。有些人,什么也不会做的,就应该造造人;另外一些人就应该促进他们的教育和幸福。我就是这样看的。有许多人喜欢把这两种行当混为一谈,我却不是这样。”
“等我听到您恋爱的时候,就不知道有多么开心了!”列文说,“到时候您一定要请我去参加婚礼。”
“我已经恋爱啦。”
“是的,您爱上了墨鱼。你可知道。”列文对哥哥说,“米海尔·谢苗内奇在写一本有关营养的著作呢……”
“哎,别胡扯了!写什么那都无所谓。只不过我确实爱墨鱼。”
“不过墨鱼并不妨碍您爱妻子。”
“墨鱼倒不碍事,可是妻子就碍事了。”
“为什么呀?”
“到时候您就明白了。现在您又喜欢农事,又喜欢打猎,可是到时候您看吧!”
“哦,今天阿尔希普来了,他说普鲁特村有许多驼鹿,还有两头熊呢。”契利科夫说。
“噢,我不去了,你们就去打吧。”
“这就对了。”柯兹尼雪夫说,“今后你就跟猎熊这种事儿无缘了,妻子不会让你去的!”
列文笑了笑。他想象到妻子不让他去的情景,心里美滋滋的,情愿永远放弃猎熊的乐趣。
“不过,您要是不去,就是打到这两头熊,那也是很可惜的。还记得在哈比洛夫那一次吗?那可是太漂亮了。”契利科夫说。
他认为列文不结婚也会有快活事儿,列文不愿意扫他的兴,所以什么也没有说。
“难怪有这种同单身生活告别的风俗。”柯兹尼雪夫说,“不论有多么幸福,失去自由还是可惜的。”
“您可承认,有一种感觉,就像果戈理笔下的新郎
 那样,想从窗口跳出去吗?”
那样,想从窗口跳出去吗?”
“肯定有的,不过就是不承认!”卡塔瓦索夫说过,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样,窗子开着嘛……咱们这就到特维尔去!那儿有一头母熊,咱们就直捣熊窝。真的,咱们就坐五点钟的火车!这儿的事就随他们怎样好啦。”契利科夫笑着说。
“可是,说真的。”列文笑着说,“我心里却没有这种惋惜失去自由的感觉!”
“您现在神魂颠倒,自然不会有什么感觉啦。”卡塔瓦索夫说,“您等着吧,等到多少清醒一点儿,那就有感觉了!”
“不,如果真是那样,我总会多少感觉出,有了感情(他不愿意当着他的面说是爱情)……和幸福,失去自由毕竟是可惜的……事实恰恰相反,我还为这种失去自由感到高兴呢!”
“真糟!这人真是不可救药!”卡塔瓦索夫说,“来,咱们干一杯,祝他清醒,或者祝他的梦想哪怕有百分之一能够实现。那也就算天下难得有的幸福了!”
一吃过饭客人们就走了,为的是赶紧回去换衣服好参加婚礼。
等到剩了列文一个人,他回想着这些单身汉说的话,又一次问自己:他心里究竟有没有他们说的那种丧失自由的惋惜感?他这样一问,不禁笑了。“自由吗?要自由干什么?幸福就在于爱情,愿她之所愿,想她之所想,也就是一点自由也没有,——这就是幸福!”
“可是我了解她的所想所愿,了解她的心情吗?”忽然有一个声音悄悄对他说。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沉思起来。他心中忽然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心情。他感到害怕和怀疑,怀疑一切。
“万一她不爱我呢?万一她只是为了出嫁才嫁给我呢?万一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在做什么呢?”他在心中问道,“她也许会清醒过来的,一结过婚就明白她不爱我,而且不可能爱我了。”于是一些有关她的奇怪的、最坏的想法来到他的心头。他嫉恨起她对伏伦斯基的感情,就像一年前那样,似乎他感到她和伏伦斯基在一起的那天晚上就是昨天。他怀疑她没有把一切都告诉他。
他一下子跳起来。“不行,这样可不行!”他灰心绝望地在心里说,“我要去找她,问问她,最后一次对她说:咱们都是自由的,是不是到此为止更好些呢?不管怎样,总要比一辈子不幸、耻辱和不贞好些!”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和愤恨一切人、愤恨自己和愤恨她的心情走出旅馆,坐上马车就去找她。
他在后屋里找到了她。她坐在大箱子上,和侍女一起在收拾东西,挑拣着搭在椅背上和堆在地板上的五颜六色的衣服。
“哈!”她一看到他,高兴得满脸放光,立刻叫了起来。“你怎么,您怎么(最近几天她对他忽而称“你”,忽而称“您”)来啦?真没想到!我正在挑拣我做姑娘时的衣服呢,看哪一件给什么人合适……”
“啊!这太好了!”他闷闷不乐地看着侍女说。
“杜尼娅,你去吧,有事我再叫你。”吉娣说,“你怎么啦?”等侍女一走出去,她就果断地称呼着“你”,问道。她发现他的脸色很奇怪,一张脸又激动又阴沉,她吓坏了。
“吉娣!我很苦恼。我一个人受不了。”他在她面前站住,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她的眼睛,用灰心绝望的声调说。他已经从她那亲热而真挚的脸色看出来,他要说的是不会有的事,但他还是需要她亲自消除他的疑虑。“我来是要说说,现在还不算晚。这一切还可以停止和改变。”
“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怎么啦?”
“我说过一千遍和我不能不考虑的是……我配不上你。你是不可能同意嫁给我的。你想想吧。你错了。你好好想想吧。你是不可能爱我的……如果……最好还是说吧。”他也不看她,说道,“我会很不幸的。让大家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好啦;总比不幸要好些……趁现在还不晚,不论怎样总要好些……”
“我不懂。”她恐惧地回答说,“就是说你想反悔……不办了吗?”
“是的,要是你不爱我的话。”
“你疯了!”她气得红了脸,叫了起来。
但是他的脸色是那样悲凄,她不由得压住怒火,把椅背上的衣服推下去,坐到他身边。
“你是怎么想的呀?全都说说吧。”
“我想,你是不可能爱我的。你凭什么会爱我呀?”
“我的天哪!我怎么办呀?……”她说着,哭了起来。
“啊呀,我这是干的什么事呀?”他叫起来,并且在她面前跪下来,吻起她的手来。
五分钟之后,公爵夫人走进来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和好了。吉娣不仅使他相信了她爱他,而且为了回答他心中存在的她为什么爱他的问题,向他解释了为什么爱他。她告诉他,她爱他是因为完全了解他,因为她知道他喜欢什么,知道他所喜欢的一切都是很好的。他觉得这就完全明白了。在公爵夫人进来的时候,他们正并肩坐在大箱子上,挑拣着衣服,并且在争论着,因为吉娣想把列文求婚时她穿的那件咖啡色连衫裙给杜尼娅,列文坚决不让她把这件衣服给任何人,可以给杜尼娅一件蓝色的。
“你怎么不懂呀?她是黑头发的,穿蓝的不配称……这一切我都考虑过了。”
公爵夫人听说他是为什么来的,半真半假地生起气来,叫他快回去换衣服,不要妨碍吉娣梳头,因为理发师沙尔里就要来了。
“就这样她这几天什么也不吃,人也瘦了,可是你还要说你那些傻话,让她烦恼。”她对他说,“快走吧,快走吧,好孩子。”
列文又歉疚又羞惭,但却完全放心地回到自己的旅馆。他的哥哥、陶丽和奥布朗斯基全都盛装打扮,已经在等他了,为的是拿圣像为他祝福。不能再耽搁了。陶丽还要回家去一趟,把她那个卷过头发并且抹了油的儿子接来,儿子要捧着圣像伴随新娘。还要派一辆车去接男傧相,派另一辆车把柯兹尼雪夫送走再转回来……总之,事情是相当复杂的,也是很多的。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能再磨蹭了,因为已经六点半了。
圣像祝福仪式很不像样子。奥布朗斯基同妻子并排站着,摆出很可笑的庄重姿势,拿起圣像,吩咐列文鞠躬到地,又带着亲热和取笑的神气吻了他三下;陶丽也照着做了之后,就匆匆坐上马车,并且又忙得不可开交地调度起车辆。
“哦,那咱们就这样办吧:你坐咱们的轿车去接他,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如果愿意的话,请他到了之后就把马车打发回来。”
“好的,我照办。”
“我这就去把他接来。东西都送去了吗?”奥布朗斯基说。
“送去了。”列文回答过,就吩咐库兹玛把要换的衣服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