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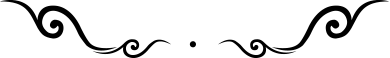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谢尔巴茨基公爵夫人本来以为,在大斋之前不可能举行婚礼,因为到大斋期只剩了五个礼拜,这期间连一半嫁妆也来不及备办;但是她不能不同意列文的意见,就是说,到大斋以后那就太迟了,因为公爵的老姑母病重,可能不久于人世,一旦服丧,就一时不能结婚了。因此,公爵夫人同意在大斋之前举行婚礼,把嫁妆分成两部分,一份大的和一份小的。她决定现在就把小的一部分嫁妆备办齐全,大的一份以后再送去,列文却怎么也不肯认真回答,是不是同意这样办,这使她非常生气。她这个想法是挺不错的,尤其因为这对年轻夫妻一结过婚就要到乡下去,在乡下是用不着大的一份嫁妆的。
列文还一直处在神魂颠倒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仿佛觉得,他和他的幸福是世间万物的主要和唯一的目的,现在他无须考虑什么,操心什么,一切事情自有别人为他操办,自会办得好好的。他对未来的生活也没有什么计划和打算;他让别人去决定一切,因为他知道一切都会非常圆满的。他该怎么做,有哥哥柯兹尼雪夫、奥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指点他。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完全同意。哥哥为他借了钱,公爵夫人劝他结过婚就离开莫斯科。奥布朗斯基劝他出国。他全都同意。他心想:“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只要你们高兴。我是幸福的,不论你们怎么办,反正我的幸福也不会增加或减少。”等他把奥布朗斯基劝他们出国的主意对吉娣说了,却未料到,她不赞成这个主意,而是对未来生活有自己的一套打算。她知道,列文的事业在乡下,那是他所热爱的。他看出来,她不仅不理解这事业,而且也不想理解。不过这不碍事,她仍然认为这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就因为她知道他们的家将安在乡下,所以不愿意到国外去,不能在国外过日子,而是要到他们安家的地方去。这种表示得很明确的心意使列文感到惊讶。但是因为他觉得去哪儿都是一样,于是就立刻请奥布朗斯基到乡下去安排一番,似乎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有丰富的情趣,就让他凭他的情趣把那里的一切安排得好好的。
“不过,你听我说。”奥布朗斯基为新婚夫妇安排好去乡下的一切,从乡下回来之后,有一天对列文说,“你有做过忏悔的证书吗?”
“没有。怎么啦?”
“没有这东西不能举行婚礼呀。”
“哎呀,哎呀,哎呀!”列文叫起来。“我好像有八九年没有斋戒了。我连想都没有想过呢。”
“你真够受!”奥布朗斯基笑着说,“可是你还说我是虚无主义者呢!这是不行的。你必须斋戒。”
“什么时候斋戒?只剩下四天了呀。”
奥布朗斯基也把这事安排了一下。于是列文开始斋戒。像列文这样不信教而又尊重别人的信仰的人,参与任何宗教仪式都是很难受的。现在,在他对一切都很敏感、心情特别温和的时候,像这样不得不装模作样,就不仅是难受,而且他觉得是不堪设想的。现在,在自己最光彩、最舒畅的日子里,他却不得不说谎作假,要么就亵渎神明。他觉得自己既不能作假,也不能亵渎神明。可是他问过奥布朗斯基多少次,能不能不斋戒就领到证书,奥布朗斯基说那不可能。
“就这么两天,这又算得什么呀?而且那司祭是一个极好的聪明老头儿。他会不等你发觉,就把你这颗牙拔掉了。”
列文在站着做第一次日祷的时候,就想唤起他在十六七岁时体验过的那种少年时代的强烈宗教感情。但是他立刻就认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想把这一切看作毫无意义、无关紧要的风俗,就像拜客访友的风俗;但是他觉得他连这一点也无法做到。列文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像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是摇摆不定的。他既不能相信,同时又不能坚决认定这一切都是毫无道理的。就因为他既不相信自己所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也不能把这当作无关紧要的形式而漠然视之,所以在整个斋戒和祈祷期间,他做着他自己不理解的事情,因而也就是他内心里觉得虚假和不好的事情,总觉得很不自在和羞惭。
在做祈祷的时候,他有时听着祷告,想方设法为祷告增添不违反他的观点的意义,有时觉得自己无法理解,觉得应该加以指责,就尽量不听祷告,而是想自己的心思,左顾右盼,回想往事,就在他这样无所事事地站在教堂里的时候,种种往事就特别真切地浮现在他的脑际。
他做过日祷、晚祷和夜祷,到第二天,又很早就起身,连茶也不喝,早晨八点钟就来到教堂做早祷和忏悔。
在教堂里,除了一个求乞的士兵、两个老婆子和几个教堂执事,再没有什么人。
一位年轻的助祭,穿着薄薄的法衣,那长长的脊背的两半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他迎住列文,就立刻走到靠墙的小桌旁,念起训条。在他念的时候,尤其是在他一再很快地重复“上帝宽恕吧”的时候,列文觉得他的思想被锁起来,而且贴了封条,现在不能碰、不能动了,要不然就乱成一团了,因此他站在助祭后面,不听也不理会,继续想自己的心思。“她手上的表情真是太丰富了。”他想起昨天他们坐在角落里那张桌子旁的情景,在心里说。当时他们无话可说,在这些日子里差不多总是这样。于是她把一只手放在桌上,不住地张开又合拢,看着手的动作,自己笑了起来。他想起他怎样吻了吻这只手,然后又怎样细细观看那粉红色手掌上纵横交错的纹丝。“还一个劲儿在念哩。”列文画着十字,鞠着躬,望着正在鞠躬的助祭的脊背那柔软的动作,在心里说,“然后她抓住我的手,仔细看了看手上的纹路,就说:你这手真是极好的手。”于是他看了看自己的手,又看了看助祭那短短的手。“哦,现在快完了。”他想道,“不,好像又要从头念起呢。”他听着祷告,又想道,“不,要结束了;瞧,他已经一躬到地了。要结束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助祭用手在波里斯绒袖口里悄悄接下一张三卢布钞票,说他要记下来的,然后就用新靴子咚咚地踩着空荡荡的教堂的石板,很麻利地走上祭坛。过了一小会儿,他从那里朝外看了看,朝列文招了招手。一直封锁着的思想这时在列文头脑里动了起来,但是他连忙驱散了。“总有完的时候吧。”他在心里说过,就朝读经台走去。他上了台阶,向右一转,就看到了司祭。司祭是个小老头儿,稀稀的下巴胡已经白了一半,一双和善的眼睛无精打采的,他正站在读经台旁翻着圣礼书。他轻轻地向列文点了点头,立刻就用习惯的腔调念起祷词。他念完了,一躬到地,然后朝列文转过脸来。
“无形的基督已经降临,在听取您的忏悔。”他指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您相信圣徒教会的全部教义吗?”司祭眼睛不再看列文的脸,双手在圣带下面合拢起来,继续说道。
“我怀疑过,而且现在还怀疑一切。”列文用自己也不喜欢的腔调说过这话,就不说了。
司祭等了几秒钟,看他是不是还说什么,然后就合上眼睛,用很重的弗拉基米尔地方口音很快地说: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不过我们应当祈求仁慈的上帝巩固我们的信仰。您有什么特别的罪过吗?”他好像是想尽量抓紧时间,不歇气地问道。
“我的主要罪过就是怀疑。我怀疑一切,大部分时间都在怀疑中。”
“怀疑是人类天生的弱点。”司祭又把那句话重复了一遍,“那您主要怀疑的是什么呢?”
“我什么都怀疑。我有时甚至怀疑上帝的存在。”列文不由地说了出来,并且因为自己失言感到惶恐。可是列文的话好像没有给司祭造成什么印象。
“怎么能怀疑上帝的存在呢?”司祭连忙带着微微的笑容说。
列文没有作声。
“您既然看得见万物,怎么能怀疑造物主的存在呢?”司祭用很快的、习惯的腔调继续说,“是谁用日月星辰装饰了天空?是谁把大地打扮得这样美丽?没有造物主怎么行呢?”他带着询问的神气看了看列文,说道。
列文觉得同司祭争论哲学问题是不相宜的,所以只能直接就问题进行回答。
“我不知道。”他说。
“您不知道吗?那您怎么能怀疑上帝创造了万物呢?”司祭带着快活的不解神气说。
“我什么也不明白。”列文红着脸说,并且觉得他的话是很蠢的,在这种场合下他的话不可能是不蠢的。
“您就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就连神父们也有过怀疑,恳求过上帝巩固他们的信仰。魔鬼是有很大力量的,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制服他。祷告上帝,恳求上帝吧。祷告上帝吧。”他又急忙说了一遍。
司祭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在沉思。
“我听说,您准备同本教区教民和忏悔者谢尔巴茨基的女儿结婚,是吗?”他又笑着说,“一个极好的姑娘呀!”
“是的。”列文替司祭红着脸回答说。他心想:“他为什么要在忏悔的时候问这事儿呀?”
于是,司祭就像回答他的念头似的,对他说道:
“您准备结婚,上帝就可能会赐给您子孙后代,不是吗?如果您不能战胜心中魔鬼的诱惑,魔鬼诱使您不信教,那会怎么样,您会给您的子孙什么样的教育呢?”他用很亲切的责备口气说,“如果您爱您的儿女,那么,您作为一个慈父,就不仅希望自己的孩子荣华富贵;您还要希望他们得救,希望真理之光照亮他们的心灵。不是吗?如果天真的孩子们问您:‘爸爸!这大地、水、太阳、鲜花、青草——我所喜欢的这世界上的一切,是谁创造的?’您又怎样回答他们呢?难道您能对他们说‘我不知道’吗?既然上帝大慈大悲,向您展示了这一切,您就不可能不知道。或者您的孩子们问您:‘人死后怎样呀?’如果您什么也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说呢?怎样回答他们呢?就任凭他们受尘世和魔鬼的诱惑吗?那就不好了!”他说到这里,就停下来,歪起头,用和善而亲切的目光看着列文。
列文现在什么也不回答,不是因为他不愿意和司祭争论,而是因为还没有谁问过他这样的问题;等他的孩子们将来问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有时间考虑怎样回答。
“您现在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司祭继续说下去,“这时候就应该选定道路,坚定地走下去。您祷告上帝,求上帝大慈大悲帮助您,怜悯您吧。”司祭结束道。又念起赦罪祷词:“愿我主上帝,耶稣基督,大慈大悲,饶恕这个儿子……”司祭念完了,又为他祝过福,便放他走了。
列文这天回到家里,心里觉得非常高兴,因为这种不舒服的状况结束了,而且是不用他说谎就结束的。除此以外,他心中还留下模糊的记忆,好像那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头儿说的话完全不像他开头所感觉的那样蠢,好像其中有些道理也是需要弄明白的。
“当然,不是现在。”列文想道,“以后再说吧。”列文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在他的心灵中是有不明确和不干净之处,感觉到自己对待宗教的态度也和别人一样,别人的态度他看得很清楚,很不喜欢,而且还因此责备过自己的朋友斯维亚日斯基。
这天晚上,列文和未婚妻一起在陶丽家里,心里特别快活。他在对奥布朗斯基说起他的兴奋心情的时候,说他快活极了,就像一条被训练钻圈儿的狗,终于领会了并且照着要求做了之后,就快活得汪汪直叫,并且摇着尾巴往桌子上和窗台上直蹦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