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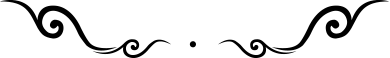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卡列宁忘记了李迪雅伯爵夫人,她却没有忘记他。就在这孤独绝望的难受时刻,她来看他了,而且不等通报就进了他的书房。她看见他的时候,他还是那副两手托着头坐着的姿势。
“我破坏了禁令。”她说着,快步走了进来,因为心情激动和走得很快,呼哧呼哧地喘着。“我什么都听说了!阿历克赛·亚力山大罗维奇呀!我的好朋友!”她用双手紧紧握住他的手,用她那若有所思的美丽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又说道。
卡列宁皱着眉头欠起身来,从她的手里抽出手来,推给她一把椅子。
“夫人,坐一坐吧?我不见客,因为我病了,夫人。”他说着,嘴唇也哆嗦起来。
“我的好朋友呀!”李迪雅夫人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又呼唤了一遍,忽然她的双眉靠里的一边扬起来,在额头上形成一个三角形;她那一张难看的黄脸变得更难看了;但是卡列宁觉得她是在为他难过,而且眼看就要哭了。他深深感动了,于是抓住她那肉嘟嘟的手,吻了起来。
“我的好朋友呀!”她因为激动,用断断续续的声音说,“您不应该一味地悲伤。悲伤是悲伤,但您应该把心放宽些。”
“我完了,彻底完了,我再也不能做人了!”卡列宁放开她的手,但依然望着她那泪水汪汪的眼睛说,“我的状况可怕,就因为不论在哪里,甚至在我自己身上,都找不到支持点。”
“您会找到支持的,您不要在我身上找,虽然我要求您相信我的友情。”她叹着气说,“我们的支持就是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爱。上帝是想到就做到的。”她带着卡列宁很熟悉的那种充满激情的眼神说,“上帝会支持您,保佑您的。”
尽管她这话里有陶醉于自己的崇高感情的成分,还有卡列宁觉得多余的、近来在彼得堡广泛流行的新的、狂热的神秘主义情绪,卡列宁现在听着这话还是很愉快的。
“我走投无路。我彻底完了。我一点没有料到,现在还是一点也不懂。”
“我的好朋友呀。”李迪雅又呼唤道。
“现在没有了,不是损失,不是的。”卡列宁继续说下去。“我不惋惜。可是我现在处境如此,见了人我抬不起头来。这很糟,可是我无可奈何,无可奈何呀。”
“我和大家都十分佩服的那种高尚的宽恕行为,那不是您,是您心中的上帝做出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十分激动地抬起眼睛说,“所以,您不能因为自己的行为抬不起头来。”
卡列宁皱起眉头,弯起胳膊,嘎巴嘎巴地扳起手指头。
“什么琐碎事儿都得过问。”他用细细的嗓门儿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夫人,我觉得自己的精力已经用完了。现在我整天都得操心,操心由于我的新的、孤单的处境而招致的(他加重语气说出“招致的”这个词儿)种种家务。用人呀,家庭教师呀,账目呀……这样小火小燎把我烤干了,我受不了啦。吃饭的时候……我昨天吃到一半差一点走掉。我儿子那样望着我,我真受不了。他没有问我这一切种种是怎么一回事儿,但他很想问,所以他那种眼神我真受不了。他怕看我,而且不仅如此……”
卡列宁想说说给他送来的那张账单,但是他的声音打起哆嗦,他不说了。他一想起那账单,想起那写在蓝纸上的女帽和缎带的欠款,不能不感到自己可怜。
“我明白,我的好朋友。”李迪雅伯爵夫人说,“我全明白。您不是要靠我帮助和安慰,不过我来就是要帮助您的,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但愿我能为您解除这些琐碎无聊的操劳……我明白,这需要女人家来管,女人家来操持。您能交给我吗?”
卡列宁默默地带着感激的神气握了握她的手。
“咱们一起来照料谢辽沙吧。我做事情不怎么行。但我要做做,我来给您做管家。您不要感谢我。我这样做并不是我自己……”
“我不能不感谢您呀。”
“可是,我的好朋友,不能老是怀着您说的那种心情,不能因为有过基督徒的高尚行为老是觉得抬不起头来,因为:‘谁谦让,谁是崇高的。’您也不必感谢我。应该感谢上帝,求上帝保佑。我们只有靠上帝,才能得到平安、安慰、拯救和爱。”她说过,抬起眼睛望着上天,卡列宁从她的默默不语中看出来,她开始祷告了。
卡列宁现在听她说话,她说的那些话,他以前即使不觉得讨厌,也觉得是没有意思的,现在却觉得很自然,很使人舒服。卡列宁原来也很不喜欢这种新的狂热精神。他是个信徒,主要是从政治意义上关心宗教,而新的教义是容许对宗教作一些新的解释的,这也就为争论和分析打开了大门,在原则上他对此是很反感的。以前他对这种教义很冷淡,甚至敌视,但和醉心新教义的李迪雅伯爵夫人从来没有争论过,而是沉默不语,尽量躲避她的挑战。现在他是第一次高高兴兴听她说话,也没有在心里反驳她的话。
“我非常非常感谢您,感谢您的行动,感谢您的话。”等她祷告完了,他说道。
李迪雅伯爵夫人又一次握了握好朋友的双手。
“现在我要动手做事情了。”她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就一面擦着脸上的泪痕,微微笑着说,“我去看看谢辽沙。不是万不得已,我就不来找您了。”她说过,就站起来,走了出去。
李迪雅伯爵夫人朝谢辽沙房里走去,在那里一面往吓慌了的孩子的脸上洒着泪水,一面对他说,他的父亲是神圣的,他的母亲已经死了。
李迪雅伯爵夫人说到做到。她确实承担了卡列宁家一切家务的安排和操持。不过,她说她做事情不怎么行,不是谦虚。她说的做法都必须变更,因为都行不通,所以都要由卡列宁的老仆柯尔尼来变通。柯尔尼现在悄没声地掌管起卡列宁家的全部家务,有什么需要向主人报告的,就在服侍他穿衣服的时候平静地、小心翼翼地报告一下。不过,李迪雅伯爵夫人的帮助还是起了极大作用的:她使卡列宁有了精神上的支柱,因为她使他意识到她对他的爱和尊敬,尤其因为,正如她一想起来就觉得安慰的,她差不多使他真正信起基督教,也就是说,使他这个冷漠的、不起劲儿的信徒变成一个近来在彼得堡广泛流行的基督教新教义的热烈而坚决的拥护者。卡列宁相信新教义是很容易的。卡列宁也像李迪雅以及另外一些抱有同样见解的人一样,完全缺乏深刻的想象力,缺乏那种精神力量,只有靠那种精神力量,想象出的想法才会非常实际,才能与其他一些想法、与现实相符合。比如他认为,死对于不信教的人是存在的,对于他是不存在的,又因为他有虔诚的信仰,他自己又能判断信仰的程度,那他的灵魂中是没有罪恶的,所以他在这人世上已经完全得救,——他就看不出这看法有什么不合情理和荒谬之处。
不错,卡列宁也模模糊糊感觉到他对自己信仰的这种看法是肤浅的和错误的,他也知道,如果他根本没想到他的宽恕是神力的驱使,而纯粹凭感情行事,那他会比时时刻刻想着心中有上帝,就像现在这样,签发公文也是奉行上帝旨意,更要幸福些。但是卡列宁必须这样想,他非常需要在屈辱中有一个崇高的、哪怕是假想的立足点,他这个人人鄙视的人就可以鄙视别人,所以他就抓住自己假想的救星当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