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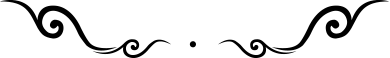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尼古拉·列文住的这一家省城旅馆,是按照新的改良式样,刻意讲求清洁、舒适甚至优雅的省城旅馆之一,但是由于过往旅客太多,很快就变成讲求时髦的肮脏酒店,而且就因为这样讲求时髦,比一般老式的、单纯肮脏的旅馆更糟。这家旅馆就是变成了这种样子;那身穿肮脏制服、在门口抽着烟卷、像是看门人的士兵,那锈出窟窿的又阴暗又难看的铁楼梯,那穿着肮脏燕尾服的大大咧咧的茶房,那餐厅和餐桌上落满灰尘的蜡制假花,那处处肮脏、灰尘和零乱,以及这家旅馆那种伴随着铁路而来的兴旺的紧张状态——这一切都使新婚不久的列文夫妇产生很不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旅馆的虚假华丽景象,和等待着他们的事极不协调。
照常问过他们要什么价钱的房间以后,才弄清楚,好房间一个也没有了。一个上等房间住了一位铁路视察,另一间住了一位莫斯科的律师,还有一间是从乡下来的阿斯塔菲耶娃公爵夫人占了。只剩下一个肮脏的房间,说是隔壁还有一个房间到晚上可以腾出来。列文很生吉娣的气,因为不出所料,他一来到,就在焦急万分地要看看哥哥病情的时候,却不能立刻跑去看哥哥,而不得不操心她的事。他生气是生气,还是领着妻子走进给他们开的房间。
“你去吧,去吧!”她用不好意思的、歉疚的目光看着他说。
他一声不响地从房间里走出来,立刻就碰到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她听说他来了,却不敢进他的房间。她还是他在莫斯科看到的那个模样;还是穿着那件毛料连衫裙,露着双臂和脖子,还有那张和善而呆板、多少有些发胖的麻脸。
“嗯,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了?”
“很不好。起不来了。他一直在等您。他……您……和夫人。”
列文开头一小会儿不明白她为什么发窘,可是她立刻让他明白了。
“我就走,我到厨房去一下。”她说,“他会很高兴的。他听见了,他在国外见过她,记得她。”
列文明白她说的是他的妻子,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咱们一块儿去吧,一块儿去吧!”他说。
可是他刚一举步,他房间的门就开了,吉娣朝外看了看。列文的脸红了红,因为又羞臊又生气,气的是妻子让他和她自己落到这样尴尬的地步。可是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脸红得更厉害。她缩着身子,脸红得要哭出来,两手抓住头巾角儿,用红红的手指头捻弄着,不知道该说什么和怎么办。
最初一刹那,列文在吉娣望着她很不理解的这个可怕女人的目光中,看出有一种急切的好奇神气。但这种神气一会儿就消失了。
“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她先问丈夫,接着又问她。
“总不能在走廊里说话呀!”列文说着,很恼火地回头看了看一位抖动着双腿、似乎因为自己有事这时从走廊里走过的先生。
“那您就进来吧。”吉娣对恢复了常态的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说;但是她发现丈夫脸上惊愕的神色,就又说:“你们还是去吧,你们先去,等会儿再叫我。”她说过,就回到房间里。列文就去看哥哥。
他所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哥哥的情形,是他怎么也料不到的。他预料他会看到的还是那种自我欺骗状态,他听说肺病病人往往是这样的,去年秋天哥哥去看他时使他感到吃惊的就是这种状态。他预料会看到那接近死亡的身体特征更明显,更虚弱,更消瘦,然而大体上还是那种样子。他预料,他自己因为可能失去亲爱的哥哥感到悲伤,感到死之可怕,还像上次那样,只是在程度上更厉害些罢了。他做好这样的准备;然而他所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样。
在一个又小又肮脏的房间里,描花的镶板上到处是唾沫痕迹,薄薄的隔板里面有说话的声音,在充满垃圾恶臭气味的空气中,在离墙放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盖着被子的人。这人的一条手臂放在被子上面,那一只大得像搂草耙一样的手令人不解地连在细细的、从顶端到中间一样粗细的长胳膊上。头侧歪着放在枕头上。列文看清了那两鬓上汗津津的稀稀的头发和皮包骨头的、仿佛透明的前额。
“这个可怕的人不可能是我的哥哥尼古拉。”列文心想。但是他走近些,看清了那张脸,就没办法再怀疑了。尽管这张脸出现了可怕的变化,列文只要一看到那一双看见他进来有了生气的眼睛,看出那嘴巴在黏糊糊的小胡子底下轻轻嚅动,就认清了可怕的事实:这个死尸般的躯体就是他还活着的哥哥。
一双发亮的眼睛带着严厉和责备的神气看了看进来的弟弟。通过这目光立刻明确了两个真正的人之间的真正关系。列文立刻感觉出他看他的目光中的责备神气,并且立刻为自己的幸福感到有愧。
列文拉住他的手,尼古拉笑了笑。那笑是轻微的,几乎看不出来,而且,尽管在笑,那严厉的眼神并没有改变。
“你没料到我会是这个样子吧?”尼古拉好不容易说出话来。
“是的……噢,不。”列文颠三倒四地说,“你怎么不早一点给我个信儿呢,就是说,在我结婚的时候?我到处打听你呢。”
必须说说话,才能不冷场,可是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尤其因为哥哥什么也不回答,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显然是想好好领会每句话的意思。列文告诉哥哥,妻子跟他一起来了。尼古拉显得很高兴,但说他怕他这个模样会叫她吓一跳。接着沉默了一阵子。尼古拉忽然动起来,说起话来。列文从他面部表情预料他要说的是特别重大、特别要紧的事,但尼古拉却说起自己的健康状况。他说医生不行,说可惜没有莫斯科的名医,于是列文明白了,他还抱着希望。
等说话一停,列文就站起来,希望摆脱一下难受的感觉,哪怕一小会儿也好,就说他要去把妻子带来。
“哦,好的,我叫人把这儿收拾干净些。我觉得,这儿又脏又臭。玛莎!把这儿收拾一下。”尼古拉很吃力地说,“等收拾好了,你就走开吧。”他补充一句,一面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弟弟。
列文什么也没有回答。他来到走廊里,就站住了。他本来说要把妻子带来,可是现在,他考虑到自己既然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决定反过来劝劝妻子,叫她不要去看病人。他心想;“何必让她也像我这样难受呢?”
“哦,怎么啦?怎么样?”吉娣带着惊惶的脸色问道。
“哎呀,这真可怕,太可怕了!你何必来呀?”列文说。
吉娣胆怯而怜惜地看着丈夫,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走过来,双手抓住他的胳膊肘。
“柯斯加!带我到他那儿去吧,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受些。你只要把我带去,把我带去,你就走开吧。”她说,“你要明白,看到你,却没有看到他,我更要难过得多。也许,我在那儿对你、对他都会有好处。请你让我去吧!”她恳求丈夫说,就好像她这一生是不是幸福全看这件事了。
列文只好答应。等他定下心来,也完全忘记了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之后,就和吉娣一起又朝哥哥的房间里走去。
吉娣迈着轻盈的步子,不停地望着丈夫,向他表露着勇敢和同情的脸色,走进病人的房间,便不慌不忙地转过身来,轻轻地把门闩上。她轻悄无声地快步走到病人的床前,绕过去,使病人不用转过头来,一下子就用她那柔软的玉手抓住他那干柴般的大手,握了握,就用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又怜惜又不伤人、又轻柔又带劲儿的语调和他说起话来。
“咱们在索登见过面,不过那时还不认识。”她说,“您没想到,我会做您的弟媳吧?”
“您恐怕认不出我了吧?”他仍然带着迎接她到来时的一脸笑容说。
“不,我认得出来。您能给我们个信儿,这有多好呀。柯斯加没有一天不想起您,不挂念您呢。”
可是病人的劲头儿没有维持多久。
她还没有把话说完,他的脸上就又出现了垂死的人嫉妒活人的那种严厉的责难神气。
“我怕您在这儿不太舒服。”她转过脸,避开他那凝视的目光,打量着整个房间说,“必须向老板另外要一个房间。”她对丈夫说,“还要离咱们近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