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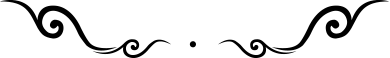
安娜和伏伦斯基为自己的朋友大发议论感到遗憾,早就在互相使眼色,终于,伏伦斯基不等主人指引,自己转身去看另一幅不大的画。
“哎呀,多美呀,美极了!真了不起!多美呀!”他们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是什么使他们这样喜欢呀?”米哈伊洛夫想道。他已经忘记了他三年前作的那幅画。他忘记了那几个月中日日夜夜全神贯注于这幅画时为这幅画经受的痛苦与欢乐,他总是这样,画好了,就忘记了。他甚至连看都不喜欢看,现在摆出来,只是为了等一个英国人来买这幅画。
“那不过是一幅旧的习作。”他说。
“多么美呀!”显然也陶醉于这幅画的魅力的高列尼歇夫说。
两个小男孩在柳荫下钓鱼。大的一个刚刚抛出钓钩,正在小心翼翼地把浮子从树棵子后面往外拖,一脸全神贯注的神气;另一个小些的躺在草地上,双手托着淡黄色乱发的头,一双若有所思的蓝眼睛望着水面。他想的是什么?
对这幅画的赞赏唤醒了米哈伊洛夫原来的兴奋心情,但是他害怕而且也不喜欢这种无谓的恋旧心情,所以,尽管他听了称赞十分高兴,他还是想带着来访者去看第三幅画。
但是伏伦斯基却问这幅画是否出卖。因为客人来访十分兴奋的米哈伊洛夫,这时觉得谈金钱的事是极不愉快的。
“摆出来就是要卖的。”他阴沉地皱着眉头回答说。
等来访者一走,米哈伊洛夫就面对着皮拉多和基督那幅画坐下来,在心里重温几位来访者说过的话,以及虽然没有明说然而却暗示过的话。说也奇怪,当他们在这里,当他用他们的眼光看待问题的时候,他觉得有些意见是很有分量的,现在他觉得顿时失去任何意义。他开始用纯粹艺术家的眼光来看自己的画,这才产生了信心,相信自己的画是完美的,因而是有价值的,他需要有这样的心情,才能不分散注意力,集中精神,只有集中精神,他才能作画。
基督的一只脚在透视上还是不对头的。他拿起调色板,画了起来。他一面修改那只脚,一面一再地注视后景中约翰的形象,那形象是来访者没有注意的,可是他知道那是完美无缺的。他修完了脚,就想再画画这个形象,可是他觉得自己太激动,没办法画。他在冷静的时候,无法作画;在过分感动,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时候,同样也无法作画。只有在从冷静到产生灵感这样的过渡时间里才能作画。今天他却是太激动了。他想把画盖起来,可是又停下来,手里拿着盖布,美滋滋地微笑着,对着约翰像看了好一阵子。最后他才依依难舍地用布盖上,带着疲倦然而幸福的心情朝家里走去。
伏伦斯基、安娜和高列尼歇夫在回家的一路上特别起劲儿,特别快活。他们谈着米哈伊洛夫和他的画。在他们的谈话中常常出现天才这个词儿,因为他们需要用这个词儿来说他们一点不懂却又很想说说的东西。他们认为这是与智慧和心灵无关的一种天生的、几乎是生理性的能力,他们就想用这个词儿来说明画家的一切所感所思。他们说,他的天才是不能否认的,但他的天才却因为缺乏教养不能充分发挥,缺乏教养是我们俄国画家共同的不幸。但是那幅两个男孩子的画却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他们一再谈到那幅画。
“真是美极了!他画得多么成功,多么自然呀!他自己也不明白,这幅有多么好。是的,不能错过,一定要把这画买下来。”伏伦斯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