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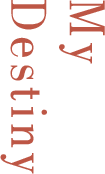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玉县的重点中学度过的。玉县起初只有一所重点中学,历史挺久了——是从前几名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创办的。据说他们中只有一人是贵州人,另外几个是外省人,有男有女。当年,他们毕业了,也就失业了。于是头脑一热,就在玉县办起了中学。不承想,一办就办成了。
贵州人就是我校长妈妈的亲伯父。那位亲伯父后来在南洋办的布匹蜡染厂很赚钱,没有他源源不断的财力支持,光凭几名联大学子的满腔热忱是办不成学校的。
解放后,那所中学便成了重点中学。从前没高中,后来有高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调出一部分老师创办了分校,叫“新重点”。
我考上的是“老重点”,它是全玉县中学的头牌,比“新重点”的录取线高十几分。
我毕业后才知道,我的分数并没达到,差七八分呢。但这一点属于学校机密,当时只有几位校领导知道。
我在中学时代开始如饥似渴地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我爸妈都不反对,只有一条要求,学习成绩不得出现排在前十五名以后的情况,一次都不许。我聪明,那对我不是件难事。我不属于那类“死用功”的刻苦学生,只要考前认真用功几天,成绩大抵会在前十左右。而这样的成绩,考高中时不论竞争多么激烈,爸爸妈妈都会保证我继续是“老重点”的高中生,正如保证我成为“老重点”的初中生那样。虽然他们从没对我这么说过,我却心知肚明。我与爸妈常能心照不宣。
我学习方面的聪明受益于什么?不再是学生之后我忆起往事,曾多次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这接近是自寻烦恼,但一个时期内它着实困扰过我。
颜值肯定与基因有关这一点毋庸置疑。父母相貌平平而儿女形象出众,这种为数不多的例子据说是隔代甚至隔了几代的基因优化组合的结果。很久以后生父何永旺告诉我,他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我生母的母亲也算得上清秀——那么我大姐是个农村美人自然有了遗传学方面的根据。
我问:“他们的智商呢?”
生父说:“你指的是聪明不聪明吧?据我所知,他们一点儿也不比同村的人强。”
这一结论曾使我大失所望。
我很想确证,我仅仅作为一个人的某一优点,是先天的普通的血缘给予我的,与后天我所一度拥有的优越外因毫无关系。连学习方面的聪明都不是生身父母所“给予”的,这使我一度暗自悲伤。
细细一想,我不得不承认,与其说我在学习方面有种天生的聪明,莫如说养父母教我的一些学习方法,使原本不聪明的我变得相当聪明。
校长妈妈曾点拨我:“学是接受老师教的知识,习是自我积累知识。比如老师讲一个新词,会强调其中某字在前边学过的词中是什么意思,在新词中又是什么意思,那么你明白了同一个字有两种意思。但实际上呢,也许不止两种,还有第三种第四种意思老师没讲。为什么呢?也许老师认为以后还会讲到那个字,也许连老师也不知道第三种第四种意思。不要以为重点中学的老师个个都知识渊博,那可不见得。有的重点中学老师,只不过是能将教材规定的内容教好罢了。超出教材的知识,自己很可能并没有。那应该怎么办呢?查字典啊!一查字典,连老师没教的知识也全面掌握了。习不仅仅是复习的意思,也包括培养自学的能力。”
那以后我完成作业时桌上总是放着字典。
我的养父也曾向我面授机宜。
他说:“数学考题本身没有任何意义,通过考题不断提高学生的推断能力才是意义。面对一道数学考题,头脑中立刻产生的解题方向如果简单,那就应首先排除开,因为简单失去了提高推断能力的意义。没有这种意义的考题,特别是一错扣十几分的大题,考试时大抵是不会出的。面对这类大题,不以简单的逻辑去推断,一般不至于犯解题方向的错误。不犯方向性错误,就不会浪费时间。”
养父的话对确保我的数学成绩每每名列前茅也至关重要。
我在中学时期不但读了不少书,还看了不少电影,我常是玉县上映的新片的首场观众。为了出现于某歌星的演唱会,我与班里的干部儿女多次到临江市去,不惜将周六、周日的时间消耗在江轮上。
“老重点”的学生不全是县里乡里的干部儿女,普通人家学习好的儿女还是占多数。我在小学时尚能与他们打成一片,成了中学生后,与他们不太合群了。相投的语言太少,共同爱好尤其少;互相交谈起来总是觉得隔着。即使我不愿那样对待他们,他们也较难做到不与我隔着,而且,与我打成一片对于他们似乎更难。结果一到初二,我的同学朋友就只是几名县里的干部儿女了,不久又多了一名乡长的女儿——据说她父亲要升为副县长了——最终却没升成,她就识趣地退出了我们那个小圈子。
我有了一辆崭新的紫色的女式自行车,“飞鸽”牌。当年“飞鸽”是名牌。自从有了自行车,我开始对县城进行“寻古探幽”。那时并无学习压力,我每天便还是有较多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我觉得逐渐长大是幸福的过程,我的这一过程没有任何方面的负担。我享受这一过程如同翅膀刚长硬的小鸟享受天空。我喜欢独自骑着自行车认街识巷,到处收集我对玉县的印象。
玉县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明代,但明代留给它的只剩一座小石桥和几段城墙的残垣断壁了。桥下缓缓流淌的是镜江的一股细小的支流水,穿城而过,又汇入了镜江。因是活水,水质颇清,两边是大石块垒的壁,却不高,也就一米半左右。镜江水大时,桥下的水也不会漫过两边的壁;而镜江水少时,桥下的水往往浅到一尺多点儿,终日有孩子踏着石阶下去捉小鱼小虾。大人从不担心他们会出事,因为水底是平的。那些残垣断壁开满了喇叭花,还有野兔出没,据说还有狐狸。我曾在那里见到过野兔,与狐狸却无一见之缘。
当时县城已经有了新区,建起了文化宫、体育馆、图书馆、法院、检察院和较大的电影院,是所谓“一宫二馆三院”重大项目的实现。也有了几排商品楼,相应地便有了柏油铺成的新路和路名。
县城老区却仍没有供机动车行驶的路,小街都不宽,小巷两边的人家往往隔着门窗聊天。街也罢巷也罢,路面都是古砖或石段铺成的,小孩子穿着家长用木板做的“鞋趿拉”跑过时,其声悦耳。当年在全国的大城市都实行“门前三包”,即包地面干净;垃圾在垃圾桶内;无积水或积雪。玉县没实行过“三包”,老区的小街小巷从来是干干净净的,没有积雪问题,也不会积水。雨过天晴,门前稍有积水,人们随即就会将水扫开,湿路面干得很快。谁家还没来得及扫,转眼对面人家就扫了。因为路面窄,所谓门前,几乎成了对门两家的公共之地。这家扫的次数多了,那家肯定过意不去,下次便抢先扫。除了几处设有垃圾桶,多数街头巷尾并无垃圾桶。即使街头巷尾可能也开着某家的门窗,设垃圾桶必遭反对,而且反对有理。所以每日清晨,会有人蹬着三轮垃圾车走街串巷将垃圾载走。中午晚上还收一次。一日三次,风雨无阻。几条商业街上的店铺皆无门窗,皆由落地木板区隔内外。晴日全卸,店内一览无余。阴天卸去多少,任凭店家的感觉怎样。家家如此,户户相同,看去便很单调。店家们为了避免单调,都在隔板上动心思,或用油漆画图案,或干脆刻出浮雕来。对我而言,那样的街特有逛头儿。
我家没有我时便有照相机了。我上中学后照相机基本属于我了。我爱上了摄影,满县城东照西照,用掉了不少胶卷。买胶卷洗照片是要花钱的,但我对钱没什么实际概念。
常常是我说“妈,又没胶卷了”,两三天后,我的床头柜上就摆着胶卷了。
如果我说欠照相馆的洗印钱了,我爸爸会对我妈争着说:“别别,你别掏钱包,轮也该轮到我给女儿一次了。”
不知怎么一来,我也快成县城的名人了。有些店家认识了我,我也欠过他们钱。有时我还忘了,店家自然不会忘,看到我母亲就会笑着告诉她:“你女儿还欠着这儿的钱呢。”
我妈妈也会赔着笑说:“这孩子,真不像话。”
她一回到家就会批评我:“你欠人家钱多不好呀,下次绝对不许啊。”
接着,会再给我些钱。
那两年我爸爸已住回到家里了。
临江市要在镜江上建一座大桥,桥的对面端要修公路,直通市里。那么一来,玉县和临江市之间就可有公交车畅行无阻了,不但缩短了距离,对玉县的发展也有极大的助力。这是省里的一个工程项目,由临江市具体落实,而临江市任命我爸爸为总负责人。
我每天都可以见到我爸爸了,我们父女之间的亲爱关系与日俱增,以至于我妈妈曾开玩笑地说:“我嫉妒了啊。”
爸爸常背着妈妈给我钱,还说:“别告诉你妈,你妈反对我也给你零花钱。”
而我则高兴地说:“遵命。”有时还会亲他一下。
钱真是好东西啊!
即使是亲生父女(那时我当然不会对这一关系有丝毫怀疑),父亲经常给女儿钱花,也会使女儿更爱他的。
我的中学时代不差钱,也没缺过任何东西。换一种说法就是,没见过大世面的小县城里的中学女生,我所希望拥有的只要不是超现实、超时代的东西,大抵可以得到。何况,我也没有多么强的拥有欲。往往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东西,我的叔叔、阿姨也就是爸爸妈妈的下属、同事、朋友也会当作礼物送给我,比如日本进口的游戏机、韩国的化妆品和从香港带回来的高级电子表——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那些东西。
由于爸爸住到家里了,家里的宾客日渐多了,多到我后来根本记不清他们谁是谁,只得免去姓氏,一律以叔叔、阿姨相称。我只能通过爸妈与他们的亲密程度来猜测,谁是爸妈的同事,谁是朋友,谁只不过仅仅是一般下属。再后来,我觉得这种判断接近无聊,也就不猜测。
家里收到的东西也渐多——有些是初次登门的人认为必须表示一下的那点儿“意思”;有些是年节相送的礼物;有些是爸妈和我的生日贺礼。总之,谁想送东西给别人,不愁找不到说辞,估计派专人来阻挡都难以挡住。而他们送的那股子真诚劲儿,常令爸妈不忍硬拒。更多的东西是烟酒茶,客人一走,爸妈就得商议再转送给谁。爸爸曾对外宣布戒烟了,而那也只不过使送烟的人少了。跑步机、健身器、按摩椅让妈妈派人搬到护校去提供给师生们用了;空调、风扇由爸爸派人拉到工地指挥部去了。
当年也没“八项规定”,只要不收钱,收什么似乎都不算“腐败”。在地方,腐败不腐败,是否属于正常“人情往来”也是一条线。
我见过妈妈面对一套看上去特高档的丝绸被褥和枕头发愁过,送的人的说辞是“该换季了”。
妈妈无奈地说:“这可怎么办?叫我如何是好呢?”
来不及转送或不宜转送的东西,有些年节日子里,几乎将我家小仓房堆满了。
贵州是水果种类较多的省份。一年四季,时令水果总是不断上市,我对水果餍足到一见胃里就返酸水的程度。成年后,我因而常常想到张家贵——就是那个为了使他和我大姐的儿女从小不必因看到水果而流口水,最终却锒铛入狱没做成我大姐夫的男人。
因而也多次想到“宿命”二字。
难道那是张家贵和我大姐的“宿命”?
校长妈妈曾对我讲过,她认为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这决定了人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和基因怎样,曰天命;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曰实命。生命生命,也指人在生活中所恪守的是非观,是生活与命的关系的组合词;三是文化给的,曰自修命。
她说:“文化”二字也是“以文化人”的组合词,不仅仅是指知识的有无或多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同时是人与文化的间接关系。某些人虽有知识,但文化上可能是糟糕的人。某些人文凭不高,却值得我们尊敬,引为良友。因为文化也在生活中,他们是善于从生活中吸收有益的做人营养的人,他们的实命使他们具有了某些做人的良好品质。良好品质体现在普通人身上,往往显得尤其可贵。不但是人的幸事,也是一国之幸……
不知为什么,那日校长妈妈有点“三娘教子”,欲罢不能,仿佛要将自己关于人何以为人,何以为好人的思考,一股脑儿都灌输给我。
我问她“宿命”是不是专指“天命”?
她立刻敏感起来,问我怎么知道了“宿命”一词?
我说我都是中学生了,读过的课外书不少了,知道也不足为怪呀。
她想了想,说我可以那么理解。
又想了想,接着说:“天命虽然是父母给的,但为此比爸比妈绝对是讨厌的社会现象,好文化是阻止这种现象蔓延的文化,反之,推波助澜是很垃圾的文化。因为自己的‘天命’优越而沾沾自喜,招摇人前的人不过是镶金边的人渣。同样,因为‘天命’不济而自哀自怜自暴自弃的人,是没搞明白何为生命之人。女儿,你要记住,真正可敬的人,是由实命和自修命所证明了的人!”
她说完,目不转睛地注视我,似乎要看出我对她的话明白了多少。
我小声问:“如果我注定了一生平凡,那可怎么办?”
她说:“那一点儿都不可怕,那就更要做一个好人。”
我想了想,忍不住又问:“都平凡了,做好人岂不是太难了?”
她沉默良久,思忖着说:“不平凡的人,往往万分甚至百万千万分之一二而已。平凡的好人,那也是百分之几的人啊。如果我女儿将来能成为百分之几的人,妈妈和爸爸就特别欣慰了。”
我对校长妈妈那日对我的教诲有点不明所以,因而印象也十分深刻。
我的初中时代不知不觉就优哉游哉幸福洋溢地过去了。
接着,我在临江市的重点中学开始了我住校的高中生活。
到临江去读高中,而不是继续在玉县的“老重点”升高中是我爸爸的主张。他认为我已经到了必须拓展成长视野,多接触新时代、新事物的年龄,仍滞留在玉县,对我的成长历练及将来的人生定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妈妈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而我也恰有此念。玉县虽也不错,而且正在变得现代起来,但毕竟是小小县城。它已再无吸引我的地方了,更无使我眷恋之处了。
爸爸妈妈的主张正中我下怀。
于是情况成了这样——每周回玉县探家的不再是爸爸,而是我这个住校的女儿了。大桥尚未落成,公路尚未开通,每周乘江轮往返一次,也是件累事。
我便向爸爸妈妈请求两星期回家一次,爸爸妈妈体恤地同意了。
实际上两星期一次我也没做到,一个月才回一次家的时候也不少。
爸爸妈妈从无怨言。
只是每次我回家那天,家里的气氛像过节,我感受到的可用“欢迎”二字形容。爸爸、妈妈和于姥姥从早到晚笑盈盈的,如同天使又下凡到了方家。于姥姥一直留在我家替我爸妈料理日常生活。我爸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无心过问生活之事。我妈在理家这件事上常常表现得弱智又无能。她无疑是好母亲、好妻子,却天生不是好主妇。家里离不开于姥姥,于姥姥自己也没家没子女,年轻轻丧夫,守寡守了一辈子。我爸妈对她好,每月给她一份她特别满意的工资,我家就等于是她的家了。
临江一中是全市唯一一所只有高中的中学。地区行署范围内各县领导的儿女、市领导的儿女、邻市某些领导的儿女,只要学习上还是那么块料,差不多都被一中吸纳了。
一般人认为,干部家的儿女,智商往往不太“灵光”——这实际上是流言。虽然流传又广又久,但那也是流言。起码在当年,在临江一中,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
临江一中的学生普遍用功,干部儿女也不例外。有的干部儿女在中学时就是班里的学习尖子,甚至是全校学霸。他们好像都有明确的人生方向,学习特自觉,根本无须任何人督促。互相的关系也淡淡的,不会多么好,却也都尽量避免将关系搞糟。并且,都特低调,一个个本能地“夹起尾巴做人”。对比起来,我不由得每每因自己从小学到中学那种“幸福外溢”的状态感到羞愧。有的同学看书也很多,他们谈起弗洛伊德、《时间简史》和《第三次浪潮》来,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插不上一句话——我从没听父母谈过那一类外国人名,家中也无那一类书。
有次在食堂吃饭,同桌的几名同学不知怎么谈到了文学,一个学兄忽然问我读过什么书?我想了想,回答了《悲惨世界》。
“啊,喜欢雨果呀。”
“改革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
“进步,才是人应该有的现象。”
另两名学兄随口背出了书中的两句话——我因为往小本子上抄过,所以知道是书中的话。
“别在学妹面前卖弄啊。学妹,也读过西蒙的小说吗?”
我怔怔地摇头。
“我除了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所开出的境界外,并不知道其他的境界为何……”
那位师姐自己也掉起书袋来。
“你这就不是卖弄了?打住,都打住,不许再谈文学,换个话题。”坐我旁边的学姐替我圆场。
我借口要添汤,端着碗起身,一去不返。
过后有同学告诉我,那几名学兄学姐已高三了,即将面临高考。他们都是校文学社的骨干,也都是一中的文学名人。
他们是不是名人我倒不感兴趣。读的小说再多,不也只不过是读者,而非任何一篇作品的作者?
但我对于他们还是不禁肃然起敬。想想吧,即将步入考场了呀,一个个居然还能那等地神闲气定、谈笑风生,内心该有多大的自信呀!读了那么多书,又能保证学习上跻身于优等生之列,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除了敬意,我内心也产生起从未有过的自卑来。
那一年,具体说是高一下学期,我感到学习上吃力了。用功再用功,也只保持住了全班中等成绩的名次。爸爸妈妈教我的学习方法,在临江一中根本不起作用了。
我第一次怀疑起自己的智商来。
我曾这样问爸爸妈妈:“你们希望我将来成为怎样的人?”
爸妈对视一眼之后,妈妈首先说:“女儿,妈妈对你只有一种希望,那就是将来做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女性。至于怎么为好,你懂的。至于你考什么大学,选什么专业,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都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的事,爸妈贡献些意见供你考虑,但绝不干涉。”
爸爸接着说:“我完全同意你妈的态度。你按自己的意愿去决定就是。别给自己预设什么高目标,非跟自己较劲地去实现。人没必要将自己的人生搞得那么紧绷,活得顺其自然也很好。总之,你幸福,你爸妈就幸福。”
爸妈对我的期许如此宽松,几无任何寄托,使我暗自庆幸,同时也难免有点儿不被重视的失落与沮丧。而他们的话是否是他们的真实想法,我就不得而知,也不想知道了。
的确,种种外因使我变得稳重了。似乎不仅仅是外因在起作用,有时候我觉得好像自己身体里也有某种属于生命本源的东西开始产生了——不,说产生不太恰当,它必定原本就存在于我生命的某一方面,起先处于“休眠”状态,由于受到外因的影响,开始“复活”了。
于是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从高二起,我蹿个儿了。到高三时,身高一米七三了。个子高了,腰显得更细了,胸部发育得更丰满了,想不那么挺都不可能。腿也不知不觉地变长了,这使我在校园里成了一名身材高挑的女生。不论穿裙子还是穿长裤,都可以用亭亭玉立来形容了。我的脸形也发生了变化,由苹果脸变成鸭蛋脸了。
这种变化使我暗自惊喜,也给我带来了几分困扰——因为我并不习惯有过多的目光投注在自己身上。那些目光首先来自男生,后来也包括了女生,再后来爸妈看我的目光也异样了。
妈妈欣赏地看我时绝不会使我感到不自在,相反那会使我十分愉快。
但我身体的变化似乎给爸爸带来了不便,他不怎么正眼看我了。在我面前,他似乎不知该将目光望向何处了。
所以我在家里不再穿裙子了。
只有于姥姥对我身体的变化毫不掩饰她的高兴。
“你这孩子,天这么热,在家穿什么长裤呀!连我看着都替你热,快换上裙子,穿最短的那条!”
她这么说时,我一笑而已。
在临江一中,我默默无闻,成绩一般。我稳重,不是装稳重,而是再也活跃不起来了,想要活跃一下的生命动能似乎消失了。没有男女生关系的任何闲言碎语,更没有恋爱经历。
唯一使我欣慰的是自己身体的变化,但这种欣慰是只能内敛于心的。因为一名来自小县城的学习成绩一般般的女生倘若得意于自己的身材怎样,那是肯定会被同学所鄙视的。
我的高中阶段就像镜江,波澜不惊。
但有一件事使我受到了情感重创——在我高三下学期时,于姥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我妈妈对于姥姥很好,于姥姥对我妈妈也非常关爱;若我妈妈接连病了几天,她往往会急得上火——但她们的关系不是母女关系,一向只不过是两个年龄不同的好女人之间的关系而已。往根子上说,是好雇主与好女佣之间的关系。
但我与于姥姥的关系却不同。
尽管我没吃过她的一口奶,但我可是她一天几次用奶瓶喂大的啊!吐了拉了尿了这类一天多次的事,可一向是她的事而不是我妈妈的事。夏天怕我生疹子,每天晚上都为我洗一遍澡擦一遍爽身粉的也是她而不是我妈妈。我小时候家里既没电扇也无空调,为了使我睡足睡好,姥姥经掌手拿蒲扇坐我床边轻轻扇啊扇的,有时自己也困得一边扇一边打起盹来。如果身体确有记忆,那么我的身体对于她的怀抱的记忆肯定深刻于对我妈妈怀抱的记忆——实际上小时候我更愿让于姥姥抱我;胖胖的于姥姥的怀抱那么舒服,那么温暖,给我以更大的依恋感。由妈妈抱着我往往好久才入睡,由于姥姥抱着,我不一会儿就睡着了。
现在我写到她时,笔下出现的虽是“于姥姥”三个字,但在当年,对于小时候的我,她就是亲爱的姥姥。我会说话以后,口口声声对她叫的也是“姥姥”,而不是“于姥姥”。她的死对我而言是第一位亲爱者的死,对我的情感打击远大于我的情感承受力,以至于我都不愿回家了,因为一迈入没有了姥姥的家门就禁不住流泪。即使眼中未流,心也在流。
我原本是要考我父亲的母校贵州大学的,却没考上。
我考上的是贵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我入校后,它改为师范大学了。
我承认,姥姥的死,影响了我的备考状态。
我对此毫无怨言——姥姥怎么可能为自己的死选择时日?
而我,觉得自己将来不管在哪儿当中学语文老师,那样的人生已挺好。能留在贵阳当然符合我的理想,去往临江也行,回到玉县也还行。
不知为什么,我对人生的理解,对所谓幸福的追求,一下子变得特现实了。简直也可以说,我变成了一名没有人生之梦的大学女生——在大学生无不有梦的年代和我最该有梦的年华。
这一点似乎也与姥姥的死有关。
既然谁都难免一死,那么对所谓幸福的孜孜以求的追求,是否也等于是对过眼烟云的专执一念?
放下便如何?
顺其自然又有何不可?
某些人的不幸恰在于连这样选择的“资本”都没有。
而我方婉之是有的呀。
我承认那时的我人生态度比较消极,而这使我更加稳重。
我稳重得不太与人交心了。
而这使我给人以“深沉”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