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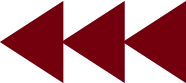
现在,让我们对前面三章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在王国的中心,一个机构掌管全国行政,一位大臣承揽全国事务;在其他省区,一个官员统领全部事宜,除了获得批准方能行事的部门外,没有任何附属行政机构;一种特别法庭审理所有与政府有关的案件,并保护所有政府官员免受法律问责。
这不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中央集权吗?虽然在很多方面它不如今天这般明确、规范及稳定,但其本质全然一样。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央集权未曾再增添或减少其他什么重要内容,只要把它周围的东西除去,就会发现它从来没有变过的本来面目。 [7]
对于我刚刚描述的这种制度,后来的模仿者数以百计,但在那个时代,这些特征都为法国所独有。很快,我们就将看到这些特征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后果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在旧制度的废墟中,新制度是如何在法国确立的?
这项任务需要耐心、智慧与时间,仅靠武力和权力无法使其成功。在大革命爆发时,与其说法国旧制度的大楼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破坏,毋宁说人们是在其已有的基础上建造了新的大厦。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旧制度下的政府是依照某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来进行这项艰巨的任务的。推动政府这样做的是一种本能,这种本能会引诱任何政府去获得可以掌控一切的权力,尽管政府及其官员不尽相同,但这种本能却不曾改变。那些属于封建制度的古老称谓与荣誉被完好地保留下来,但其实际权力却被慢慢蚕食殆尽;人们仍保留着自己的地位,但已被引离权力的核心。这种追求权力的本能利用这些人的懒惰与自私,悄悄占据他们的位置;它对旧制度中的一切弊病不仅不予纠正,反而利用并取而代之。最后,所有的旧势力几乎都被清除干净,总督成为唯一的政府代理人,而总督这个头衔,在旧制度诞生之初还不曾存在。
司法权是挡在中央政府掌控一切权力面前的唯一障碍,不过对此,它也最终掌握了权力的实质,并只给它的反对者留下一道权力的虚影。中央政府并未将高等法院从行政领域里排除,相反将它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并使自己的势力在其中不断扩大直至几乎全部占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饥荒时期,法官们的雄心会被激愤的民众唤醒,中央政府便会做顺水人情,让法院暂时管理一些事务,以此引发一些风波,使之在历史中回荡。不久之后,中央政府便会悄无声息地再次将暂存于法院的权力收回,并暗中重新把所有的人及案件控制起来。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高等法院针对王权的反抗与斗争,我们就会看到其内容基本集中在政策制定而非政府行政方面。双方争执的焦点往往是新的税法,由此可见法院与政府争夺的并不是行政权,而是立法权,尽管两者对此都无权占有。
这种斗争随着大革命的不断临近而越发频繁。民众的愤怒逐渐过激,高等法院因而更多地插手政治领域;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和它的代理人在处理事务的经验与技巧方面也越来越丰富而老练。高等法院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与其称之为行政机构,不如说它像古罗马时期的保民官。

即便到大革命结束后,法国新政府仍保持着旧政府独揽大权的做法。
时代的发展不断为中央政府拓展新的行政领域,而缺乏灵活性的法院完全跟不上政府的脚步。无先例可循的新案件层出不穷,法院对此已无能为力。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亦在不断地创造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需求对中央政府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新权力,因为除了它,没有任何其他机构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就行政范围而言,法院总是固定不变,而政府则是灵活多变,并且后者还会随着文明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大革命爆发在即,法国人的精神世界开始地震般地震颤,无数的新思想从中迸发并广泛传播,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央政府。在中央政府被大革命推翻之前,它与它相关的事物都在不断地完善和进步,这一点在中央政府留下的档案资料中显得尤为突出。同样是总监与总督的职务,在1740年和1780年这两个时间点,已有了天壤之别——政府已被改造一新。政府官员的职务未变,但他们的精神已不同于过往。随着政府的管理领域不断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而开明;其管理手段也变得更加温和,压迫逐渐转变为引导。
大革命最初的功绩是摧毁了这个庞大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后者于1800年又死灰复燃。虽然人们常说1789年的行政原则在当时及后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事实恰恰相反,取得胜利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并自那时起一直存留至今。
旧制度的这些内容是如何完好无损地与新社会融为一体的?如果有人这样问我,我将回答:中央集权从未被大革命摧毁,相反,中央集权正是大革命的根本与特征。我还要进一步补充说,人们在摧毁贵族统治的同时也将自己推向了中央集权。对于这样的趋势,推动要比抑制容易得多。当所有的权力都倾向于统合为一时,只有强大的腕力才能使其保持散乱。
民主革命确实摧毁了很多属于旧制度的体制,但它巩固了中央集权,所以在这个由革命造就的新社会中,中央集权很自然地找到了属于它的位置,而人们也心安理得地认为它是大革命的伟大成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