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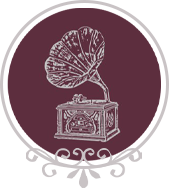
从技术上来说,女性口述历史和男性口述历史并无不同,都在为人类书写历史;但在访问内容上却有分殊,访问女性如同访问不同的专业人物一样,必须掌握专业人物各自的特性,因此主访人应针对受访人的特性进行访问,不能采用如出一辙的访问方式。据此,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首先,主访人的态度是否应具性别意识?或以女性主义的观点从事访问?过去的主访人较少思考性别问题,随着女性主义的日益盛行,这个问题变得相当重要。我个人并不反对主访人具有女性主义的观点;不过,我通常较喜欢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说法。事实上,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观点”或“站在女性立场”都是访问女性应有的认知,也唯有具备性别意识才能确切掌握女性受访人的情境。以访问女性工作者的待遇为例,除了解受访人的薪资与升迁情形之外,应进一步关心与女性工作权益有关的法规,例如服务机构是否订有单身或禁孕条款等,这就是有性别意识的访问方式。重要的是,借此始能凸显女性受访人的特性。
以我访问的女教育家邵梦兰为例,她的一生都奉献在教育事业上,病逝前,还在东吴大学兼课。她曾告诉我:“我将教到倒下为止。”对教育的这份挚爱,很自然地成为她述说自己生命史的重点,也因此,她的历史和男性没有两样。再加上,五四时期不断倡导把“女人当作人”的说法,在邵女士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但她的父亲、公公不把她当成女人,她在事业上受到毁谤、中伤时,她本人更不曾以女人这个标识,去博取同情,反而以公正不阿、不屈不挠的态度迎战。


图1 邵梦兰女士于士林中学校长任内,在校庆时演奏古筝
然而,这并不表示邵女士缺乏女性特质,当我跳脱她的事功,从女性立场切入,结果我看到她另外的一面。例如,生下头胎之后,邵女士在家当母亲或回上海升学之间,陷入天人交战,因舍不得离开孩子,每次为孩子喂完奶,她便哭泣,最后是头也不回地走,怕的是“不马上走的话,又走不了了”。
 这种乍似无情、却是有情的表现,是女性面对家庭与学业/事业抉择时的不得已。此外,邵女士的母爱张力,在她与学生的互动中,始终展露无遗。因此,如果在访问女性时,忽略了女性特质或者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我们很可能失去访问女性的意义。
这种乍似无情、却是有情的表现,是女性面对家庭与学业/事业抉择时的不得已。此外,邵女士的母爱张力,在她与学生的互动中,始终展露无遗。因此,如果在访问女性时,忽略了女性特质或者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我们很可能失去访问女性的意义。
其次,访问女性应偏重哪些内容?由于家庭生活占据女性生活的大半,因此站在女性立场从事访问,不免会出现一些与个人事功或国家、社会无关紧要的叙述,特别是受访者本身若仅是一般家庭主妇,访问的内容容易趋于褊狭。然而自另一角度来看,这类口述材料却是家庭史研究的最佳素材;同时,借由这类口述可以记录到生育文化、养生之道、家政技艺、理财或消费观念等,又能为经济史、文化史或医疗史提供丰富素材。此外,我个人的经验是,即使受访者是具有专业长才的女性,访问的方式也不应局限在专业技术或活动上,她们的婚姻或居家生活也可一并关心,我访问罗东地区早期的女名医陈石满女士时,便发现陈女士的医疗工作固然十分忙碌,治家之道并不亚于一般妇女,例如在挑选奶妈或采买蔬菜方面,她自有定见。
 因此,如果不站在女性的角度进行访问,是无法窥得女性历史的全貌的。
因此,如果不站在女性的角度进行访问,是无法窥得女性历史的全貌的。

图2 1933年,陈石满女士成为罗东地区第一位女医师
最后,访问女性是否应凸显父权宰制的观念?无可否认的,为女性设身处地的访问方式,可以让女性受访人畅所欲言,不过,刻意以父权宰制、两性不平等一类的话题来引导受访人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访人都具有女性意识,也不是所有的女性受访人都曾有父权压迫的经验;另一方面,这类话题易误导受访人的回忆,致使部分受访人失去自觉,导致出现“以今论古”的情形,这样的答案尽管符合主访人的期待,却不是受访人当时的实际感受。
 例如,日据时期台籍男女教师薪资的不平等是一项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根据我的访问,有些受访的女性教师并不认为这样的待遇不公平,因为她们指出当时女性教师多半不是出自正统的师范学校,薪资有别是理所当然。
例如,日据时期台籍男女教师薪资的不平等是一项众人皆知的事实,但根据我的访问,有些受访的女性教师并不认为这样的待遇不公平,因为她们指出当时女性教师多半不是出自正统的师范学校,薪资有别是理所当然。
 又如,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但邵梦兰的口述却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她的父亲非常重视女权,不仅创办东陵女子小学,还反对女儿缠足,并为邵家女子争取宗祧继承权。
又如,一般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普遍存在着“重男轻女”的观念,但邵梦兰的口述却给了我们不一样的答案,她的父亲非常重视女权,不仅创办东陵女子小学,还反对女儿缠足,并为邵家女子争取宗祧继承权。
 还有,当邵女士的祖母担心,邵梦兰会因大脚而嫁不出去时,她的父亲却说:“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
还有,当邵女士的祖母担心,邵梦兰会因大脚而嫁不出去时,她的父亲却说:“嫁不出去,就娶一个进来!”
 换句话说,主访人应让受访人回到她的时代,叙述当时的情境,如此一来,始不乖离历史。
换句话说,主访人应让受访人回到她的时代,叙述当时的情境,如此一来,始不乖离历史。

图3 邵梦兰女士的父母
从受访女性是否受父权宰制这点又可发现,有的主访人为突显这种概念,着眼悲情或受难女性的访问,易使读者误将女性史视为女性牺牲史。事实上,悲情女性也有她们不悲情或足以傲人的一面。例如我访问日据时期的台湾女工时,发现有的女工虽然来自贫困家庭,但因工作表现良好,她的家人或家族先后通过她的援引进入同一工厂,这不但改善了家庭生活,也使她深受家族敬重。
 更重要的是,受访人本身并不因曾为家庭牺牲而自苦。因此,我认为主访人千万不要以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附会。
更重要的是,受访人本身并不因曾为家庭牺牲而自苦。因此,我认为主访人千万不要以个人的价值判断强加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