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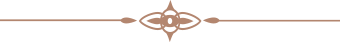
1979年,杰夫·康诺顿第一次见到乔·拜登。拜登那年三十六岁,是美国参议院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参议员。康诺顿十九岁,是亚拉巴马大学的一名商科学生。他的父母住在亨茨维尔,父亲为陆军导弹司令部当了三十年的化学工程师,而在这之前,父亲曾在陆军航空部队服役,在欧洲、中国和日本执行了四十七次飞行任务,后来受惠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就读塔斯卡卢萨的亚拉巴马大学,之后做过时薪一美元的伯明翰钢铁厂工人,在阿肯色州的家具厂和全国流动石膏厂待过,最后终于进入战后蓬勃发展的国防工业。从事小型火箭推进器生产是一份不错的中产阶级工作,每年最多能赚五万五千美元,有联邦政府和冷战为之担保;不过,康诺顿夫妇都出身贫寒。杰夫的父亲曾目睹自己的父亲在1932年跟随补助金大军前往华盛顿特区抗议
 。杰夫的母亲来自亚拉巴马州唐溪镇,童年时曾与姐妹一起在祖母家的农场里摘棉花,以熬过艰难时期。她五岁时攒了五分钱,打算为母亲买一份生日礼物。有一天她病了,高烧四十度,当运冰车路过门外,她的母亲想要买一块冰来为她降温,她拒绝了,因为全家只剩下她的五分钱。杰夫一直觉得,如果有一天自己会竞选公职,那一定要讲讲这个故事。
。杰夫的母亲来自亚拉巴马州唐溪镇,童年时曾与姐妹一起在祖母家的农场里摘棉花,以熬过艰难时期。她五岁时攒了五分钱,打算为母亲买一份生日礼物。有一天她病了,高烧四十度,当运冰车路过门外,她的母亲想要买一块冰来为她降温,她拒绝了,因为全家只剩下她的五分钱。杰夫一直觉得,如果有一天自己会竞选公职,那一定要讲讲这个故事。
康诺顿一家的选票并不一致。杰夫的母亲记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来到唐溪镇为惠勒大坝剪彩的那天,所有孩子都跑到车站,在一片安静肃穆中望着总统被人从火车上抬进车里。她一生都会投给民主党。杰夫的父亲战后在亚拉巴马第一次投票,他问该怎么做,票站工作人员说:“投给公鸡图案下面的人名就行啦。”那是亚拉巴马州民主党的标志,当时只有他们有足够的影响力。就在那一刻,康诺顿先生成了一名共和党人,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始终如一,而其他的南方白人也很快跟他一致。然而多年以后,当杰夫来到华盛顿为拜登工作,自称为职业民主党人时,他的父亲投给了克林顿——甚至投给了奥巴马。那时,住在他们那个城郊的所有人几乎都是忠实的共和党人,有人从康诺顿家的前院里偷走了奥巴马-拜登的标牌。康诺顿先生是在为自己的儿子投票。
杰夫·康诺顿个头矮小,一头棕发,聪颖勤奋,终生怀有亚拉巴马男孩身上特有的自卑情结。成长过程中,他不曾有过清晰的政治观念。1976年,他被罗纳德·里根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鼓舞:“在民主党对这个国家的统治下,自由已经遭到侵蚀。”1979年,吉米·卡特诊断美国患上了“信心危机”,警告“我们中有太多人崇尚自我放纵和消费”,康诺顿在《塔斯卡卢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为这番被称为“痼疾演讲”的讲话辩护。在搬到华盛顿之前,他一直是一名摇摆选民;他也对肯尼迪家族心怀敬意。1994年有一回,他在希科里希尔参加了凯斯琳·肯尼迪·汤森德的筹款活动,埃塞尔和其他肯尼迪家族成员在庄园前的草坪上友善地欢迎每一位客人。
 康诺顿溜进了书房,他本不该去那里。他从书架上拿下一卷罗伯特·F. 肯尼迪演讲的合订本——原始版本,上面还有手写的笔记。康诺顿的目光落在了一句话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肯尼迪划掉“应该”,改成了“必须”。康诺顿仿佛捧着《圣经》。这是他对政治最早的认知:伟大的演讲、历史性的事件(暗杀)、椭圆办公室和玫瑰园里的JFK黑白肖像。他是华盛顿的年鉴中被人忽视却不可缺少的一环,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罗森克兰茨
康诺顿溜进了书房,他本不该去那里。他从书架上拿下一卷罗伯特·F. 肯尼迪演讲的合订本——原始版本,上面还有手写的笔记。康诺顿的目光落在了一句话上:“我们应该做得更好。”肯尼迪划掉“应该”,改成了“必须”。康诺顿仿佛捧着《圣经》。这是他对政治最早的认知:伟大的演讲、历史性的事件(暗杀)、椭圆办公室和玫瑰园里的JFK黑白肖像。他是华盛顿的年鉴中被人忽视却不可缺少的一环,不是哈姆雷特,而是罗森克兰茨
 ,不是主角,而是追随者——多年之后,他会说:“我是个完美的二号人物。”他被公共服务和权力的浪漫所吸引,二者最终彼此纠缠、不可分割。
,不是主角,而是追随者——多年之后,他会说:“我是个完美的二号人物。”他被公共服务和权力的浪漫所吸引,二者最终彼此纠缠、不可分割。
1979年初,康诺顿大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朋友邀请他作为亚拉巴马州代表参加在费城举办的全国学生联会年会。机票要花一百五十美元。学生会拨给他二十五美元补助,《塔斯卡卢萨日报》愿意给他七十五美元,让他就自己的经历写一篇报道。最后五十美元来自一家温蒂汉堡的收款机,康诺顿每周会在那里吃几顿饭——那家店的经理听说这个大学生正在凑路费前往一个全国大会,而那个会议的目的是在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发生几年后消除校园中的冷漠、重建人们对政治的信心,他不禁大为感动。
费城这场会议的第一个发言者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众议员,他来自伊利诺伊州,名叫丹·克兰。在美国人民选出的代表中,有千千万万人在华盛顿完成了任期却没能留下痕迹,他就是其中一个。第二个发言者就是乔·拜登。他如此开场:“如果说克兰代表刚刚给了你们自由主义者的观点,那么接下来就是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你们都被捕了。”这句话引发了哄堂大笑。康诺顿对接下来的演讲内容毫无记忆,却对这位演讲者印象深刻。拜登年轻风趣,他知道该如何对大学生讲话。康诺顿永远无法忘记那一刻。
回到塔斯卡卢萨,康诺顿建立了亚拉巴马政治联盟。在秋季的第一场活动里,他邀请了拜登和来自犹他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克·加恩,请两人就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
 展开辩论。两位参议员都接受了邀请(1979年尚无规定禁止他们接受大学提供的五百美元酬金,只有一项限制:参议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五万七千五百美元工资的百分之十五,这项规定从当年1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加恩退出了。原本计划的辩论最后只能变成一场演讲。
展开辩论。两位参议员都接受了邀请(1979年尚无规定禁止他们接受大学提供的五百美元酬金,只有一项限制:参议员的额外收入不得超过其五万七千五百美元工资的百分之十五,这项规定从当年1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加恩退出了。原本计划的辩论最后只能变成一场演讲。
康诺顿跳进了他的雪佛兰,随行的还有从杨百翰大学过来的一个朋友,他跟加恩一样都是摩门教徒。他们驱车十四个小时赶往首都,试图说服加恩参议员改变决定。康诺顿从来没去过华盛顿,环城快道上并未明确标出通往城市的出口——与其说是通道,不如说它更像是一条护城河——国会大厦穹顶一直在远方时隐时现。最后,他们终于摸到了通往国会山的小路。那里是贫穷的、黑人的华盛顿,枯萎的华盛顿,属于八成民众的华盛顿。后来,康诺顿在这座城市居住和工作的二十年里,几乎再也没见过华盛顿的这一面。
早上,他们在拉塞尔参议院大楼找到加恩的办公室,它位于其中一条高挑幽深的走廊中一扇令人生畏的高大桃花心木门后面。因为康诺顿带了一位犹他州的摩门教徒,他获得一次事先未安排的会面机会,在等待室里见到了参议员本人。但他没能改变加恩的决定——在辩论当天,加恩已有另外一项安排。于是,康诺顿和摩门朋友离开了办公室,在拉塞尔大楼里逛起来——看到那白色的佛蒙特大理石、康科德花岗岩、黑色的桃花心木,感受到两党当时仍完好无损、壁垒森严、制度性的体面,这两个年轻的外地人感到自己十分渺小。不过,那份体面很快会出现裂缝,随后将一触即溃。他们想要找一名共和党参议员当替补,但走廊几乎空无一人,有一种不太民主的安静,康诺顿也根本不知道随便一个参议员长什么样。他也许瞥见了霍华德·贝克、雅各布·贾维茨、查克·珀西或巴里·戈德华特。
 民主党人里,休伯特·汉弗莱刚刚去世,但埃德蒙·马斯基仍在,弗兰克·丘奇、伯奇·贝、盖洛德·尼尔森和乔治·麦戈文也在。
民主党人里,休伯特·汉弗莱刚刚去世,但埃德蒙·马斯基仍在,弗兰克·丘奇、伯奇·贝、盖洛德·尼尔森和乔治·麦戈文也在。
 他们很快将被扫地出门。
他们很快将被扫地出门。
突然传来一声蜂鸣,走廊里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群头发灰白、气宇轩昂的高大男人。康诺顿和他的朋友跟着他们走进电梯(那个戴着苏格兰圆扁帽的小个子日本男人不是早川一会
 吗?),下到地下室,搭上在拉塞尔和国会大厦之间往返耗时三十秒的电动车。泰德·肯尼迪
吗?),下到地下室,搭上在拉塞尔和国会大厦之间往返耗时三十秒的电动车。泰德·肯尼迪
 就在大步流星地迈向下一趟车的参议员中,他被认出后露出微笑,康诺顿的朋友走上前去跟他握手。至于康诺顿,他太过敬畏,以至于动弹不得。(公众还不知道,当时肯尼迪正准备在1980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挑战现任总统卡特:正是拜登在1978年初头一个警告了卡特,肯尼迪正打算挑战他。)
就在大步流星地迈向下一趟车的参议员中,他被认出后露出微笑,康诺顿的朋友走上前去跟他握手。至于康诺顿,他太过敬畏,以至于动弹不得。(公众还不知道,当时肯尼迪正准备在1980年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挑战现任总统卡特:正是拜登在1978年初头一个警告了卡特,肯尼迪正打算挑战他。)
康诺顿回到塔斯卡卢萨,没能带来一名能辩论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共和党人。这无所谓。9月,拜登身穿定制西装、打着红色领带出现在校园里,他风度翩翩,微笑时露出一口闪闪发亮的白牙;在Phi Mu姐妹会
 (康诺顿的女朋友也是其中一员)的晚宴上,他迷倒了满屋子可爱的女学生。那天晚上,杰夫作为拜登的助手坐在他身旁,此刻的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政治生涯。两百名学生来听拜登的演讲,学生中心被挤得满满当当。康诺顿介绍了拜登,然后在前排坐下。拜登走上讲台。
(康诺顿的女朋友也是其中一员)的晚宴上,他迷倒了满屋子可爱的女学生。那天晚上,杰夫作为拜登的助手坐在他身旁,此刻的他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政治生涯。两百名学生来听拜登的演讲,学生中心被挤得满满当当。康诺顿介绍了拜登,然后在前排坐下。拜登走上讲台。
“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们听说我是一个伟大的人。”拜登说,“没错,我是广为人知的所谓‘当总统的料’。”人群紧张地笑起来,为他的幽默感倾倒。“为什么这么说呢,今晚早些时候,我跟一群学生讲话时,他们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牌子,写着‘欢迎拜登参议员’,当我走到那个牌子下面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这位肯定就是被召唤的参议员吧
 。’”笑声更响亮了。现在,拜登吸引住了听众,他转向自己的话题,花了九十分钟清楚地解释削减美国和苏联核武器的重要性,反驳参议院中对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反对声音,全程没看一眼笔记。前一天,由于在古巴发现了苏联部队,谈判遭受了打击。“大伙儿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拜登轻声说道。他拿着麦克风走向观众,用手势示意他们身体前倾听他讲话。“那些部队一直都在古巴!”他大声说道,“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演讲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康诺顿站起身来,他想要走向拜登表示感谢,却无意间引发了全场观众跟着起立喝彩。
。’”笑声更响亮了。现在,拜登吸引住了听众,他转向自己的话题,花了九十分钟清楚地解释削减美国和苏联核武器的重要性,反驳参议院中对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的反对声音,全程没看一眼笔记。前一天,由于在古巴发现了苏联部队,谈判遭受了打击。“大伙儿听着,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拜登轻声说道。他拿着麦克风走向观众,用手势示意他们身体前倾听他讲话。“那些部队一直都在古巴!”他大声说道,“而且,每个人都知道!”演讲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康诺顿站起身来,他想要走向拜登表示感谢,却无意间引发了全场观众跟着起立喝彩。
一个校园保安开车送拜登回伯明翰机场,康诺顿一同随行。因为演讲,拜登看起来很疲倦,但他深思熟虑地回答了保安的每一个入门级问题(“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的区别是什么?”),仿佛是大卫·布林克利
 在向他发问。当康诺顿问拜登为什么他每天都要搭火车从威尔明顿去华盛顿,参议员冷静地讲述了1972年12月那场几乎害死他全家人的车祸。事故发生在他当选参议员之后一个月。“我的妻子和小女儿死了,”拜登说,“儿子们受了重伤。于是我留在医院陪伴他们。我当时完全不想做参议员了。但最后,我在儿子的病床边宣誓就职。我是一名参议员,但我每天都会回家陪伴儿子们。这么多年来,特拉华州已经习惯了我每天都会回家。所以我真的没法搬去华盛顿。”
在向他发问。当康诺顿问拜登为什么他每天都要搭火车从威尔明顿去华盛顿,参议员冷静地讲述了1972年12月那场几乎害死他全家人的车祸。事故发生在他当选参议员之后一个月。“我的妻子和小女儿死了,”拜登说,“儿子们受了重伤。于是我留在医院陪伴他们。我当时完全不想做参议员了。但最后,我在儿子的病床边宣誓就职。我是一名参议员,但我每天都会回家陪伴儿子们。这么多年来,特拉华州已经习惯了我每天都会回家。所以我真的没法搬去华盛顿。”
就在那一刻,康诺顿迷上了乔·拜登。他身上有悲剧,有能量,有雄辩口才——如同肯尼迪家族一样。拜登会对遇到的每一个人施展魅力,直到建立起某种联系,才会继续前行——姐妹会的女生,演讲的听众(许多学生参加演讲是为了拿学分),校园保安,以及那个邀请他来塔斯卡卢萨的大三商科学生。这就是一个想当总统的人所需要的特质和动力。他们在机场下车后,康诺顿请拜登在活页本上签名,“致杰夫和亚拉巴马政治联盟:请继续参与政治。我们需要你们所有人。”他知道,他会追随这个人进入白宫。对于进入白宫之后该做什么,他并不清楚,也不重要。关键在于进入那个房间,登上美国社会的顶峰。
从亚拉巴马毕业之前,康诺顿又两次邀请拜登(与数十名其他民选代表一起)前来进行有偿演讲,拜登每一次演讲前都会说同样的笑话,到第三次时,他的演讲已经价值一千美元。康诺顿最后一次送拜登到伯明翰机场时,他告诉参议员:“如果有朝一日您竞选总统,我会在您身边。”
他没有立刻前往华盛顿。他先是拿着拜登本人的推荐信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那是1981年,《时代》周刊发布了名为《追逐金钱》的封面故事,讲的是工商管理学硕士(MBA)风潮,封面图是一名毕业生,学位帽的流苏由美元制成。康诺顿从来都没有过多少钱,华尔街的吸引力与白宫不相上下。MBA的全部意义就是华尔街。就像去了华盛顿却进了内政部一样,如果拿到一个精英商科学位只是为宝洁公司或IBM工作,那就毫无意义了。在他的同学看来,如果谁找到的工作是在一个实业公司,那就等于落后于其他人。第二年快结束时,康诺顿飞到迈阿密去接受莱德卡车公司的面试,整个过程中他都在想,如果不是在迈阿密,如果不是为了在沙滩上待一天,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费心申请这家公司。在前两个学年之间,他已经在休斯敦的康诺可石油公司做了一份暑期工作,他们想让他回去开展一番事业,但他一想到初入职时年薪只有三万两千美元,还要每六个月在路易斯安那州的莱克查尔斯和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之间侧向移动一次,就觉得这跟在卡车公司工作一样悲惨。康诺顿来自飞越之地
 ——他并不想在那儿工作。如果他没能在所罗门兄弟或高盛这样的投行或是麦肯锡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
——他并不想在那儿工作。如果他没能在所罗门兄弟或高盛这样的投行或是麦肯锡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就会觉得自己失败了。
康诺顿没有忘记乔·拜登。在学校图书馆学习到午夜时,他会把金融书籍推到一旁,翻出《时代》周刊60年代的旧杂志,再次阅读暗杀的经过、杰克的总统任期和博比的崛起
 。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出现在那些黑白照片里。就连申请华尔街工作的时候,他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拜登的事业,还给他写了几封信来请求一份工作——不是给他的参议员办公室,或是给那个他稍微有些熟识的幕僚(他也许真的会回信),而是给拜登本人:“亲爱的拜登参议员,我即将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不知道,拜登的办公室只会回复特拉华州的信件,而他的信直接进了废纸篓。
。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出现在那些黑白照片里。就连申请华尔街工作的时候,他也一直密切关注着拜登的事业,还给他写了几封信来请求一份工作——不是给他的参议员办公室,或是给那个他稍微有些熟识的幕僚(他也许真的会回信),而是给拜登本人:“亲爱的拜登参议员,我即将从芝加哥大学毕业……”他不知道,拜登的办公室只会回复特拉华州的信件,而他的信直接进了废纸篓。
康诺顿在美邦公司的公共财政部门找到一份工作,起薪为每年四万八千美元;他在1983年夏天搬到了纽约。这正是在华尔街起步的好时机,如果康诺顿像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一样留下来,他也许已经攒下了一小笔钱。公共财政指的是州政府或地方政府的免税债券,这里赚钱不多,但很适合康诺顿;他在商学院申请文书里写过,他想要了解商业和政府之间的交叉点,并希望自己的事业能让他在两者之间往来。美邦当时承销了佛罗里达州的供水和排水系统债券,那里的城镇人口每隔几年就会翻番,需要筹措五千万到一亿美元用于基建项目。
合同成交后,公司会在曼哈顿的吕特斯餐厅举办耗费三万美元的奢华晚宴,提供豪华轿车,并向顾客保证不需要他们的州政府出一分钱:他们可以把在免税市场上筹到的资金拿来投资,利息比他们花在公共债券上的钱还要高百分之三,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把承销费用(包括晚宴花销在内)全部赚回来。康诺顿会告诉官员们:“我能给你们搞到音乐剧《猫》的前排座位,只要说一声就好,不需要你们的纳税人付一毛钱。”他们会犹豫,但几乎每一次,康诺顿都会在第二天收到一条电话留言:“我们改变主意了——我们想去看《猫》。”有一回,另一个银行家来到田纳西州杰克森县,对该县委员会解释说,银行收取的费用越高,县政府最后省下的钱就越多。房间后排有人拉长了声音说:“胡——说八道……”作为一个南方人,康诺顿相信,每当纽约的投资银行家来到南方说什么“我们能为你们省钱”,房间里就一定会有人回应“胡——说八道”。
康诺顿在上东区跟人合住一间公寓(公司出钱租的)。他每天早上9点半走进美邦在中城的总部,工作一整天,跟同事一起吃晚饭,然后回到办公室,加班直至深夜。跟身边那些在电脑上计算债券走势的极客相比,他并没有那么聪明,但作为一个南方人,他更风趣,还能跟曼哈顿的亚拉巴马女人打得火热。他从来没碰过毒品,一次也没有。(多年之后,当他受雇去白宫为克林顿政府工作时,将会在安全调查中被问到是否使用过毒品,康诺顿答道:“我等了一辈子,就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但他喝了不少波本,还有一次在“54工作室”酒吧跳了一整晚舞。从11月起,他的同事之间唯一的话题就只剩下年末奖金能发多少钱。
一年后,他转任去了芝加哥。他讨厌寒冷,想念南方,因此在1985年初放弃两万美元的奖金,跳槽去E. F. 赫顿公司在亚特兰大的办公室。几个月后,在一场规模浩大的空头支票诈骗丑闻中,公司承认曾实行两千多桩电报和信件诈骗。整个80年代,E. F. 赫顿一直在开出它无法负担的支票总额,并把钱在账户间挪来挪去,把资金当作无息贷款短期挪用,在流动中赚取了数百万美元。在华盛顿,归属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乔·拜登负责此案。他开始在电视上谈论华尔街如瘟疫般流行的白领犯罪,以及里根政府的司法部在监管这些罪行上如何失败。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说:“人们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及其管理者已经失效了,他们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尝试过如何有效地处理上层社会那些不合伦理、涉嫌违法的不端行为。”里根正处于低迷的第二任期,他的政府腐败泛滥,拜登则决定要去追逐大奖。
E. F. 赫顿公司认罪后流失了客户,公司开始被掏空,但康诺顿幸存了下来。随着他对这门生意愈发娴熟,他会独自飞到佛罗里达会见各市财务官。他甚至想出一个有销路的主意:各县市都有巨额养老金负债,为什么不拿去套利呢?发行一亿美元的免税养老金债券,利率百分之四,然后把这笔钱拿去投资,几年内就能获利百分之六到七。这是在欺骗美国纳税人。但一家债券公司给出了有利的意见(如果你能让一家法律事务所来告诉你这么做是合法的,那么这就是合法的——随着这些行为带来的利润呈指数级增长,律师们也变得愈发有创造力),他的老板——曾经也是一名债券律师——也对此十分满意。80年代,康诺顿搞懂了投资银行。玩弄税法只不过是一种钻空子的把戏罢了。
他二十七岁,当上了助理副总裁,年薪超过十万美元,然而每天晚上回到家里,他总会怀疑这并不是自己毕生想做的事。1986年底,拜登将要竞选总统已经显而易见。康诺顿永远无法忘记他。他拜托E. F. 赫顿的一名跟竞选活动有关系的说客帮他牵线。这次奏效了。
“拜登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邪教崇拜对象。”很久之后,康诺顿说,“他是我要追随的人,因为他就是我的马。我会骑着这匹马进入白宫。那将是我人生中的下一站。我已经通关了华尔街,接下来我要通关白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