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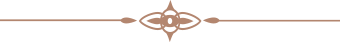
1987年,本该把华尔街银行家送往财政部高层职位的旋转门,只让康诺顿在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中获得一个初级职位,年薪两万四千美元。他把全新的标致换成父母那辆1976年的雪佛兰迈锐宝,因为他还不起车贷了。对他来说,这些都无所谓。
他还没离开亚特兰大就接到第一项任务:在佐治亚州找到二十个人,让每人为竞选活动写一张两百五十美元的支票。如果在二十个州里做到这些,候选人筹得的款项就达到能够获得联邦配套资金
 的标准。这是康诺顿做过的最困难的事,但对失败的恐惧激励了他,让他去请求自己在佐治亚认识的每一个人写支票。他成功了,在这一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筹款:不必说服所有人相信拜登能赢,甚至不必说服他们相信拜登在议题上是正确的——只需要说明你需要他们帮个忙。“为我这么做。”关键在于是谁在打这个电话。不过,当他询问曾经是Phi Mu成员、现在住在佐治亚的前女友时,她拒绝了:她辗转听说拜登“为了当总统宁愿出卖自己的祖母”。
的标准。这是康诺顿做过的最困难的事,但对失败的恐惧激励了他,让他去请求自己在佐治亚认识的每一个人写支票。他成功了,在这一过程中,他学会了如何筹款:不必说服所有人相信拜登能赢,甚至不必说服他们相信拜登在议题上是正确的——只需要说明你需要他们帮个忙。“为我这么做。”关键在于是谁在打这个电话。不过,当他询问曾经是Phi Mu成员、现在住在佐治亚的前女友时,她拒绝了:她辗转听说拜登“为了当总统宁愿出卖自己的祖母”。
这是里根卸任之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就像每一次竞选活动一样,拜登忙得一塌糊涂,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随时需要即兴发挥,一直在吃垃圾食物:我们不知道你正在做什么,但三天后请务必出席。3月,康诺顿在邻近华盛顿的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一个薯片商会官员的家里租了一个房间,但等他到了才被告知,他并不会在竞选团队的华盛顿办公室工作,而是会被派遣到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市郊外。“拜登当总统”竞选团队在城镇边缘一栋低档办公楼里占据了一间空荡荡的大型商铺,几十张办公桌散乱地摆放在蓝色地毯上。通往白宫的山路,要从不那么迷人的大本营起步。
康诺顿在佐治亚通过电话募集支票的成功事迹,意味着他将成为一名筹款人。这当然并不是康诺顿在拜登的塔斯卡卢萨演讲之夜所想象的政治,但他已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只要告诉我该去哪儿就行了。”他说。他得到了一张办公桌,开始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天从弗吉尼亚州单程通勤两小时,最后开始在办公室附近的戴斯酒店度过周二到周四的夜晚。
康诺顿在特德·考夫曼手下工作。考夫曼是拜登身经百战的幕僚长,身材瘦高,下巴尖细,头发蓬松浓密,如同埃尔·格列柯笔下的人物。考夫曼是拜登的心腹之一,当拜登的妹妹瓦莱丽把考夫曼介绍给杰夫时,她说:“你很幸运能为特德工作,他跟乔的关系太好了,他没什么需要担心的。”康诺顿真希望自己当时能镇定地问出这个问题:“有什么需要担心的吗?你能不能多说几句详细解释一下?”她话中的含义很清晰:“你跟特德不一样,你确实需要担心,因为你跟拜登没什么关系;拜登的王国中遍布地雷,有些标记了出来,有些则没有。”
考夫曼和康诺顿一拍即合。两人都是MBA,他们决定要像运营公司一样运营筹款活动。康诺顿帮忙起草战略方案,设计了一套由组长和副组长组成的金字塔结构组织。副组长筹集的资金越多,组长就能有越多机会接触到拜登。康诺顿记录着这场竞赛的进程,决定着谁能获得一枚胸针,谁又能与候选人共进晚宴。他还为捐款人也设立了一个系统。如果其中有人想见拜登,就得至少捐赠一千美元。康诺顿会告诉出手最大方的捐款人:“花上五万美元,你就能跟参议员在他家里共进晚宴。两万五千美元,你能跟参议员共进晚宴,但不是在他家里。”有些捐款人就会拼命多凑出两万五千万美元来,只为了能告诉朋友们:“我跟乔在他威尔明顿的家里共进晚宴了。”
加里·哈特被发现跟唐娜·赖斯在“猢狲把戏”号上举止不端,成为这一年里首位丑闻和媒体狂热的受害者
 。在那之后,拜登成了总统提名战中强有力的竞争者。康诺顿终日待在那间铺着蓝色地毯的宽敞房间里伏案工作,从不休息,直到半夜才开车回到亚历山德里亚,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第二天一早醒来再赶回威尔明顿,重复昨天的生活。他心想:“此时此刻,我正在实现我的目标。”
。在那之后,拜登成了总统提名战中强有力的竞争者。康诺顿终日待在那间铺着蓝色地毯的宽敞房间里伏案工作,从不休息,直到半夜才开车回到亚历山德里亚,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第二天一早醒来再赶回威尔明顿,重复昨天的生活。他心想:“此时此刻,我正在实现我的目标。”
那个春季里的一天,拜登来到威尔明顿的办公室。他穿着高领毛衣,戴着飞行员太阳镜,看上去神采奕奕。他跟竞选团队打了招呼——其中许多人从1972年就开始为他工作了,那年二十九岁的拜登第一次当选参议员——并就竞选进展做了一番简短的讲话来鼓舞士气。距离康诺顿上一次在亚拉巴马见到拜登已经过去六年,时间里填满了石沉大海的信件。就算拜登认出了康诺顿,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参议员准备离开时,康诺顿想象自己追上去站在他面前,告诉他:“我曾三次邀请您来到亚拉巴马大学。上一次,我承诺我会助您当上总统。现在,我来了。”然而他只是转身回到了办公桌前。
康诺顿步步攀升,他在南方城市的出庭律师与犹太人社区中策划了多场五万美元级别的筹款活动。他开始与拜登一同旅行,每当飞机延误,或是拜登抵达后的讲话太长或太短时,康诺顿就会替他挡住捐款人的不满。他和拜登从未交谈。
有一天,在去往休斯敦一场筹款活动的航班上,康诺顿被安排向拜登简单介绍活动内容。他拿着活动手册,穿过飞机过道,来到拜登和他妻子吉尔所在的头等舱。
“参议员,我能跟您谈一会儿吗?”康诺顿问。
“把你手上的东西给我就行了。”拜登说,他几乎头也没抬。
拜登显然不记得亚拉巴马了。康诺顿为他工作很久之后,这位老板会搞错他们最初的联系,说:“我很高兴多年以前你还在法学院时就能认识你。”拜登总会花时间跟陌生人相处,特别是当他们跟特拉华州有关时更是如此。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或者是像考夫曼一样长时间为他工作的心腹,如果你像参议员爱说的那样“流着蓝色的拜登之血”,那么他也会对你表现出强烈的忠诚。然而,如果你只是为他鞍前马后忙上几年,他会无视你、恐吓你,有时会羞辱你,对你的进步毫无兴趣,也永远不会记得你的名字。他会冲你叫“嘿,长官”或者“怎么样,队长”,除非他对你动了气,那时他就会使用他最喜欢的男性下属称呼:“操他妈的白痴”。“操他妈的白痴还没把我要的简介材料拿过来。”这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这个活动领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还是说你们太操他妈的白痴了连这也不知道?”
康诺顿所做的是艰难且必不可少的筹款工作,同时也得不到回报。为了这份工作,他遭受了永远的创伤,因为拜登痛恨筹款,痛恨它所带来的麻烦和妥协。拜登的同僚中,有些人似乎大半辈子都在打电话筹款——加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哪怕在健身房里骑室内脚踏车时也在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就为了筹得五百美元——但拜登几乎从来没给任何人打过电话。作为特拉华州参议员,他的整个州其实只有一些县那么大,从来不需要筹集多少钱;他一直没能适应总统竞选中的财务压力。他痛恨那些帮他筹款和为他写下支票的人对他提出要求,仿佛他无法忍受自己欠他们什么。在华盛顿,他从不跟固化的上层阶级打交道,而是每天晚上都会离开国会山的办公室,穿过马萨诸塞大道走向联合车站,然后搭火车回到威尔明顿的家人身旁。他一直是“普通人乔”
 ,这成了一种挑衅般的骄傲。他无法被收买,因为他不知感恩。
,这成了一种挑衅般的骄傲。他无法被收买,因为他不知感恩。
在华盛顿,民选代表认为自己更高等。他们是“负责人”,他们曾展现出勇气,忍受站在大众面前的羞辱;在他们眼里,幕僚是低等人类——依附于台前人士搭便车的寄生虫。康诺顿知道,他没有什么能教给乔·拜登的;拜登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已在政界摸爬滚打近二十年,对美国人想要的东西了如指掌。康诺顿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除非他能用埋头苦干来证明自己。
“他在我眼睛里看到了不确定。”康诺顿后来说,“我对这一切如此陌生。我曾在华尔街接受训练,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对我们的关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观念,因为我为了加入他的团队已经等待太久。而在他看来,我只不过是竞选团队中普普通通的一分子。我受到权力的吸引。我的头脑中并没有太多想法。我想要打入一个小团体,好在总统就职那天搬入白宫西翼,操控整个国家。这就是华盛顿的终极游戏。他的竞选失败之后,我迷失了方向。”
9月初,康诺顿从竞选活动中短暂抽离,观看了亚拉巴马州立大学-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橄榄球对抗赛。他正开车穿过宾州乡村,收音机里传来了一则新消息:拜登在艾奥瓦州的一次辩论中抄袭了英国工党政治家尼尔·基诺克的演讲,甚至还照抄了基诺克作为煤矿工人后代的身份。
如果只是个例,这个故事不会流传太远。但媒体已经搞垮了哈特——包括《纽约时报》的陶曼玲和E. J. 迪翁,以及《新闻周刊》的埃莉诺·克利夫特
 ——他们嗅到了另一桩丑闻,比赛着要挖出拜登的其他过错:从休伯特·汉弗莱和罗伯特·肯尼迪那里剽窃的语句;一篇有着糟糕脚注的法学院论文导致的成绩不及格;关于拜登过去的夸张描述等等。然后,美国有线频道在新罕布什尔一户居民家厨房里录下的片段浮出水面。拜登当时同意在一次不加剪辑的竞选活动中全程佩戴麦克风——这在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在这九十分钟的八十九分钟里,他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但他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话太多,就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一名选民问起他的法学院成绩,拜登嗤之以鼻:“我觉得我的智商可能比你要高得多。”接下来,他气势汹汹地就自己的教育背景做出了至少三个不实陈述。
——他们嗅到了另一桩丑闻,比赛着要挖出拜登的其他过错:从休伯特·汉弗莱和罗伯特·肯尼迪那里剽窃的语句;一篇有着糟糕脚注的法学院论文导致的成绩不及格;关于拜登过去的夸张描述等等。然后,美国有线频道在新罕布什尔一户居民家厨房里录下的片段浮出水面。拜登当时同意在一次不加剪辑的竞选活动中全程佩戴麦克风——这在政治史上是第一次。在这九十分钟的八十九分钟里,他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但他在整个职业生涯里都话太多,就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一名选民问起他的法学院成绩,拜登嗤之以鼻:“我觉得我的智商可能比你要高得多。”接下来,他气势汹汹地就自己的教育背景做出了至少三个不实陈述。
康诺顿并没有听过基诺克的演讲,也不知道拜登是如何运用的。说实话,他并不关心拜登的巡回演讲;他总能用一句话引发满堂喝彩:“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政治英雄被谋杀了,就说我们的梦想已经破灭,它深深埋在我们破碎的心底。”康诺顿比任何人都更敬重肯尼迪,但这句台词让他显得平平无奇——它太文绉绉了,更适合十年前或更久之前的美国人。为什么拜登不能让演讲更务实,谈谈议题、事实和解决方案,就像在塔斯卡卢萨谈及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那样呢?他似乎在用自己触动人心的能力来竞选总统,年轻时的杰夫·康诺顿正是因为他的这种能力才花六年时间来加入他的团队。触动人心之后,又要让他们做什么呢?他试图让自己听上去就像那些被谋杀的英雄本人一样。学者们说,肯尼迪家族引用希腊先贤,而拜登引用肯尼迪家族。有时还不加注明。
终极游戏的规则正在改变。1968年,乔治·罗姆尼在电视上说,他在越南时被将军们洗脑了,而他的总统竞选之路也终结于此。
 1972年,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雪花飘落,埃德·马斯基站在威廉·勒布——这位编辑诽谤了他的妻子简——的《联合导报》的办公室门外的一辆平板卡车上,在摄像机前擦拭愤怒的泪水,而这成了马斯基的结局。
1972年,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雪花飘落,埃德·马斯基站在威廉·勒布——这位编辑诽谤了他的妻子简——的《联合导报》的办公室门外的一辆平板卡车上,在摄像机前擦拭愤怒的泪水,而这成了马斯基的结局。
 1980年,罗纳德·里根歪头一笑:“你又来了。”结果吉米·卡特只做了一任总统。
1980年,罗纳德·里根歪头一笑:“你又来了。”结果吉米·卡特只做了一任总统。
 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问:“牛肉去哪儿了?”这映衬得加里·哈特突然间看起来像是个头发浓密、虚有其表的年轻人。
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问:“牛肉去哪儿了?”这映衬得加里·哈特突然间看起来像是个头发浓密、虚有其表的年轻人。
 电视上的十秒钟能永远固定一个人的角色,既能给他加冕,也能终结一场竞选。总统和竞争者完全可以在媒体迫不及待的帮助下实施协助自杀。
电视上的十秒钟能永远固定一个人的角色,既能给他加冕,也能终结一场竞选。总统和竞争者完全可以在媒体迫不及待的帮助下实施协助自杀。
然而,在杰夫·康诺顿把自己的野心寄托在乔·拜登身上的那一年,终极游戏的新规则才刚刚引起注意。1987年,曾为戏剧化的政治余兴节目而存在的事物开始喧宾夺主:暴露在镁光灯下的候选人和他遭受羞辱的妻子;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巨细无遗地描述、证明和否定自己过去的提名候选人;人们在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问题上都会互相对立,双方的狂热分子和利益团体动员着全面战争;对一个政治家生活中或新或旧的罪恶的日常挖掘;记者们如同野狗一般,嗅着有权势但已受伤的猎物身上的血腥气味彼此竞逐,势头越来越猛,抵达高峰。1987年有加里·哈特,罗伯特·博克
 ,还有乔·拜登——后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还有乔·拜登——后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在竞选团队内部,基诺克的故事爆出之后的两周如同一场失控的噩梦,每一天都有新的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但回想起来,结局的到来仿佛早已注定、无可避免,如同古代部落文化中核心的一场献祭仪式。候选人发誓要坚持,试图无视狂吠的猎犬。媒体则不停地抽血。候选人的同僚表示支持他。但这些故事已经树立起难以挽回的糟糕形象,可能再也无法抹除。候选人把家人和心腹聚集在身旁,一个接一个地询问他们的建议。他们希望他能继续参选,好保卫自己的名誉;他们希望他能退选,好保卫自己的名誉。带着泪水,他选择放弃。他压抑着怒火,扬起下巴,面对摄像机。
9月23日早晨,考夫曼让康诺顿去通知全国的筹款组长们,拜登将在中午宣布退选。媒体发布会前两分钟,康诺顿给在亚拉巴马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唯一能说出口的只有“打开电视”。他在洗手间里哭泣时,其他所有幕僚都在听拜登在拉塞尔大楼发表的声明。“我为陷入这番境地而生自己的气——让自己陷入这番境地。”拜登对着如同行刑队般的摄像机说,“我该去博克的听证会了,以免我说出什么听起来很讽刺的话。”言毕,拜登走进三楼的参议员党团活动室,坐在司法委员会主席的位置上;这场听证会阻挠了罗伯特·博克法官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也开启了拜登在政治上的复健。
康诺顿患上了战斗疲劳症。短短两周里,他的英雄被揭发为伪君子,从白宫材料变成了全国笑料。
“他曾声称,他的力量在于他能通过演讲触动人心。”康诺顿说,“结果,他只是在借用其他人的话,一切都被彻底动摇了。”现在,康诺顿不知道该做什么:他的人生突然失去了方向。当考夫曼要求他在威尔明顿多留几个月来协助结束竞选活动时,他答应了。这让他看起来像个好战士,但事实是,他已经彻底瘫痪,无力去寻求更好的选择。他现在做的是政治中最糟糕的工作——花费数小时打电话给愤怒的支持者,他们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或是打电话给艾奥瓦和新罕布什尔愤怒的职员,他们扣留了竞选活动中使用的电脑,除非能拿到最后一笔工资。哪怕只给竞选活动捐过一个火腿三明治的人,现在都寄来了账单。康诺顿的任务是记录归档拜登受此番耻辱中的每一步——每一桩可能在1990年的下一次参议员竞选中对他不利的负面新闻和评论。这种新闻和评论足足有数百条,在这场炼狱的最后,拜登的人生已被研究透彻——就连他植发的事也不例外。这就像在一场可怕的事故之后负责清理尸体碎片,还要把那些碎片保留下来作为呈堂证供。
1987年末,康诺顿得到一份为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筹款的工作。他拒绝了——他不想花费整个职业生涯去记录支票和胸针。他仍然想要涉足政治的实务:议题。然后,考夫曼告诉他司法委员会有一个职位空缺;年薪四万八千美元,相当于华尔街新手分析员。但是,那里会有关于反垄断法、知识产权和民事司法改革的有趣工作。康诺顿感到自己与考夫曼之间有稳固的纽带,他也不想放弃拜登。况且,华尔街也不可能雇用他:10月19日,股票市场崩盘,迎来史上单日最高跌幅;1986年的税制改革法案终结了许多曾让公共财务部门欣欣向荣的套汇漏洞。他决定留在华盛顿。
在华盛顿特区,每个人都得是谁的人。康诺顿是拜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