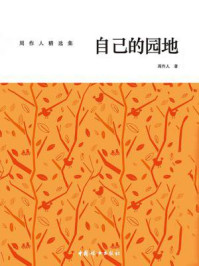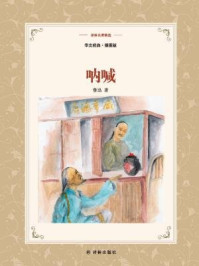有位西方的发展学者说:贫穷是一种生活方式。言下之意是说,有些人受穷,是因为他不想富裕。这句话是作为一种惊世骇俗的观点提出的,但我狭隘的人生经历却证明此话大有道理。对于这句话还可以充分地推广: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洛克先生以为,人人都追求快乐,这是不言自明的。以此为基础,他建立了自己的哲学大厦。斯宾诺莎也说,人类行为的原动力是自我保存。作为一个非专业的读者,我认为这是同一类的东西,认为人趋利而避害,趋乐而避苦,这是伦理学的根基。以此为基础,一切都很明白。相比之下,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作崇高——举例来说,孟子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这是人先天的良知良能,这就是崇高的根基。我也不怕人说我是民族虚无主义,反正我以为前一种想法更对。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富裕,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贫困;从前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快乐,从后一种想法里产生的总是痛苦。我坚定不移地认为,前一种想法就叫作聪明,后一种想法就叫作愚蠢。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理科,凭这样的学问底子,自然难以和专业哲学家理论,但我还是以为,这些话不能不说。
对于人人都追求快乐这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罗素却以为不尽然,他举受虐狂作为反例。当然,受虐狂在人口中只占极少数。但是受虐却不是罕见的品行。七十年代,笔者在农村插队,在学大寨的口号鞭策下,劳动的强度早已超过了人力所能忍受的极限,但那些工作却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对于这些活计,老乡们概括得最对:没别的,就是要给人找些罪来受。但队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乐此不疲,干得起码是不比别人少。学大寨的结果是使大家变得更加贫穷。道理很简单:人干了艰苦的工作之后,就变得很能吃,而地里又没有多长出任何可吃的东西。这个例子说明,人人都有所追求,这个道理是不错的,但追求的却可以是任何东西:你总不好说任何东西都是快乐罢。
人应该追求智慧,这对西方人来说是很容易接受的道理;苏格拉底甚至把求知和行善画上了等号。但是中国人却说“难得糊涂”,仿佛是希望自己变得笨一点。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因为这个缘故,在我年轻时,总是个问题青年、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的:别人希望我变得笨一些。谢天谢地,他们没有成功。人应该改变自己,变成某种样子,这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有疑问的只是应该变聪明还是变笨。像这样的问题还能举出一大堆,比方说,人(尤其是女人)应该更漂亮、更性感一些,还是更难看、让人倒胃一些;对别人应该更粗暴、更野蛮一些,还是更有礼貌一些;等等。假如你经历过中国的七十年代,就会明白,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答案。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我相信洛克的理论。人活在世上,趋利趋乐暂且不说,首先是应该避苦避害。这种信念来自我的人生经验:我年轻时在插队,南方北方都插过。谁要是有同样的经历就会同意,为了谋生,人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必须搬动大量沉重的物质:这些物质有时是水,有时是粪土,有时是建筑材料,等等。到七十年代中期为止,在中国南方,解决前述问题的基本答案是:一根扁担。在中国的北方则是一辆小车。我本人以为,这两个方案都愚不可及。在前一个方案之下,自肩膀至脚跟,你的每一寸肌肉、每一寸骨骼都在百十公斤重物的压迫之下,会给你带来腰疼病、腿疼病。后一种方案比前种方案强点不多,虽然车轮承担了重负,但车上的重物也因此更多。假如是往山上推的话,比挑着还要命。西方早就有人在解决这类问题,先有阿基米德,后有牛顿、卡特,所以在一二百年前就把这问题解决了。而在我们中国,到现在也没解决。你或者会以为,西方文明有这么一点小长处,善于解决这种问题,但我以为这是不对的。主要的因素是感情问题。西方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源于自身,所以就重视解决肉体的痛苦。中国人以为,人的主要情感是亲亲敬长,就不重视这种问题。这两种想法哪种更对?当然是前者。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在西方人看来,人所受的苦和累可以减少,这是一切的基础。假设某人做出一份牺牲,可以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很多幸福,这就是崇高——洛克就是这么说的。孟子不是这么说,他的崇高另有根基,远不像洛克的理论那么能服人。据我所知,孟子远不是个笨蛋。除了良知良能,他还另有说法。他说反对他意见的人(杨朱、墨子)都是禽兽。由此得出了崇高的定义:有种东西,我们说它是崇高,是因为反对它的人都不崇高。这个定义一直沿用到了如今。细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混蛋逻辑,还不如直说凡不同意我意见者都是王八蛋为好。总而言之,这种古怪的论证方式时常可以碰到。
在七十年代,发生了这样一回事:河里发大水,冲走了一根国家的电线杆。有位知青下水去追,电杆没捞上来,人也淹死了。这位知青受到表彰,成了革命烈士。这件事引起了一点小小的困惑:我们知青的一条命,到底抵不抵得上一根木头?结果是困惑的人惨遭批判,结论是:国家的一根稻草落下水也要去追。至于说知青的命比不上一根稻草,人家也没这么说。他们只说,算计自己的命值点什么,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崇高。坦白地说,我就是困惑者之一。现在有种说法,以为民族的和传统的就是崇高的。我知道它的论据:因为反民族和反传统的人很不崇高。但这种论点吓不倒我。

过去欧洲有个小岛,岛上是苦役犯服刑之处。犯人每天的工作是从岛东面挑起满满的一挑水,走过崎岖的山道,到岛西面倒掉。这岛的东面是地中海,水从地中海里汲来。西面也是地中海,这担水还要倒回地中海去。既然都是地中海,所以是通着的。我想,倒在西面的水最终还要流回东面去。无价值的吃苦和无代价的牺牲大体就是这样的事。有人会说,这种劳动并非毫无意义,可以陶冶犯人的情操、提升犯人的灵魂;而有些人会立刻表示赞成,这些人就是那些岛上的犯人——我听说这岛上的看守手里拿着鞭子,很会打人。根据我对人性的理解,就是离开了那座岛屿,也有人会保持这种观点。假如不是这样,劳动改造就没有收到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性就被逆转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要逆转人性,必须有两个因素:无价值的劳动和暴力的威胁,两个因素缺一不可。人性被逆转之后,他也就糊涂了。费这么大劲把人搞糊涂有什么好处,我就不知道,但想必是有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个岛。细想起来,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就包含了这种东西。举个例子来说,朝廷的礼节。见皇上要三磕九叩、扬尘舞蹈,这套把戏耍起来很吃力,而且不会带来任何收益,显然是种无代价的劳动。但皇上可以廷杖臣子,不老实的马上拉下去打板子。有了这两个因素,这套把戏就可以耍下去,把封建士大夫的脑子搞得很糊涂。回想七十年代,当时学大寨和抓阶级斗争总是一块搞的,这样两个因素就凑齐了。我下乡时,和父老乡亲们在一起。我很爱他们,但也不能不说:他们早就被逆转了。我经历了这一切,脑子还是不糊涂,还知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只说明一件事:要逆转人性,还要有第三个因素,那就是人性的脆弱。

我认为七十年代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看法和一些同龄人是一样的。七十年代的青年和现在的青年很不一样,更热情、更单纯、更守纪律,对生活的要求更低,而且更加倒霉。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是一种极难得的际遇,这些感受和别人是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这种经历是一种崇高的感受,我就断然反对,而且认为这种想法是病态的。让我们像奥威尔一样,想想什么是一加一等于二,七十年代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个极痛苦的年代。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对这个道理稍加推广,就会想道:人是一种会自己骗自己的动物。我们吃了很多无益的苦,虚掷了不少年华,所以有人就想说,这种经历是崇高的。这种想法可以使他自己好过一些,所以它有些好作用。很不幸的是它还有些坏作用:有些人就据此认为,人必须吃一些无益的苦、虚掷一些年华,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崇高。这种想法不仅有害,而且是有病。
说到吃苦、牺牲,我认为它是负面的事件。吃苦必须有收益,牺牲必须有代价,这些都属一加一等于二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我在七十年代吃的苦、做出的牺牲是无价值的,所以这种经历谈不上崇高;这不是为了贬低自己,而是为了对现在和未来发生的事件有个清醒的评价。逻辑学家指出,从正确的前提能够推导出正确的结论,但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就什么都能够推导出来。把无价值的牺牲看作崇高,也就是接受了一个错误的前提。此后你就会什么鬼话都能说出口来,什么不可信的事都肯信——这种状态正确的称呼叫作“糊涂”。人的本性是不喜欢犯错误的,所以想把他搞糊涂,就必须让他吃很多的苦——所以糊涂也很难得呀。因为人性不总是那么脆弱,所以糊涂才难得。经过了七十年代,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变得更聪明。有些人对人世间的把戏更看不懂了,他就是变得更糊涂。不管发生了哪种情况,七十年代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