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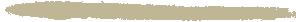
德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美国文学和日本文学介绍到我国已经有了很长一段历史,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出现了大量各国文学译本。特别是日本文学,据查,在明代已经有李言恭、郑杰编纂的日本短歌 39 首被译为中文。澳大利亚文学进入中国则是比较近期的事。1953 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詹姆斯·阿尔德里奇(James Aldridge)的小说《外交官》(
The Diplomat
)的中文译本,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澳大利亚小说。1954 年出版了弗兰克·哈代(Frank Hardy)的《幸福的明天》(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和《不光荣的权力》(
Power Without Glory
),此后又陆续出版了一些长篇和短篇小说以及一些诗集和剧本,包括凯瑟琳·苏珊娜·普里查德(Katharine Susannah Prichard)的《沸腾的九十年代》(
The Roaring Nineties
),朱达·沃顿(Judah Waten)的《不屈的人们》(
The Unbending
)等。
 但是,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澳洲文学翻译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翻译的选题范围狭窄,作品内容单一。
但是,总的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我国的澳洲文学翻译不仅数量很少,而且,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翻译的选题范围狭窄,作品内容单一。
这一局面的改变得益于 1978 年我国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些对澳洲文学翻译具有深远意义的事情。安徽大学成立了大洋洲文学研究所,推出《大洋洲文学》期刊,翻译出版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一些文学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寿康翻译的《劳森短篇小说集》。这一年年底,教育部将全国选拔出的 9 位中年教师集中于北京,准备派往悉尼大学。这就是日后人们戏称“九人帮”的一批学者。在悉尼大学,他们虽然分属英文系和语言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但多数都选学了澳大利亚文学课程。这一批学者在学成归国后,在推动澳大利亚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就是在这一年,李尧先生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学翻译之旅。
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时代。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呈现出勃勃生机。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包括艾伦·马歇尔(Alan Marshall)的《我能跳过水洼》( I Can Jump Puddles ),罗尔夫·博尔德沃德(Rolf Boldrewood)的《空谷蹄踪》( Robbery Under Arms ),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风暴眼》( The Eye of the Storm )、《人树》( The Tree of Man )、《探险家沃斯》( Voss )、《树叶裙》( A Fringe of Leaves )和《镜中瑕疵》( Flaws in the Glass ), 迈尔斯·弗兰克林(Miles Franklin)的《我的光辉生涯》( My Brilliant Career ), 兰道夫·斯托(Randolph Stow)的《归宿》( To the Island ),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的《辛德勒的名单》( Schindler's List )和《内海的女人》( Woman of the Inner Sea ),彼得·凯里(Peter Carey)的《奥斯卡和露辛达》( Oscar and Lucinda )以及一批短篇小说集和诗集。杰克·希伯德(Jack Hibberd)的剧本《想入非非》( A Stretch of the Imagination )不仅翻译出版,而且在京沪两地公演。综前所述,可以看出我国译者不断拓展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范围,将不同背景、不同流派的作家纳入自己的视野,使得澳洲文学翻译在我国不仅数量激增,而且内容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致力于翻译和介绍澳大利亚文学的中国学者是一个群体,既包括早期的马祖毅、刘寿康等,也包括八十年代初从澳大利亚归来的留学学者黄源深、胡文仲等,他们一直处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教学和研究的第一线。译者中还包括朱炯强、叶胜年、曲卫国、欧阳昱、李尧等。这一大批译者在介绍和推广澳大利亚文学方面成绩显赫。其中李尧的贡献尤为突出。除了文学翻译,还应该特别提到黄源深教授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以及王国富教授主编翻译的《麦夸里英汉双解词典》,这两部巨著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研究和翻译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李尧先生致力于文学翻译四十年,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也翻译出版了部分英美文学作品,总计 52 部,字数逾千万,在我国翻译界如此多产的译者实属少见。李尧翻译的作品涵盖澳大利亚作家老中青三代,既包括老一代作家帕特里克·怀特,托马斯·肯尼利,亚历克斯·米勒等,也包括中年作家彼得·凯里, 尼古拉斯·周思等,还包括一些年轻的儿童文学作家。从文学流派看,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都囊括其中。此次出版的《李尧译文集》只占他翻译的澳大利亚文学作品的约三分之一。收入集子的作品大部分获得过文学大奖,在澳洲文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有些则是考虑到作家在中国的影响或者题材与中国有关。这一译文集集中反映了李尧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
李尧先生 1966 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外语系,从事记者工作和文学创作二十余年,发表过报告文学、散文、小说等近百万字,1986 年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正是由于李尧的作家背景,他翻译的文学作品具有一个突出特点:文字优美,行文流畅。阅读他翻译的作品,给人以欢畅淋漓的感觉。李尧回忆说:“我翻译小说的时候,常常是从一个写小说的人的角度出发,像我自己写小说一样,体会、捕捉作者的思路,创作的技巧,注意人物性格化语言的翻译。不是只从字面上去对应。我看懂原文,就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字典上的意思去翻译。这样译出来的东西就比较鲜活,可读性强。”翻译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的《卡彭塔利亚湾》(
Carpentaria
)难度很大。作者是澳大利亚当代最有成就的原住民作家。小说涉及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宗教信仰、部族矛盾、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人情、历史渊源等,而且写作方法也比较独特。李尧在翻译这部小说前,大量阅读了有关澳大利亚原住民历史文化的著作,同时不断和作者联系,取得她的帮助。悉尼大学在授予李尧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时指出:“《卡彭塔利亚湾》是李尧毕生从事文学翻译和四十余年来中澳文化交流的巅峰之作。”有评论指出:“《卡彭塔利亚湾》是纯文学性文本,李尧先生翻译策略的选择,让译文洋溢着一种梦幻般的抒情色彩,充满文学情调,让读者感受到澳大利亚古老土地的荒芜。”
 翻译从来都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王佐良先生对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曾经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因为有翻译,哪怕是不免出错的翻译,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语言学家、文体学家、文化史家、社会思想家、比较文学家都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通过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做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人要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翻译从来都不是简单地把一种语言变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王佐良先生对于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曾经发表过许多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因为有翻译,哪怕是不免出错的翻译,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语言学家、文体学家、文化史家、社会思想家、比较文学家都不能忽视翻译。这不仅是因为通过翻译者的辛勤劳动才使得一国的文化遗产能为全世界的人所用,还因为译者做的文化比较远比一般人要细致、深入。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
 李尧正是通过他的文学翻译将独特的澳洲大陆文化介绍给了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民。
李尧正是通过他的文学翻译将独特的澳洲大陆文化介绍给了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民。
李尧先生几十年来耕耘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这片土地上,他的勤奋努力非常人所可比拟,他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他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方面的成就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于1996、2008、2012 年三次获得澳中理事会颁发的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奖。2014年被悉尼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表彰词指出,李尧“在中国,在文学翻译和澳大利亚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把许多澳大利亚作家介绍给中国读者,包括帕特里克·怀特,托马斯·肯尼利,亚历克西斯·赖特,为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人民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在中国的成功首先是由于译者的努力和奉献,但与澳大利亚作家们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也紧密相关。许多译者都与澳大利亚作家有过密切而友好的交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无私的帮助。澳中理事会在推动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和澳大利亚学术研究方面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后,还应该提到中国出版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兴趣和关注。没有他们一以贯之的支持就不可能有今天澳大利亚文学翻译在中国的丰收。
2018 年适逢中国澳大利亚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也恰是李尧先生从事文学翻译四十周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西悉尼大学和在华澳大利亚研究基金会共同发起出版的十卷本《李尧译文集》既是对于李尧几十年来从事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充分肯定,更是繁茂的中澳文化交流之见证。我们相信,澳大利亚文学翻译事业今后在我国必将取得更长足的进步,在促进中澳文化交流方面也必将起到更大的作用。

2017 年 8 月 2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