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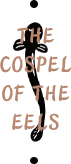
是爸爸教会我怎样钓鳗鱼的,在那条流过田野的小溪中。田野旁边就是爸爸童年时住的房子。8月的一个黄昏,我们开车去那里,在那条与小溪相交的乡间公路上左转,拐进一条小路——说是小路,其实就是地上的两道拖拉机车辙,沿着一个很陡的山坡往下开,然后顺着小溪前行。左边是一片麦田,熟了的麦子哗啦哗啦地刮着车身;右边是一片草地,高高的杂草窸窸窣窣地响着。草地后面是一条大约6米宽的小溪,水流平静,蜿蜒于植被间,在黄昏的最后一抹阳光下如同一条闪光的银链。
我们在路上沿着急流慢慢地向前开——溪水惊恐地拍打着石头,路过一棵歪斜的老柳树。当时我7岁,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很多次了。地上的车辙终止了,我们面前出现一堵茂密植被形成的墙,这时爸爸关闭了发动机。天色暗了下来,周围一片寂静,只有水里传出的轻轻的汩汩声。我们俩都穿着橡胶靴和油亮的聚乙烯面料的裤子,我的是黄色的,他的是橙色的。我们从后备厢里拿出两个装渔具的黑色桶、一把手电筒和一罐蚯蚓,然后出发了。
沿着溪岸,那些草湿漉漉的,很难拨开,高度超过了我的头。爸爸走在前面,踩出一条小路。我跟在后面,那些植被围拢起来,仿佛在我头顶形成一道拱门。蝙蝠在小溪上方来回翻飞,像在天空中画下黑色的标点符号。
走了大概40米,爸爸停了下来,四下张望。“这儿应该不错。”他说。
一个陡峭泥泞的斜坡通往下面的小溪。如果一脚踩错,就可能冲下斜坡,直接滑进水里。天已经变暗了。
爸爸用一只手挡开那些杂草,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往下踩,然后转过身来伸出一只手给我。我抓住他的手,以同样小心翼翼的步子跟在他后面。来到水边,我们在溪岸边一起踩出了一小块平地,放下我们的水桶。
爸爸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察看了一会儿溪水,我模仿他的样子,跟随他的目光,想象着我也能看到他看到的东西。当然不可能确切地知道我们选的地方好不好。水很暗,几丛猛烈摇曳的水草从各处冒出来,然而水面下的一切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无法知道任何事情,但我们选择相信,有时候我们必须这么相信。钓鱼常常就在于相信。
“嗯,这儿应该不错。”爸爸又说了一遍,然后转向我。我从桶里拿出一卷钓鱼线,递给了他。他把钓竿顶在地上,快速地缠上钓鱼线,把鱼钩拿在手里,从罐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条很肥的蚯蚓。他咬紧嘴唇,在手电筒的光线下查看那条蚯蚓。把它穿上鱼钩之后,他把鱼钩举到面前,假装朝它吐了两口唾沫以求好运,“噗噗”,永远都是两声,然后在空中挥舞一下,把它抛进水中。他弯下身子,触摸了一下钓鱼线,确保它是紧绷的,同时又不会被溪流带得太远。随后他把背挺直了,说“就这样吧”,然后我们重新沿着斜坡爬上去。
那个我们称之为钓鱼线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普通的钓鱼线。钓鱼线通常是指一根长线,上面有很多鱼钩,鱼钩之间还有很多沉子。而我们用的钓鱼线要更为原始。爸爸取来一根木条,用斧子把一头削尖。他剪下一段粗尼龙绳,四五米长,把它系在木条的一头。沉子他是这么做的:把熔化的铅灌进一根钢管里,让它凝固,然后把钢管锯成段,每一段两厘米,在中间钻一个可以穿钓鱼线的孔。沉子系在离钓鱼线终端一手长的地方,钓鱼线最下端是一个比较大的单独的鱼钩。我们将木条锤进地里,让挂着蚯蚓的鱼钩落在溪底。
我们通常会带10根或12根钓鱼线,装好鱼饵后,把它们扔进水里,扔完一个再扔另一个,间隔约10米。在陡峭的斜坡上爬上爬下,每一次都是同样辛苦的程序,同样训练有素的协作,同样的手势,以及同样的祈求好运的两声“噗噗”。
设置好最后一根钓鱼线后,我们原路返回,在斜坡上爬上爬下,再检查一遍每一根钓鱼线:小心地拽一下,确认还没有鱼上钩。然后静静地站着感受,让直觉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应该不错,只要我们多给一点时间,就会有好事发生。到我们确认完最后一根钓鱼线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无声的蝙蝠只有在掠过月光的光束时,才能被看见。我们最后一次爬上斜坡,走回车里,开回了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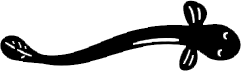
我不记得在溪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谈论过鳗鱼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钓到鳗鱼之外的话题。事实上,我都不记得我们说过话。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确实没有说过话。因为我们身处一个谈话需求有限的地方,一个最好保持沉默才能好好品味的地方。月光的倒影、沙沙作响的草丛、树的影子、单调的溪流声,还有那些蝙蝠——它们仿佛盘旋在这一切上空的星号。我们得保持安静,才能让自己成为这个整体的一部分。
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把一切都记错了。因为记忆是会骗人的,它会筛选和选择保存哪些东西。当我们在记忆中搜寻一个往昔的场景时,我们完全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记住了最重要或最相关的内容,但我们记住了符合我们预想的内容。当记忆描绘出一个画面时,其中的各种细节必然是互为补充的。记忆不允许任何与背景不协调的颜色存在。所以我们不妨说,当时我们是沉默的。不然的话,我也不知道我们可能会说些什么。
我们住在离小溪只有两公里的地方。深夜回到家后,我们把靴子和聚乙烯面料的裤子脱在屋外的台阶上,我直接上床睡觉了。我很快就睡着了,早晨五点一过,爸爸又把我叫醒。他不需要多说什么。我立刻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短短几分钟后我们就已经坐到车里了。
来到溪边,太阳正要升起。黎明将天空的下沿染成了深橘色。水流似乎变了一种声音,更加清澈,更为明亮,仿佛刚从一场柔软的睡梦中醒来。还有其他声音围绕在我们四周:一只乌鸫唱起歌来;一只凫降落在水面上,笨拙地溅起水花;一头苍鹭在小溪上空无声地侦察,它长着硕大的喙,仿佛一把高举的匕首。
我们穿过潮湿的草丛,再次侧着身子踩着斜坡下到溪边,来到第一个鱼钩处。爸爸在坡下接住我,我们一起检查钓鱼线是不是紧绷的,寻找水面之下的动静。爸爸弯下身子,把手放在钓鱼线上。然后他直起腰,摇了摇头。他收起钓鱼线,把鱼钩举到我面前。上面的蚯蚓已经空空如也,大概是狡猾的雅罗鱼干的。
我们继续走向下一处鱼钩,它也是空的。第三处也一样。在第四处,我们可以看到钓鱼线被扯进了一片芦苇丛中,爸爸去拉它的时候,它被卡住了。他非常小声地嘀咕了一句什么,两只手抓住钓鱼线,拽得更加用力,但是它却一动不动。可能是水流把鱼钩和沉子拖进了芦苇丛中。但也可能是一条蛰伏在那里的鳗鱼吞进了鱼钩,然后又被水草缠住了。如果拉一下手里的钓鱼线,有时候还能感觉到小小的动静,仿佛水面之下钓鱼线另一头被卡住的那个东西正在挣扎。
爸爸一边绕一边拉,咬着嘴唇,嘴里嘀嘀咕咕地骂着什么。他知道要摆脱现在的状况只有两种方法,两种方法都会有输家。要么帮鳗鱼解围,这样可以把它拉上来;要么扯断钓鱼线,让这条鳗鱼待在溪底,困在芦苇丛中,身上带着鱼钩和沉重的沉子,就像一副刚刚打造好的脚镣。
这一回似乎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他往旁边走了几步,寻找另一个角度,用力拉扯,尼龙线就像小提琴的弦一样紧绷,但无济于事。
“唉,不行。”他最后说,然后用尽所有力气一拉,钓鱼线高高地弹了起来,断了。
“只能祝它好运了。”他说。然后我们继续走上斜坡,再走下斜坡。
在第五个鱼钩处,爸爸弯下腰,轻轻地用指尖摸了摸钓鱼线。然后他直起身子,往一边迈出一步。“你能拿着它吗?”他说。
我拿住钓鱼线,轻轻地拉了一下,立刻感觉到了回应的力度。爸爸仅用指尖就能感觉到。我立刻意识到,这种感觉很熟悉。我略微使劲拉了一下,那条鱼动了起来。“是条鳗鱼。”我大声说。
鳗鱼不会像狗鱼那样乱扑腾,它们更喜欢侧着身子扭动,这会产生一股起伏的阻力。就其体量来说,鳗鱼非常有劲,尽管它的鳍很小,它却是游泳高手。
我尽可能慢地收钓鱼线,不让它松弛,仿佛在细细品味这一刻。不过钓鱼线很短,附近也没有鳗鱼可以逃进去的芦苇丛,很快我就把它拎出了水面,看到了那闪闪发亮的黄褐色身体,在黎明的阳光下扭动着。我试图捏住它的头后侧,但几乎抓不紧。它像一条蛇一样扭来扭去,缠着我的手臂,一直缠到肘部。我感觉这种力量更像是一股静止的力量,而不是一股活动的力量。如果现在我让它掉到地上,它就会钻进草丛中溜走,在我重新抓住它之前,再次游回水里。
最终,我们取下了鱼钩,爸爸往桶里装满了溪水。我把鳗鱼放了进去,它立刻沿着桶壁游了起来,仿佛训练有素。爸爸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说这条鳗鱼很漂亮。我们继续向下一个鱼钩处走去,迈着轻松的步子沿着斜坡上上下下。拎桶的工作由我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