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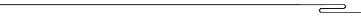
人们常说“字如其人”,我们的笔迹里潜藏着我们的性格心理。同理,西方有些国家认为“人如其食”,也许是基于食物进入身体后所产生的奇妙的化学反应,我们吃的食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我们的一些心理特征。
食物有酸、甜、苦、辣、咸的五味之分,而只有辣最特别。在我国,爱吃辣的人差不多占到了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还不算那些喜欢微辣,偶尔吃辣的人。因为辣是一种痛觉和热觉,吃得太辣,我们习惯喝凉水去冲淡辣的感觉,这其实很类似于降温。
吃辣能够提升人的攻击性,对此,心理学界进行了一些研究测试。实验一:通过提问的方式记录被试是否爱吃辣,爱吃辣的程度是怎样的(微辣、特辣、变态辣),记录之后让被试做关于攻击性的量表,以此来对比,发现喜欢吃辣的程度越高的人,他的攻击性就越强;实验二:给到所有的被试相同的食物,但其中一组微辣,另一组不辣,等被试吃完,让他们进行填词游戏,发现微辣组的人更偏向填写带有攻击性的词汇;实验三:让被试去看一些辣或者不辣的食物,然后对被试的攻击性水平进行测试,得到的结果与前两个实验相同。
弗洛伊德认为攻击性属于本能。宇宙的文明起源不可探寻,人类文明的出现源自一把火,文明利用力比多(指性力,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将大家串联在一起,使得群体之间产生相互的认同,文明意味着规矩,规矩就是束缚,人类便需要更多的力比多来保持这样的状态,用以保证原始的性不会打破现状。人类不愿意承认的就是天生具有攻击性,周围的人不仅可以是合作伙伴还可以是攻击对象,因为某些目的或者追求某种刺激,我们有时会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当然这种目的或者刺激也可以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实现。在某些情况下,对于攻击性的管束往往会失去控制,这个时候人不够冷静,可能完全靠本我支配,攻击性就会变为攻击行为。
我们可以在自己或者朋友身上发现这种攻击性的倾向,我们和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也因为攻击倾向变得棘手,整个群体的文明正为此消耗着能量。人类原始的攻击性被自我压制,后天形成的超我服从社会大的原则同样在限制着本能的展现,除了偶尔合理的、不触犯社会规范的攻击行为,人类凡是对社会群体其他成员的攻击都会受到惩罚。超我伴随着文明而发展,文明又在我们越来越了解自己的时候,给了我们返璞归真的机会,促使我们懂得与自己的欲望和谐相处。
美国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弗洛伊德对于攻击性的认识存在片面性。前者在《人类的破坏性攻击》中指出,攻击分为“良性攻击”和“恶性攻击”。“良性攻击”是一种反抗式、逃跑式的,它依然是生物本能的一部分,如同大多数动物遇到天敌会全力逃跑、躲藏,借以让自己好好活下去一样,人类在遇到危险时也会退缩,也会逃避。“良性攻击”就像是生命的防御机制,它是生存体制的一部分,完全是应着进化论原则而生的,一旦个体确认自己安全,这样的攻击性就会褪去。而“恶性攻击”并非生存演化而来,它只是为了满足人们残忍的欲望。
实际上恶性攻击也可以做一个区分,一种是天生的攻击性,一种是意识形态对权力的渴望,还有一种是心理层面的心理竞争。大概在4岁左右,人类有了“我”的概念之后,“我”与“他”的竞争便相伴出现了,弗洛伊德说“自我的房子里住着的并不是自己的主人”。对于这一点,弗洛姆提出“心理生存”的概念,如同人要在社会上立足要活下去,心理也要生存。我们对于心理所渴求的东西、能量或者说是刺激,除非我们本身能够制造幻觉蒙骗自己,否则只能通过外部的手段来获取。
如此说来,心理有自己的生存方式,生命活动都有自己的动机,那么心理的动机又是怎样的?“存在性冲动”让我们变得像是弗洛姆所说的“宇宙的畸形儿”,我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思维又常常跳出这个世界去琢磨这个世界,其他动物就不同,它们不会陷入这样的矛盾之中。动物不会去思考广袤的宇宙,它们的驱动模式是本能。人的心理的运转,在自我意识与对象意识出现后变得更为复杂。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互相证明的,辨别东西南北的前提是要先有一个方向,同理,在我们陷入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交缠后,我们就丧失了附着感,也丧失了存在的确定性,我们只有依赖被秩序化的主客体的结构来建立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确实存在,这就是心理的动力,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总是害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漠视。存在性冲动驱使我们展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回归到竞争层面。
作为社会人的角色,攻击性不可忽视。辣,能够挑起人的攻击性,首先是生理的作用,然后记忆将这种刺激与辣画上等号以至于我们看到辣就有可能产生攻击性,攻击性是本能,但它同样受自我的管制,并非所有的攻击性都会表现为攻击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