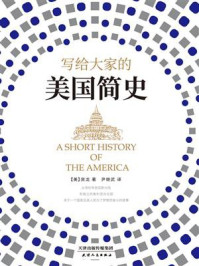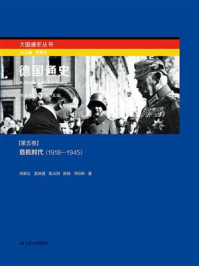即将临盆的女人、拴在原地的狗,以及要命的口臭……这些令人难忘的景象记录着一座罗马城市的普通日常生活突然被中途打断。这样的景象还有很多:烤炉里的面包还在烘烤着就被遗弃了;一群画师在重新装饰一个房间时夺路而逃,把颜料罐和一满桶新鲜灰泥落在了高高的脚手架上——当火山爆发时,脚手架坍塌,桶里的灰泥刚好溅落在整洁的墙壁上,形成一层厚厚的外皮,至今仍然清晰可见(见本书163—168页)。可剥开表层,你会发现庞贝的故事远比想象中复杂,且更加引人入胜。在许多方面,庞贝并不仅仅等同于古代的“玛丽·塞勒斯特”号( Marie Céleste ),当这艘19世纪的航船被神秘地遗弃时,煮鸡蛋(据说)都还留在早餐桌上。庞贝并不只是一个在中流被冰冻的罗马城市。
首先,如果不是在灾难发生的几天前,庞贝居民就是在几小时前已经看到了某些征兆。我们如今唯一拥有的一份目击证词,是25年后小普林尼写给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几封书信。灾难降临时小普林尼正在那不勒斯湾附近。小普林尼在信中表明,即便维苏威火山口出现“雪松状”的乌云后,也仍有一丝逃离的生机,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掺杂了想象的事后之明。小普林尼的叔叔是最著名的受难者之一,夺走他生命的是哮喘病和科学家的好奇心,他勇敢地,或者说愚蠢地决定要近距离观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的考古学家认为,如果在最终灾难爆发的数天或者数月前就已经出现了一系列轻微震颤和小型地震,那么应该也会警醒人们撤离此地。毕竟庞贝并不是唯一受到威胁并最终被吞噬的城市,包括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和斯塔比亚(Stabiae)在内的维苏威以南大片地带都是灾区。
根据城中尸体的数量可以确定,的确有许多人离开了。约有1100具尸体重见天日。城市还有尚未发掘的部分(庞贝古城有四分之一的部分尚未勘察),我们必须为这部分埋藏的尸体留有余地,还要考虑到在早期发掘中遗失的人体残骸(孩子的尸骨容易被误认为动物尸骨而被扔掉)。即便如此,要说有2000多名居民在这场灾难中丢了性命,似乎也不太可能。据估计,这里的人口总量在6400人到3万人之间,这取决于我们所设想的人口居住的密度或者我们所选择的现代参照物,但无论总人口有多少,死者都只占其中一个较小或者非常小的比例。
在浮石大雨中逃窜的人群可能只带了些他们触手可及且方便携带的物件。时间更充裕的则带走了更多家当。我们必须想象这样一幅画面:绝大部分居民尽其所能地用驴子、货车和手推车载着大批家当涌出城市。有些人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将最珍贵的财产锁了起来,指望危机过去之后再回来。在我们于城内或附近的房子里找到的壮观珍藏——比如,令人震惊的银器收藏(见本书297—298页)——中,其中一部分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被留下的。但就绝大部分而言,留给考古学家去发掘的还是一座居民们匆忙打包带走家当并离去之后的城市。这可能有助于解释庞贝城里的房屋里为何只有很少的家具、丝毫也不显得凌乱。这大概并不是因为1世纪时盛行某种现代派的极简主义审美风格。大多数主人都用货车载走了自己心爱的摆设。
这种匆忙的撤离或许也为我们在城内房屋里发现的一些古怪之处提供了解释。例如,如果一堆园艺工具出现在一个精致的餐厅里,那么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则颇感意外——它们平时就放置在这个地方;同样有可能的是,在仓促逃离时,主人把家当归拢在了一起,看看决定要带走什么,于是铲子、锄头和脚手架就恰好被留在这儿了。尽管有些市民仍旧照常打理着日常营生,毫不怀疑第二天还会到来,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处于正常状态的城市,而是一个众人奔逃的城市。
火山爆发后的数周或数月之中,许多幸存者也曾重归故里,寻找他们留下的东西,抑或从被掩埋的城市中抢救(或掠夺)那些可再度利用的资源,例如青铜、铅、大理石。此时看来,由于想要稍后将财宝取出来而将它们锁起来的做法可能并不是那么不明智。因为,庞贝许多地方都有清晰的迹象表明,曾有人穿过火山灰成功回到了这里。无论那是财宝的主人还是企图投机冒险的强盗或寻宝人,他们都凿通了通向豪宅的地道,在从一个被堵住的房间进入下一个时,墙壁上有时会留下凿洞的痕迹。19世纪的发掘者挖出了一座几乎空无一物的大房屋,人们可以从大门上刻着的两个单词一窥他们当时的活动:“此屋已凿”。这基本不可能是房主人留下的文字,因此有可能是一个掠宝者留给同伙的信息,告诉他们这座房屋已经“搞定”。
我们对这伙凿洞人几乎一无所知(但这些用拉丁文写成的信息使用了希腊字母,这表明他们是双语者,属于意大利南部的希腊-罗马社群,我们在第1章中将详加讨论)。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实施劫掠的确切时间:庞贝废墟中发现了一些后灾难时期的罗马硬币,铸币日期大概在公元1世纪末到4世纪初。无论后来的罗马人在什么时候以及出于什么缘由决定向这座被掩埋的城市挖掘,都极其危险,他们可能是希望取回可观的家族财产,抑或带着劫掠来的财宝潜逃。这些地道必定十分危险,既昏暗又狭窄,如果从一些墙洞的大小来判断,有些地方只有孩子才能通过。即便是在那些稍微好走一些的地方,在那些没有被火山灰填满的地区,墙壁和天花板也都有随时坍塌的危险。
讽刺的是,在迄今发现的尸骨中,几乎可以肯定其中有一些不是火山爆发的受害者,而是在灾难发生之后的数月、数年甚至几个世纪之中冒险回到这座城市的人。例如,在“米南德之家”(House of the Menander)——该房子的现代名称,由在其中找到的一幅希腊戏剧家米南德的画像得名(见图44)——的花园庭院旁的一个漂亮房间里发现了一组三人尸骨,包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身上还有一把铁锹和锄头。某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些人是里面的住民,可能是奴隶,在房子快被火山灰吞没时试图夺路逃离房屋,途中命丧黄泉。也有人想象这是一群掠宝者,在试图凿出一条进入房屋的通道时,可能由于通道过于脆弱而坍塌致死。会是哪一种情形呢?
有关这座陷入混乱的城市的图景由于更早之前的一场天灾而变得更加复杂。在维苏威火山爆发的17年前,即公元62年,庞贝就已经受到了一场地震的严重破坏。根据史家塔西佗的记载,“大半个庞贝城毁于一旦”。几乎可以肯定,庞贝银行家卢基乌斯·卡伊基利乌斯·尤昆都斯(Lucius Caecilius Jucundus)家中发现的那对雕刻饰板描绘的就是这一事件。图像表明主要有两片地区受灾较重:广场以及面向维苏威火山的北城门附近的那片地带。在其中一块饰板上,广场上的朱庇特、朱诺和密涅瓦三神庙严重向左倾斜;神庙两侧的骑士雕像仿佛活了过来,骑手要从坐骑上栽下来(见图5)。而在另一块饰板上,面向火山的城门则不祥地向右倾斜,与其左侧的大型分水堡正在分离。这场灾难使我们对庞贝的历史提出了最难回答的问题。它对城市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它让城市花了多长时间恢复正常?或者说,庞贝是否恢复过来了?有没有可能,庞贝人在公元79年仍然住在一片狼藉中,广场、神庙、浴场,更不用说那些私人住宅,或许都还尚未修葺?

图5

人们对此做过大量猜想。有观点认为,一场社会革命在地震之后席卷了庞贝。许多贵族世家决定永远离开此地,在他乡安置家业。他们的离开不仅促使释奴和新兴富人崛起,而且也让庞贝的一些较漂亮的房子从此堕入“没落”之途,它们旋即成了漂洗坊、面包坊、酒馆或者其他工商业场所。事实上,在餐厅里找到的那些园艺工具本身可能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个标志:一所高级住宅被新主人急剧拉低了档次,他们将其改为经营园艺生意的基地。
事实或许确实如此。我们或许还有其他理由认为,公元79年灾难降临时,这座城市的状态绝非“正常”。然而我们无法确定所有这些改变都是由地震直接引起的。毕竟在灾难来临之前,某些产业转型可能就已经开始了。几乎可以肯定,就算不是很多,其中一些也是遵循着财富、用途和声望的固有转变模式发生转变的,这在古往今来的任何城市都有迹可循。更不用说在现代考古学界流行着那种“官员阶层”的偏见,他们自信地将社会流动性和新兴富人阶层的崛起等同于发生了变革或衰落。
还有一种主流意见认为,公元79年的庞贝还没有完成其漫长的修复工程。从我们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塔西佗声称“大半个庞贝城毁于一旦”,可能言过其实了。但是许多公共建筑的运营状况(例如,公元79年时只有一家公共浴场是完全正常运营的)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火山爆发时大量私人住宅里都有装潢工匠表明,(地震带来的)损失不仅十分惨重,而且(在火山爆发时)状况尚未恢复正常。17年过去了,这座罗马城市里的大部分公共浴场始终未能恢复运营,几个主神庙仍然无法使用,私人住宅一片混乱,这说明要么是资金严重短缺,要么是社会机制的瘫痪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抑或二者兼有。当地议会在这近20年中到底为此做了些什么?袖手旁观而放任城市走向崩溃?
不过事实在这里也许同样并非它表面看起来的样子。我们能确定火山爆发时正在展开的修复工作都是针对那次地震产生的破坏的吗?当然,任何城市都几乎总有大量建筑工程在实施(从古至今,修复和建筑工作都是城市生活的核心部分),但抛开这个观点,还有一个问题使研究庞贝的考古学家产生激烈争执:地震是否只有这一场?一些人仍然坚信,公元62年的大地震是唯一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地震,而且——没错——正是它让城市的修复工作步履维艰,直至多年以后仍未完成。但如今更多的人强调,当时必然还发生过一系列的震颤,它们曾持续数日甚至数月,最终导致火山爆发。火山学家深信不疑地告诉我们,这正是激烈的火山爆发的前兆,而且小普林尼也正是这样描述的:“在之前的几天里,大地时常震动。”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那么当时匆忙展开的装潢工作就更有可能是为了修缮新近的损毁,而并非是为了收拾17年前的烂摊子而展开的一项迟来的、不合时宜的工程了。
至于整个城市更普遍的状况,尤其是公共建筑的,后来那些掠宝行为在这里再次被证明是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一个因素。显然,公元79年时有些公共建筑已经化为废墟。有一座俯瞰大海的庞大神庙通常被认为是献给女神维纳斯的,至今仍是一片建筑工地,尽管看起来人们想要按照比原来那座更为恢宏的规模进行修复。其他一些地方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例如伊西斯神庙就一切照常,人们重建了它,用大量城里如今最著名的画作将其重新装饰了一番(见图6)。

图6

不过,相比之下,火山喷发时城市广场的情形要难解得多。有观点认为这就是个半废弃的残迹,几乎没有被修复过。若果真如此,那么这至少表明,委婉说来,公共生活已经不再是庞贝人生活的重心了。最糟糕的情形是,它标志着市政机制的全面崩溃,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与城市里的其他证据并不完全相符。近来也有观点将矛头指向了火山爆发后归来的抢救队或掠宝者。这种观点认为,广场的大部分都已经得到修复,事实上得到了改进。可由于它近来刚刚被饰以昂贵的大理石砌面,于是在城市被火山灰掩埋之后,知情的当地人就立即掘地三尺,把它们从墙上劈了下来。这样一来,整个广场看起来仿佛尚未完工或者径直被荒弃了。当然,也有可能这些抢救者是奔着装饰广场的许多昂贵青铜塑像去的。
这类争论与歧见不断为考古学会议提供养料,成为学术争论和学生论文的素材。但无论这些问题最终被如何解决(如果解决了的话),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们的”庞贝城并非像某些旅游指南或小册子上所介绍的那样,是一个“在时空中冻结”了的正在正常运转的罗马城市。它是一个远为扑朔迷离而又引人深思的地方。它陷入一片混乱,一切都被打断,人们从中撤离又回过头来劫掠,它承载了各种不同的历史痕迹(和疮疤),这正是本书所要讲述的故事,并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庞贝悖论”:对于那里的古代生活,我们同时既知之甚多又一无所知。
的确,这座城市为我们所提供的真实人物及其生活的生动图景,远比罗马世界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我们在其中见到了倒霉的情侣(“织布工苏克凯苏斯[Successus]爱上了一个叫依瑞斯[Iris]的酒肆女郎,可她毫不领情”,一则潦草的涂鸦如是说)和不知羞耻的尿床人(“我尿在床上,搞得乱七八糟,我没有撒谎/但是啊,亲爱的主人,是因为你没有提供尿壶”,在一家寄宿客房的卧室墙面上,这则韵文如此自吹自擂)。我们可以追寻到庞贝孩童的足迹,其中既有蹒跚学步的幼儿,他们将几枚硬币戳进一座小房屋的主厅或中庭的新鲜灰泥里去,乐此不疲,至今还能在地面上看到70多处印痕(不经意间为我们测定这次装修的年代提供了绝佳的证据),也有在浴场门口闲得无聊的孩子,他们在够得着的地方随手画了些火柴人,或许是在等待还在洗浴的妈妈。更不用说那些铃声刺耳的马具、骇人的医疗器械(见图7)、从煮蛋器到蛋糕模具(如果我们没猜错的话,见图78)的各种古怪厨具,以及那些令人不快的肠道寄生虫,人们在2000年后仍然能在一个厕所的边缘发现它们的痕迹。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重新捕捉到庞贝人生活中的景象、声音与感受。

图7

尽管这类细节十分容易引起共鸣,可该城的全局图景和许多更基本的问题仍然完全令人困惑。我们面临着许多难题,除了城市人口总量,城市与海的关系同样令人费解。大家一致认同,海与庞贝城之间的距离在古代远比今天近得多(如今是2公里)。可现代地质学家还是无法测定到底近多少。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在紧挨着现代观光者进城的主要通道——城市西大门——的一段城墙上,有看起来明显是系船环的东西,仿佛大海波浪几乎直接就拍打着城市的这个角落(见图8)。唯一的麻烦在于,人们在再往西的地方也发现了罗马建筑,那是朝向大海的方向,它们不太可能是建在水底的。最有可能的解释再次回到了那些持续不断的地震活动上来。在火山爆发前的几百年中,庞贝城的海岸线和海平面必然发生了大幅变化,而人们在邻近的赫库兰尼姆发现了这种变化的清晰痕迹。

图8

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些基本的日期也存在争议——不仅是那场大地震的日期(有可能是公元62年,但也可能是63年),也包括火山爆发的日期。本书遵循的是传统记录,即公元79年8月24、25日,与小普林尼的记载一致。但也有证据表明灾难可能是在这一年更晚的时候发生的,在秋冬季节。首先,如果我们翻开小普林尼《书信集》( Letters )的各种中世纪手抄本,就会发现它们给出的火山爆发日期不尽相同(因为中世纪的抄写员几乎总是会抄错罗马日期和数字)。另外,城市废墟中残留着的数量惊人的秋季果蔬也证实了这一点,而许多遇难者似乎还穿着厚重的羊毛衣物,根本不是意大利炎热夏季的合适装束——但如果人们是为了穿越火山灰逃生才穿上这些衣服,那就不太能反映出季节和天气。更可靠的证据来自一枚罗马硬币,据其出土之处的情形来看,不太可能是掠宝者落在那里的。而专家判定这枚硬币的铸造时间最早也是公元79年的9月。
事实上,我们对庞贝城的了解既比想象中要多,又比我们所自认为的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