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学化的思维习惯是唯一有约束力的思维习惯,这种观点的灌输以及柏拉图的权威,使人们几乎不能充分意识到如下做法的严重后果:一个具体的社会范畴,如美德范畴(高尔吉亚将之明确定位在一个社会语境当中,即统治的语境当中
 )应当被还原为其骨架,就如同这骨架是它的本质似的。在数学的胜利以及每种胜利中,如在神谕的讯息中那样,回荡着某种神秘的号角声:倾听这号角声的人,已经忘却了最美好的东西。数学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它的全部统治范围仅限于它预先准备好的、被驯化了的东西。在《美诺篇》(
Menon
)中,苏格拉底所要求的是,将美德还原为不变的,但因此也是抽象的东西,它被从高尔吉亚的语境中抽取出来了,这种要求被表达为不证自明的,因而也是没有理由的、独断的,而且是不可反驳的。不过实际上,这种要求可能并非没有缘由,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绕开那种严重后果。这种要求在纯粹现象学的每一项含义分析的背后都能觅其踪迹,它早已是对一种明确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要求,即对精神的操作方式的要求,这种操作方式总是被有效地运用着,因为它抛弃同实事即认识对象的所有联系,柏拉图对这种联系还是试图保持敬意的。
[9]
这种方法概念所指的,是关于方法自己内涵(ihre eigene Implikation)的方法,是诉诸自身控制的主体的方法,是认识论还没有意识到的先声,并且,这种先声几乎不过是对方法的反思。然而,它所贯彻的这种模式,对于一种“第一哲学”(
)应当被还原为其骨架,就如同这骨架是它的本质似的。在数学的胜利以及每种胜利中,如在神谕的讯息中那样,回荡着某种神秘的号角声:倾听这号角声的人,已经忘却了最美好的东西。数学是一种同语反复,因为它的全部统治范围仅限于它预先准备好的、被驯化了的东西。在《美诺篇》(
Menon
)中,苏格拉底所要求的是,将美德还原为不变的,但因此也是抽象的东西,它被从高尔吉亚的语境中抽取出来了,这种要求被表达为不证自明的,因而也是没有理由的、独断的,而且是不可反驳的。不过实际上,这种要求可能并非没有缘由,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绕开那种严重后果。这种要求在纯粹现象学的每一项含义分析的背后都能觅其踪迹,它早已是对一种明确意义上的方法论的要求,即对精神的操作方式的要求,这种操作方式总是被有效地运用着,因为它抛弃同实事即认识对象的所有联系,柏拉图对这种联系还是试图保持敬意的。
[9]
这种方法概念所指的,是关于方法自己内涵(ihre eigene Implikation)的方法,是诉诸自身控制的主体的方法,是认识论还没有意识到的先声,并且,这种先声几乎不过是对方法的反思。然而,它所贯彻的这种模式,对于一种“第一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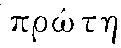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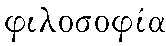 )概念来说是构造性的。正如这种哲学几乎不可能被设想为除方法以外的其他东西,方法即受控于规则的“道路”,也总是后继者对先行者的追随,这种追随是合法的:方法上的思考也要求一个第一者,由此这条道路不会中断并终止于偶然,第一者正是为了对抗偶然设计出来的。这种操作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以至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外在于其阶段序列的东西可能会打断它。因而,所有属于方法的东西都是无害的,从笛卡尔的怀疑一直到海德格尔对传统的充满敬意的解构。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只有规定了的而非绝对的怀疑是危险的;绝对怀疑通过方法目标让自己运行起来,而这目标又是在绝对怀疑之外产生的。胡塞尔在其认识论中将“悬搁”(
)概念来说是构造性的。正如这种哲学几乎不可能被设想为除方法以外的其他东西,方法即受控于规则的“道路”,也总是后继者对先行者的追随,这种追随是合法的:方法上的思考也要求一个第一者,由此这条道路不会中断并终止于偶然,第一者正是为了对抗偶然设计出来的。这种操作是预先计划好了的,以至于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外在于其阶段序列的东西可能会打断它。因而,所有属于方法的东西都是无害的,从笛卡尔的怀疑一直到海德格尔对传统的充满敬意的解构。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只有规定了的而非绝对的怀疑是危险的;绝对怀疑通过方法目标让自己运行起来,而这目标又是在绝对怀疑之外产生的。胡塞尔在其认识论中将“悬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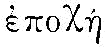 )同智者学派与怀疑论区分开来的做法
[10]
,就符合上述情况。怀疑仅是将判断转换为对如下一点的准备:在对普通人类知性的暗中同情中,假定前批判的意识被科学地证实了。然而同时,方法为了认识未知的实事,只能必须对之不断施以暴力,并且按照自身将他者模式化,这是起源哲学建构无矛盾性时的“原初矛盾”(Urwiderspruch)。作为方法的认识得到保护而免于反常、专断,并自认为是无条件的,这种认识的“最终目的”(
)同智者学派与怀疑论区分开来的做法
[10]
,就符合上述情况。怀疑仅是将判断转换为对如下一点的准备:在对普通人类知性的暗中同情中,假定前批判的意识被科学地证实了。然而同时,方法为了认识未知的实事,只能必须对之不断施以暴力,并且按照自身将他者模式化,这是起源哲学建构无矛盾性时的“原初矛盾”(Urwiderspruch)。作为方法的认识得到保护而免于反常、专断,并自认为是无条件的,这种认识的“最终目的”(
 )是纯粹逻辑的同一性。但因此,这种同一性将自己作为绝对来取代实事。如果没有方法的暴行,社会与精神、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将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随后,这赋予了同一性以不可抗拒性,反映在形而上学中便是一种超主体的存在。然而,从起源上来说,起源哲学(它只有作为方法才能得出真理观念)也是一种“谎言”(
)是纯粹逻辑的同一性。但因此,这种同一性将自己作为绝对来取代实事。如果没有方法的暴行,社会与精神、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将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随后,这赋予了同一性以不可抗拒性,反映在形而上学中便是一种超主体的存在。然而,从起源上来说,起源哲学(它只有作为方法才能得出真理观念)也是一种“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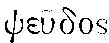 )。只有在历史的间断时刻,思想才会暂停下来,比如经院哲学强制的松动与近代资产阶级科学开端之间的时刻。在蒙田那里,思维主体的怯生生的自由同一种怀疑论相结合,这种怀疑论质疑方法即科学的万能。
[11]
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在方法的构造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裂表现为方法与实事之间的分裂。在劳动过程中,方法程序的普遍性是专门化的结果。精神已经被狭隘化为一种专门功能,为了自己的特权,它将自己误认成绝对者。巴门尼德诗作中的断裂,已经预示了方法与实事之间的差异,尽管那时还没有一种方法概念。两类真理直接并列出现,然而其中一个应当是单纯的假象,这两类真理的荒谬性十分明显地表达了最早形态的“合理化”的荒谬性。真理、存在与统一性,爱利亚学派的这些最高概念,是纯粹的思维规定,而且巴门尼德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正如他及其后继者至今仍在隐瞒的那样,它们也是关于如何思维的说明,即“方法”。相较于毕恭毕敬地盲从古人的做法,纳托普的非历史的新康德主义对古代哲学的这一方面的理解是更好的。实事还只是作为干扰内容处于方法操作的对立面,处于巴门尼德的太初之言(Urworte)的对立面:被他斥之为单纯的欺骗。巴门尼德所说的“意见”(
)。只有在历史的间断时刻,思想才会暂停下来,比如经院哲学强制的松动与近代资产阶级科学开端之间的时刻。在蒙田那里,思维主体的怯生生的自由同一种怀疑论相结合,这种怀疑论质疑方法即科学的万能。
[11]
但是,从社会角度来看,在方法的构造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裂表现为方法与实事之间的分裂。在劳动过程中,方法程序的普遍性是专门化的结果。精神已经被狭隘化为一种专门功能,为了自己的特权,它将自己误认成绝对者。巴门尼德诗作中的断裂,已经预示了方法与实事之间的差异,尽管那时还没有一种方法概念。两类真理直接并列出现,然而其中一个应当是单纯的假象,这两类真理的荒谬性十分明显地表达了最早形态的“合理化”的荒谬性。真理、存在与统一性,爱利亚学派的这些最高概念,是纯粹的思维规定,而且巴门尼德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正如他及其后继者至今仍在隐瞒的那样,它们也是关于如何思维的说明,即“方法”。相较于毕恭毕敬地盲从古人的做法,纳托普的非历史的新康德主义对古代哲学的这一方面的理解是更好的。实事还只是作为干扰内容处于方法操作的对立面,处于巴门尼德的太初之言(Urworte)的对立面:被他斥之为单纯的欺骗。巴门尼德所说的“意见”(
 )是感性世界超出思维之后的剩余;思维是真实的存在。与其说,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真正地提出了起源问题,却由于后来被滥用而扭曲了,不如说,在他们那里,断裂与异化已经纯粹地、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了,在柏拉图那里依然如此。这就是他们的高贵之处,但这样一种思想的高贵之处,依然没有掩饰其所见证的罪恶。然而,前进着的“理性”(ratio),作为前进着的中介,更为灵巧地掩盖了那种它不能控制的断裂。因此,它不断强化了起源的非真理性。柏拉图所教授的“分离”(
)是感性世界超出思维之后的剩余;思维是真实的存在。与其说,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们真正地提出了起源问题,却由于后来被滥用而扭曲了,不如说,在他们那里,断裂与异化已经纯粹地、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了,在柏拉图那里依然如此。这就是他们的高贵之处,但这样一种思想的高贵之处,依然没有掩饰其所见证的罪恶。然而,前进着的“理性”(ratio),作为前进着的中介,更为灵巧地掩盖了那种它不能控制的断裂。因此,它不断强化了起源的非真理性。柏拉图所教授的“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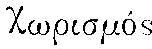 )学说反对的是爱利亚学派断裂的、不受概念限制的矛盾,这种学说已经将这两个领域一并考虑了,尽管这两个领域明显是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先于一切“分有”(
)学说反对的是爱利亚学派断裂的、不受概念限制的矛盾,这种学说已经将这两个领域一并考虑了,尽管这两个领域明显是相互矛盾的。这就是先于一切“分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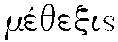 )的最初中介化,并且柏拉图的后期著作,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那样,竭尽全力地去弥合这条鸿沟。因为这条鸿沟是作为起源哲学之条件被纳入其自身当中的,然而,它们又不能容忍这条鸿沟。它提醒起源哲学注意自身的不可能性,注意其客观性源自主观的任意性。它们的闭合性本身就是一种断裂。因而,方法作为一种总体的任意性,其偏激的不宽容,反对所有背离它的任意性。它的主观主义建立起了关于客观性的规律。精神的统治只相信它自己是无拘无束的。然而,作为重新获得的统一性,它只是保证了分裂。它的确是一种绝对,是和解的假象,它同它所试图与之和解的东西分离开来,并且,正是在这种绝对性中,它才是无解的、与罪责关联的真实图像。恰恰是精神不能缺少的不断顺从(Gefügtheit)给起源哲学带来了灾难,同时从这种哲学中得出了自由的条件。被合并到第二重神话之中的精神渗透在去神秘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揭示出的,恰恰是第一者观念本身的非真理性。对于起源哲学来说,第一者必须变得更为抽象;它变得越是抽象,它所能解释的就越少,也就越不适于作为基础。为了完全的一贯性,第一者直接采用分析判断,它试图将世界转换为这些判断。第一者是同语反复,并且最终说不出更多的东西。第一者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将自身消耗殆尽,这就是它的真理,如果没有第一者哲学,我们将不能获得这一真理。
)的最初中介化,并且柏拉图的后期著作,就像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著作那样,竭尽全力地去弥合这条鸿沟。因为这条鸿沟是作为起源哲学之条件被纳入其自身当中的,然而,它们又不能容忍这条鸿沟。它提醒起源哲学注意自身的不可能性,注意其客观性源自主观的任意性。它们的闭合性本身就是一种断裂。因而,方法作为一种总体的任意性,其偏激的不宽容,反对所有背离它的任意性。它的主观主义建立起了关于客观性的规律。精神的统治只相信它自己是无拘无束的。然而,作为重新获得的统一性,它只是保证了分裂。它的确是一种绝对,是和解的假象,它同它所试图与之和解的东西分离开来,并且,正是在这种绝对性中,它才是无解的、与罪责关联的真实图像。恰恰是精神不能缺少的不断顺从(Gefügtheit)给起源哲学带来了灾难,同时从这种哲学中得出了自由的条件。被合并到第二重神话之中的精神渗透在去神秘化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揭示出的,恰恰是第一者观念本身的非真理性。对于起源哲学来说,第一者必须变得更为抽象;它变得越是抽象,它所能解释的就越少,也就越不适于作为基础。为了完全的一贯性,第一者直接采用分析判断,它试图将世界转换为这些判断。第一者是同语反复,并且最终说不出更多的东西。第一者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将自身消耗殆尽,这就是它的真理,如果没有第一者哲学,我们将不能获得这一真理。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