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哲学上的第一者必须总是已经包含一切,因而精神就同化了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并据为己有。精神把这些东西编目列表;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跳出这个网络,原则必须确保完备性。这些被编列起来的东西的可计数性(Zählbarkeit)变成了公理。可支配性造就了哲学与数学的联盟。这一联盟始于柏拉图将爱利亚学派传统、赫拉克利特传统与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结合起来,自此一直持续着。根据他的晚期学说,理念是数。这可不仅仅是异域思辨的放纵。从这个思想的特异性上就可以觉察出重要的东西。数的形而上学以具有示范性的方式执行了关于秩序的假设,凭借这种秩序,精神彻底网罗了被统治者,直到这一网络成为它所遮掩的东西自身。柏拉图中期对话中的苏格拉底认为,“一定要求助于某些概念,在探讨事物的真实本质时使用它们”
[7]
。但是,精神的面纱越是紧密,作为统治者的精神也就会变得愈加物性,正如在数中发生的那样。第一者概念统治了西方哲学的最初文献,并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中被主题化了。在这种第一者概念中,数与可计数性是一起被思考的。第一者已经自在地属于数的领域;谈及一种“第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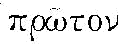 )时,必然会出现一种“第二者”(
)时,必然会出现一种“第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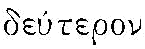 ),它必定是可计数的。甚至爱利亚学派的“一”(它应当是唯一的)的概念,也只有在同它所否定的“多”的关系中才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在巴门尼德诗作的第二部分中发现其关于“一”的论点是前后不一致的。然而,如果没有“多”的观念,“一”的观念是完全不能被规定的。在数中反映出来的,是能够进行组织与把握的精神同它所面对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精神为了将这对立面与自身同化,便将这种东西还原为未被规定的,之后才将它们规定为“多”。虽然精神依然没有将之说成是与自己同一的或可以还原为它自身的。但是,对于精神来说,这种东西已经变成类似的了。作为众多单位的聚合,“多”丧失了其特殊的质性,直到它被揭示为对抽象中心的抽象重复。定义数的概念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数自身的本质就是那些规定它的概念的形成机制。概念本身是归摄(Subsumtion),并由此包含一种数的关系。数是整理,也就是使非同一物在“多”的名义下,变成对于主体来说、对于一种统一性典范来说是可度量的。它们将经验的杂多抽象化。一旦作为统一性的意识与世界相对立时,世界就会变得混乱,而“多”便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如果统一性已经作为一种因素自在地包含在“多”当中(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多”就不能被思考),那么,数与复多性(Vielheit)的观念就需要“一”。当然,关于复多性的思想还没有通过综合将与主体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世界统一性的观念属于一个较晚的阶段,即同一性哲学的阶段。然而,自柏拉图以来,数字序列的连续性一直是所有体系之一贯性及其完备性要求的模型。由这种连续性已经可以导出笛卡尔式的、所有以科学自居的哲学都遵从的规则:不能略过中间环节。在之后的哲学同一性要求的独断预期中,这一法则将闭合性(Geschlossenheit)强加于待思考之物,哲学是否应当获得那些待思考之物,取决于这种闭合性。精神与自身的同一性,以及随后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通过单纯的操作被投射到实事上,而且这操作愈是严苛,实事就会愈加整洁和严格。这就是“第一哲学”的原罪。恰恰是为了加强连续性与完备性,它必须清除一切与它判断不相符的东西。哲学体系性(Systematik)的贫困最终使哲学体系(Systeme)矮化为怪物;这种贫困并非哲学开始衰落时才有的征兆,而是早已被操作本身以目的论的方式设定了的,在柏拉图那里,这种操作已经无可反驳地要求,美德必须通过还原为其图式(Schema)来得到证明,就像一种几何图形那样。
[8]
),它必定是可计数的。甚至爱利亚学派的“一”(它应当是唯一的)的概念,也只有在同它所否定的“多”的关系中才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在巴门尼德诗作的第二部分中发现其关于“一”的论点是前后不一致的。然而,如果没有“多”的观念,“一”的观念是完全不能被规定的。在数中反映出来的,是能够进行组织与把握的精神同它所面对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精神为了将这对立面与自身同化,便将这种东西还原为未被规定的,之后才将它们规定为“多”。虽然精神依然没有将之说成是与自己同一的或可以还原为它自身的。但是,对于精神来说,这种东西已经变成类似的了。作为众多单位的聚合,“多”丧失了其特殊的质性,直到它被揭示为对抽象中心的抽象重复。定义数的概念之所以是困难的,是因为数自身的本质就是那些规定它的概念的形成机制。概念本身是归摄(Subsumtion),并由此包含一种数的关系。数是整理,也就是使非同一物在“多”的名义下,变成对于主体来说、对于一种统一性典范来说是可度量的。它们将经验的杂多抽象化。一旦作为统一性的意识与世界相对立时,世界就会变得混乱,而“多”便在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是,如果统一性已经作为一种因素自在地包含在“多”当中(如果没有这个因素,“多”就不能被思考),那么,数与复多性(Vielheit)的观念就需要“一”。当然,关于复多性的思想还没有通过综合将与主体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世界统一性的观念属于一个较晚的阶段,即同一性哲学的阶段。然而,自柏拉图以来,数字序列的连续性一直是所有体系之一贯性及其完备性要求的模型。由这种连续性已经可以导出笛卡尔式的、所有以科学自居的哲学都遵从的规则:不能略过中间环节。在之后的哲学同一性要求的独断预期中,这一法则将闭合性(Geschlossenheit)强加于待思考之物,哲学是否应当获得那些待思考之物,取决于这种闭合性。精神与自身的同一性,以及随后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通过单纯的操作被投射到实事上,而且这操作愈是严苛,实事就会愈加整洁和严格。这就是“第一哲学”的原罪。恰恰是为了加强连续性与完备性,它必须清除一切与它判断不相符的东西。哲学体系性(Systematik)的贫困最终使哲学体系(Systeme)矮化为怪物;这种贫困并非哲学开始衰落时才有的征兆,而是早已被操作本身以目的论的方式设定了的,在柏拉图那里,这种操作已经无可反驳地要求,美德必须通过还原为其图式(Schema)来得到证明,就像一种几何图形那样。
[8]
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