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将持存之物谎称为真实的,真理的起点就变成了欺骗的起点。
 持存之物比消逝之物更真实,这是一种谬论。那种将世界改造为可供支配的财富的秩序佯称自己是世界本身。只有无视概念所掌握的东西的短暂的规定性,概念的不变性才是可能的,而这种不变性与自在存在的不可变性相混淆了。那位现象学的行家里手
持存之物比消逝之物更真实,这是一种谬论。那种将世界改造为可供支配的财富的秩序佯称自己是世界本身。只有无视概念所掌握的东西的短暂的规定性,概念的不变性才是可能的,而这种不变性与自在存在的不可变性相混淆了。那位现象学的行家里手
 能够运用怪诞诡计,来对付他所谓的关于不朽的问题,因为他虽然坚信每一个个别灵魂是会毁灭的,但他又因如下一点而沉静:每一个这种灵魂的纯粹概念,即它的个体“埃多斯”(
能够运用怪诞诡计,来对付他所谓的关于不朽的问题,因为他虽然坚信每一个个别灵魂是会毁灭的,但他又因如下一点而沉静:每一个这种灵魂的纯粹概念,即它的个体“埃多斯”(
 )是不腐的。这种无能的诡计,因其拙劣而只表明了被掩藏在宏大思辨深处的东西。黑格尔与尼采都曾致敬的赫拉克利特
[22]
还是将本质等同于消逝之物;而自理念学说的第一次真正表述
[23]
以来,消逝性就被归入了显现、归入了“意见”的王国、归入了假象,而永恒性则留给了本质。只有尼采对此表示反对:“哲学家们的另一种特异体质危险性同样不小: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那最后到来的东西——可惜!因为那根本就不该到来!——把那些‘最高的概念’,这就是那些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现实那蒸发着的最后的雾气,作为开端设置在开端。这又是他们进行崇拜的表达方式: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里长出,根本不允许长成……教诲就是:所有第一等级的东西,必须是其自身的原因(causa sui)。来源于其他被视为异议,视为价值的不可靠。所有最高的价值均隶属第一等级,所有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者,善,真实,完美——这一切不可能是生成的,也就一定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过,这一切也不可能彼此不同,不可能自相矛盾……那最后的、最单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起始,自因,最最真实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
[24]
为了生命,尼采所认为的“病蜘蛛”
)是不腐的。这种无能的诡计,因其拙劣而只表明了被掩藏在宏大思辨深处的东西。黑格尔与尼采都曾致敬的赫拉克利特
[22]
还是将本质等同于消逝之物;而自理念学说的第一次真正表述
[23]
以来,消逝性就被归入了显现、归入了“意见”的王国、归入了假象,而永恒性则留给了本质。只有尼采对此表示反对:“哲学家们的另一种特异体质危险性同样不小:这就是混淆始末。他们把那最后到来的东西——可惜!因为那根本就不该到来!——把那些‘最高的概念’,这就是那些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现实那蒸发着的最后的雾气,作为开端设置在开端。这又是他们进行崇拜的表达方式: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里长出,根本不允许长成……教诲就是:所有第一等级的东西,必须是其自身的原因(causa sui)。来源于其他被视为异议,视为价值的不可靠。所有最高的价值均隶属第一等级,所有最高的概念,存在者,绝对者,善,真实,完美——这一切不可能是生成的,也就一定是其自身的原因。不过,这一切也不可能彼此不同,不可能自相矛盾……那最后的、最单薄的、最空洞的东西被设置为起始,自因,最最真实的存在者(ens realissimum)。”
[24]
为了生命,尼采所认为的“病蜘蛛”
 的亵渎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但这种亵渎恰是因生命本身的野蛮而犯下的。他从“第一者谎言”(
的亵渎是“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但这种亵渎恰是因生命本身的野蛮而犯下的。他从“第一者谎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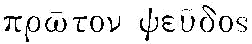 )中解释出的、作为精神疾病的灾难,源自实在的统治。胜利者以更优者自居,以此来编纂胜利。按照成功的残暴行为,被征服者应当相信,幸存者比已逝者更具正当性。为了使思想能够将幸存者易容(transfigurient)为真理,幸存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死去,为的是被圣化为永恒:“您问我,哲学家都有哪些特异体质?……比如他们缺乏历史的意识,他们对于生成之表象自身的憎恨,他们的埃及主义。当他们从永恒的视角出发(
sub specie aeterni
),对一件事进行非历史化时——当他们把它做成木乃伊时,自以为在向一件事表示尊敬。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处理过的一切,是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生动活泼地出自他们之手。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当他们朝拜时,他们在杀戮,他们在制作标本——当他们朝拜时,对一切的一切造成生命危险。死亡,变化,年岁,如同生育和生长,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的不生成;生成的不存在。现在,他们全都,甚至带着绝望,相信存在者。因为他们无法弄到它,他们就寻找理由,别人为何对他们隐瞒它。”
)中解释出的、作为精神疾病的灾难,源自实在的统治。胜利者以更优者自居,以此来编纂胜利。按照成功的残暴行为,被征服者应当相信,幸存者比已逝者更具正当性。为了使思想能够将幸存者易容(transfigurient)为真理,幸存者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必须死去,为的是被圣化为永恒:“您问我,哲学家都有哪些特异体质?……比如他们缺乏历史的意识,他们对于生成之表象自身的憎恨,他们的埃及主义。当他们从永恒的视角出发(
sub specie aeterni
),对一件事进行非历史化时——当他们把它做成木乃伊时,自以为在向一件事表示尊敬。几千年来哲学家们处理过的一切,是概念的木乃伊;没有什么真实的东西生动活泼地出自他们之手。这些概念偶像的侍从,当他们朝拜时,他们在杀戮,他们在制作标本——当他们朝拜时,对一切的一切造成生命危险。死亡,变化,年岁,如同生育和生长,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的不生成;生成的不存在。现在,他们全都,甚至带着绝望,相信存在者。因为他们无法弄到它,他们就寻找理由,别人为何对他们隐瞒它。”
 但同时,尼采低估了他所看透的东西,因此,他依然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思想的自身反思依然有必要摆脱这一矛盾。“从前,人们把变化,转换和生成,统统看成假象的证明,看成某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事物存在的标记。今天,我们相反地看到,恰恰是理性的偏见迫使我们,设定统一,同一,持续,实体,起因,物性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自己卷入谬误,强制我们陷于谬误;根据我们这里的一种严格的复核,我们对此十分肯定,即此处有谬误。”
但同时,尼采低估了他所看透的东西,因此,他依然处于一种矛盾之中,思想的自身反思依然有必要摆脱这一矛盾。“从前,人们把变化,转换和生成,统统看成假象的证明,看成某种会把我们引入歧途的事物存在的标记。今天,我们相反地看到,恰恰是理性的偏见迫使我们,设定统一,同一,持续,实体,起因,物性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自己卷入谬误,强制我们陷于谬误;根据我们这里的一种严格的复核,我们对此十分肯定,即此处有谬误。”
 关于持存之物的形而上学,从与物的显现相对立的物之恒常那里获得了它的认识基础,并且,尼采所恢复的这种启蒙了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是休谟式的批判)瓦解了这种形而上学提出的关于物的假说。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在被统治者那里没有一种固定之物(Feste)的因素,那么固定之物要反对混乱并控制自然的企图从来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否则,这种因素将不断证明主体在撒谎。以怀疑的方式完全拒斥那种因素,并只将它定位在主体中,这表现出的主体的傲慢,并不比它将概念秩序图式绝对化时表现出的傲慢少。在这两种情况中,主体与客体已经凝结为“基础”(
关于持存之物的形而上学,从与物的显现相对立的物之恒常那里获得了它的认识基础,并且,尼采所恢复的这种启蒙了的批判(从根本上来说是休谟式的批判)瓦解了这种形而上学提出的关于物的假说。但是,这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如果在被统治者那里没有一种固定之物(Feste)的因素,那么固定之物要反对混乱并控制自然的企图从来都不可能获得成功。否则,这种因素将不断证明主体在撒谎。以怀疑的方式完全拒斥那种因素,并只将它定位在主体中,这表现出的主体的傲慢,并不比它将概念秩序图式绝对化时表现出的傲慢少。在这两种情况中,主体与客体已经凝结为“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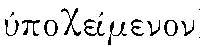 )。进行反思的精神为了其绝对权力而将世界贬低成一种单纯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就像它建立起来并对之崇拜的宇宙那样。
)。进行反思的精神为了其绝对权力而将世界贬低成一种单纯的混乱,而这种混乱恰恰就是这种精神的产物,就像它建立起来并对之崇拜的宇宙那样。
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