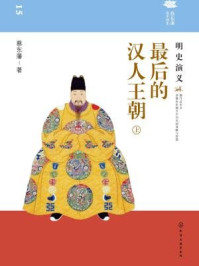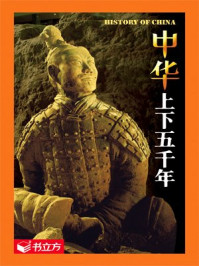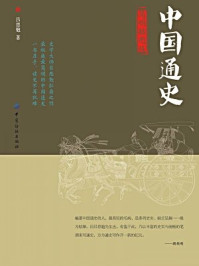商代已经有了完整而成熟的文字,这已为地下发掘所充分证明了。商代人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鬼神,把卜问的结果记录在甲骨上,这就是甲骨文。这种文字,在民间长期有着一个成语化的俗名——
长期以来,人们把埋在地底下后被发掘出来的骨片神秘地称之为“龙骨”。又因为它上面的文字是刻画在甲骨上的,又称“契文”,合起来被叫做“龙骨契文”。
龙骨契文的发现,还有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呢!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秋,时任翰林院编修的王懿荣突然病倒了。他患的是恶性风寒疟疾,这种病很凶险,用了不少药,总是见不了效。一次有人给他从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买了一味中药叫龙骨,吃了,病立见好了许多。于是,他就继续服用此药。病中无事,他就细细的翻看这些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达仁堂的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确信原来那些“龙骨”上斑斓的条纹图案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人工刻画出来的。这是个大发现,他就开始在京城大量收购“龙骨”,并穷根溯源,追寻到了“龙骨”的源头是在河南一个叫小屯村的地方。经过研究,王懿荣断定所谓“龙骨”就是殷人用来占卜的卜骨和卜甲,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这也就是史书上说的“殷人有典有册”的典册。
由于这一发现,原先小屯村人磨碎了随便入药、价廉的龙骨,一下身价百倍了,王懿荣也因此而赢得了“甲骨文之父”的美誉。
商人与夏人不同。夏人面对现实,面对生活,比较的实在,注重于直面人生。而商人特别的尊重神灵,尊上帝,尊祖先神,尊自然神,遇事先要卜问鬼神,后再决定人世间的礼俗,这叫做——
《礼记·表记》上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心目中的神灵有上帝、祖先神和自然神三大类。所谓“鬼”主要指祖先神。
为了沟通人与鬼,就要进行卜问。“卜”是一种相传成习的仪式,“问”是求得鬼神的旨意,指明人应该怎么做的方向。占卜的面极为广泛,有的内容是问天气的,有的是问农作物收成的,也有问病痛、问生儿育女的,更有大量的是问打猎、作战、祭祀这样一些在当时看来是“国之大事”的。殷人习惯于把占卜的结果记录在甲骨上,这就形成了所谓的“甲骨文”。
制作甲骨文有严格的程序和步骤。一是选取兽骨和龟甲。安阳当地出土的卜用兽骨主要选自牛的肩胛骨,少数选用羊、鹿、猪的肩胛骨。卜龟骨除当地产的外,有的还来自南方长江流域。二是整治甲骨,包括对牛肩胛骨的脱脂和对龟甲的铲平。三是对甲骨进行烧灼。用一根烧热的圆柱形树枝对甲骨靠近加热,直至甲骨上出现裂纹,这些裂纹通常称为“兆”。四是把占卜的“兆”的内容演化成文字刻录在甲骨上,这就是卜辞,也就是甲骨文,它通常刻在“兆”的旁边。
商人崇拜天,就要了解天,研究天,于是,在甲骨文中就有了诸多关于“天”的记述,以至于有人世间最早的如是记录——
甲骨文记录了商人在天文方面的巨大成就。其中已经有了日蚀和月蚀的明确记录。《佚》374中,有“日夕有食”的明确记述。这里,有食的“食”,即“蚀”。“日夕”,也就是太阴偏西的时候,发生了日蚀。在时间上,写得很精准。《甲骨文合集》11484,有某月六日,月亮偏西的时候,发生了月蚀现象的明确记录。《英国所藏甲骨集》886,有“庚申月有食”的记录,时间上也很确定。
甲骨文存在于三千多年前。在甲骨文中就有明确的日蚀和月蚀的记述,说明我国当时在天文方面的成就处于领跑世界的地位。国外关于日食的最早记录发现于古巴比伦的文献,时间是在公元前911年。而中国最早的日食记录却是在殷墟甲骨文中记载的。殷商甲骨卜辞里明确的“日食”“日夕有食”俯拾皆是。有学者认为,殷商晚期由“食”变为“戠(织)”是中国古人天文知识以及科学精神的巨大飞跃——“日食”代表某种超自然力量在吞食太阳,属于认识的原始阶段;而“日织”的“织”字,就是把天体的运行比作一台纺织机,“织”代表经纬线的来回交织。这说明商人已经发现,日食是由于天体运行互相交织形成的。这实在是从迷信到科学的转变,起码也是站在了科学的门口。不管是“日食”还是“日戠”,中国商代对天象的认识程度,都是毋庸置疑的。它至少比西方同类的记述要早了五六百年。
在商人的心目中,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天、地、人三位一体,完全是相容、相依、相通的。基于这样的认识,就有了融天、地、人于一体又以人为本的记时法。基于中国人特有的记时方法,就衍生出了一年十二月和六十年为一甲子的概念,在一月中还分出了上中下三旬。中国式记时被称为——
我们的古人真聪明,他们以天为“干”,以地为“支”,天地相配,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天干地支”说。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有十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与地支相配,形成从甲子、乙丑,到壬戌、癸亥六十个干支。六十干支循环往复,行之无穷,既可记日,又可记月,还可记年。这种记时法,有利于农业,一直沿用到当今。
这是甲骨文留给我们的一份重大的文化遗产。
基于天干地支,甲骨文中已有了十二月的记述,此外还有“十三月”的说法,说明当时已懂得置闰。在月之下,商人又懂得置旬,一旬为十天,在一月中还区分出了一旬、二旬、三旬(即现今的上旬、中旬、下旬),一旬中多几日,又有“旬有几日”的说法。这是一种相当严密,也是相当先进的阴阳合历的历法。
商人迷信,相信人死后将进入另一个世界。为了让死去的人在另一个世界中过上更加美满的生活,人们常会在坟墓中安放诸多的随葬品。在商人的墓葬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数量相当可观的——
“以人殉葬”,指古代葬礼中以活人陪葬的陋俗,这是一种残忍而野蛮的宗教行为,后人以此形容残暴。它出现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奴隶制时代。人殉,指的是用活人为死去的氏族首领、家长、奴隶主或封建主殉葬。被殉葬者多是死者的近亲、近臣、近侍,以及战争中的俘虏等。人殉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古代丧葬仪式。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商品交换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引起氏族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因此,这种宗教活动的出现,同私有制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每次殉多少人,并无具体执行标准,但有一个大概。墨子曾说过,天子死后,殉葬者多则数百人,少则也有数十人,将军大夫级别的,殉葬者多则数十,少则几个。
我国人殉最盛的时代当是商周时期。据考古发掘,商代贵族大墓中都有人殉。考古学家对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一座殷代大墓的发掘发现,在墓道、墓室以及祭祀坑中,到处都是白骨累累的殉葬者,其人数有六七十人之多。专家分析其操作过程是:先将墓室下的人殉者活埋后再填土夯平,墓主人下葬后留下墓道,再用此墓道将其余人殉者10人、20人一行反绑着牵入墓道再陪葬。
甲骨文中有“鬼”字,其字形如人字上头一个田字,《说文》注曰:“人之所归为鬼。”也就是人死后归于(埋葬)田园,就变成了鬼。在迷信的商人看来,鬼与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于是就要有殉葬品。殉葬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起始于殷商时代的。
河南安阳小屯村及其附近的遗址,发现有殷王大墓九座,在大墓的东区,又发现有附属于大墓的小墓1242座。而在这些墓穴中,可以说没有一座是没有人殉的。
就以安阳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来说,此墓已被盗过,但基本情况还是依稀可见的。如以原墓复原看,这里的殉葬人数当在三四百人之间。看来,墨子明确指出的“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的说法,完全是符合实际的。
在大墓的东区,附属于大墓的小墓有一千二百余个。这可能是基层官员及普通百姓家的墓地。这里也普遍存在着殉葬现象。殉葬者中有全躯人骨的,也有不少无头肢体,也有无肢体的头骨。这些殉葬者有的是成年人,但更多的是未成年人,还有连天灵盖都未长满的一二岁的婴儿。这一千多小墓,殉葬者少说也有二三千人。
社会发展到当今之世,实指的殉葬现象已在世界上灭绝了。但是,已经成语化的“殉葬”、“殉葬者”、“殉葬品”这样一些词汇还活着,还时时会给人以人文的思索。
如果说夏代是中国农耕社会的起始期的话,那么,商代则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发展期和成熟期。在商代,“井”的开掘已十分普遍,人们习惯于聚“井”而居,国家也依“井”而管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
“井”来源于井田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井,表示田地规划得非常整齐,阡陌纵横,后引申为有条理。井井有条,形容条理分明,整齐不乱,引深为办事有条有理。
“井井有条”这种说法起始得很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作品中已作为成语使用。而这一成语又与“井”的发明与使用密不可分。“井”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易经》的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十八卦专设一《井卦》。井的发展历程十分漫长。开初可能只是“掘土汲水称井”,显然制作是很粗糙的,后来是所谓“古者伯益初作井”(《说文》),伯益是协助大禹治水的一位了不起的英雄,治水中发明凿井,并取水食用,那是完全可能的。到了殷商时代,凿井不只与吃水问题联系在一起,还涉及农田水利。《世本》上有记载,说商汤时大旱,“伊尹教民田头凿井灌溉”。到这时,井井有条才有了实际的意义。
现在已经发现的甲骨文中有井字,而且井字反复出现。井字是像物字,“像井口形也”。这时的井已具有管理功能。《甲骨文合集》18770有“百汫”之说,意思是从井中引出的水分成百条细流(即“百汫”)溉入农田之中,这可说是“井井有条”之一义。同时,通过井的开凿与管理又把农户组合起来,管理起来,即《说文》以为的“井,八家一井”,这是最初的户籍制度,此“井井有条”之二义也。荀况《荀子·儒效》有载:“井井兮其有理也。”
井井有条的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商代农业的发展,甲骨文中有各种谷物名,有很奇特的“丰”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句成语——
五谷丰登,其意思是指年成好,粮食丰收,引自《六韬·龙韬·立将》:“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登,社稷安宁。”
现在常用的“丰”字,是简笔字,原本的繁体字应写作“豐”。“豐”的下半部是一个“豆”字,是祭祀用的礼器。“豐”的上半部是放在礼器上的祭品,那些祭品放得满满当当的,上半部中的两个“丰”字形符号,高高大大的,在甲骨文中都要高于上半部的边界线,《说文》以为:“丰,豆之丰满者也。”甲骨文中“豐”字的反复出现,说明农业收获有积余的“五谷丰登”景象在商代是存在的。
商代卜辞中重要农作物的名字都有了。甲骨文中的“麦”是个像物字,有根、叶、茎、穗,很传神。甲骨文中有“黍”字,也是象物字,它与稻不同,稻是合穗的,黍是散穗的,从字形上也可以看出来。甲骨文中有“米”字,《说文》释为“米,粟实也”,也就是粟加工成不带壳的粟实后称米,与后代人的说法基本一致。甲骨文中有“豆”字,是豆类食物的总称。甲骨文中还有了一个“農”字,即农业的农字的繁体字。该字中的“辰”,指的是农具。上半部的“曲”字,像是农夫手持农具“在田中耕作之形”。可见,商代人已将农业当作生产的主业。
商代人的农业发展得如何?这可从甲骨文中的“穑”字那里得到解答。有专家解释“穑”字时说:“从禾,从田。从禾者,像仓库中装满禾谷,以示仓满。故田夫称为穑夫。”当时仓库中已“装满禾谷”了,岂不正好说明是五谷丰登吗?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养殖业的发展。在商代,家庭养殖业上取得的成就也是惊人的。可以说,后世家庭养殖的家畜门类,在那时已经基本齐全了,而且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家畜不只用之于膳食,还大量用之于祭祀,真可谓——
六畜兴旺,泛指农耕社会中的各种家畜繁衍生息,兴旺富庶。六畜指马、牛、羊、鸡、狗、猪。语出《管子·牧民》:“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六畜,亦称六牲。《周礼·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郑玄注:“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也。”事实上,以畜养角度定名,称六畜。以饮食角度定名,则称六食或六膳。而如果从祭祀角度定名,则称为六牲了。
在甲骨文中,牛、马、羊、豕、犬、鸡六畜多次出现,而且写法相当定型,表现了商代养殖业的成熟性。出土文物更是证明了商代六畜的兴旺。在安阳殷墟,先后发现了31座车马坑,有两马拉车的,也有四马拉车的。马车有的是代步工具,有的则是战车。商代牛的饲养规模很大,《甲骨文合集》1027有“册千牛”的记载,就是用一千头牛来祭祀上帝和祖先。牛除用来祭祀和食用外,还用来拉车。商人很早就养羊,历史上有著名的“丧羊于易”的故事。商代的养猪业非常发达,在商代遗址中,动物骨骸一直以猪骨为主。商代常以犬祭祀,甲骨文中有以百犬祭祖的。养鸡在商代也很普遍,还有吃鸡蛋的记录。
商代除了饲养上述的六畜外,还饲养有鹿、鸭、鹅等。在饲养过程中,还逐步设立了专门的畜牧业管理机构。
在十分兴旺的六畜各业中,何者为主业呢?毫无疑问当推猪了。猪的饲养历史长达近一万年,而且饲养面特别的广。考古资料证明,到了商代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有养猪的习俗,并渐次形成了这样的民族化的观念——
“家”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字眼,很多人一生漂泊在外,但到了最后都还是要“叶落归根”,回到故土。“家乡”、“家国”这些词语曾经牵动着多少游子和古今仁人志士的心。据《周礼·小司徒》注:“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可见“家”至少由夫妇两人构成。我们常说的“成家”其实就是指结婚,一男一女相互结合的过程。人们常要问:为什么“宝盖头下有头猪”就是家了呢?
那是因为远古时代,人们茹毛饮血,后来才懂得了养殖动物,最初被圈养的动物就包括“猪”。人们把猪圈养在屋里,有了一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一个“家”了。于是“说文解字”做了形象的解读。古人“家”的原始观念是很有特色的。古人把“家”字,写成“宀”下面一个“豕”字。“宀”是房屋的象形,“豕”就是我们日常说的猪。房屋造来住人的,但是在远古的祖先看来,如果屋中没有“豕”,还是不能算家。“有猪为家”的观念根深蒂固。再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没有别的收入,猪就是财富的象征。在郑州二里岗出土的三万多块动物骨料中,大约有一半是猪骨,按当时那里的人口计算,大约一户一猪是不为过的。
猪不只为人类提供了主要的肉食之源,它还是人类的守护神。在强敌如林的现实世界上,人时时会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种种威胁,人一旦与猪生活在一起,安全系数大增。猪耳大,福大,听觉灵敏。一旦猛兽来袭,它就能发出一种浑厚有力、让对手生惧的吼声。这对人是一种警示,对来犯者是一种抗拒。正是在这基础上,人猪建立起了密切的关系。商代人已懂得圈养动物,所谓“圈牛于牢,圈羊于宰,圈犬于突,圈马于厩,圈豕于家”。有资格与人一起居于家中的,唯有猪也。
家羊的饲养大约可追溯到距今七千年前,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就发现了数量相当可观的羊的牙齿、羊的头骨的化石和陶塑的羊头。到了距今五千来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羊骨的遗址和数量明显增多。到了商代,不只吃羊肉、喝羊乳、穿羊皮成为一时之时尚,而且用羊祭祀天地,称为少牢,也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羊大为美”,有多种解读,多指羊肥,因为羊是人类生存的重要需求对象,羊越肥越能满足人的某种需求。
羊初始是用于膳食,后来则常用来祭祀。《甲骨文合集》20699有“五百宰”的记录,就是一次祭祀就用了五百头羊。《屯南》4404说“御父丁百小宰”,就是说,为了祭祀商王父丁,用了一百头小羊羔。为何商代人那样重视以羊为祭呢?《说文》以为,“羊,祥也”。羊又与吉祥如意的“祥”同声。人们一听到羊的叫声,就会联想到吉祥。因此,十分迷信的商代人就自然而然地会把羊抬上祭桌了。
由羊的吉祥形声,进一步推演,就有了“羊大为美”的观念。甲骨文中有“羊”字,也有推演而得的“美”字。《说文》:“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义。”从膳食的角度讲,羊越大,就越肥美和甘美,这是从口味好来说,后来泛化为美学意义上的“美”。“美与善同意”,这样又把泛化了的“美”,与道德意义上的“善”合在一起了。
在商代,大自然中的象与龟两物被视为灵物。当时黄河中上游地区气温要比当今高得多,大批的大象穿行在黄土高原上,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喜气和吉祥。“商人服象”,人与象之间的互动是中原大地的一道特有的风景线。中原大地也盛产龟。龟的长寿,龟甲的斑斓条纹,都给人以无穷的想象。久而久之,商代就形成了如是一说,叫——
象龟祥瑞,说的是大象和乌龟都是灵物,它们会给人类带来吉祥如意的瑞气。三代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比现在要湿润,气温也高,大量的大象穿行在山地和平原地带,给人们带来一道特殊的风景线。象巨大的身量、力大无比的劳作力,都予人以一种神异的感受。象字在甲骨文中反复出现,当时的人们把河南地区称为“豫”——该字的一边是代称人的“予”字,另一边是一个“象”字,可见象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简直可以说是把人与象合为一体了。
商代人已经学会训象,或训其运输、耕田,或训其打仗等。象是现代地球上最大的陆生动物,其生活圈越来越小。近年来,在湖北天门石家河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中发现大批种类繁多的鸟兽类小型陶塑,其中有多种造型生动的泥红陶象塑,可以编队成群。这正说明江汉平原北部的山林地区,早在4000多年前有象类生存出没其间。约千年后的商代,这种生态仍然存在。《吕氏春秋·古乐》谈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说明商人有时打仗还出动象队。
《吕氏春秋·古乐》中说到“商人服象”,服象就是训象。《甲骨文合集》37364中说到“获象十”,一次能捕获十头大象,可见当时象数量之多,又可见猎象者的技艺之高。象可用来运输、耕地(所谓“象耕”),还可用来作战。当时还用象军打过东夷。商王对象很重视,重视到崇拜的程度,常常亲自巡视大象。《甲骨文合集》中多次说到“王省象”,一些学者将“省”释为巡视,其实,更确切地解读当是礼拜,对灵气十足的象送去敬意和祭品。1978年在河北武官村发现一象坑,内葬有一人一象,这也是当时的人将象神灵化的一个明证。
酒是商代社会的一道风景线,酒的门类多,有粟米酒、醴酒、果子酒、药酒。喝酒的人也很多,早期还得以控制,后来则是——
《书经》中有一篇“酒诰”,是周公代表成王告诫康叔应严厉戒酒之词。文中说到了商代的民风。说商的先哲,指的是成汤到帝乙,敬畏天命和民心,把心放在政事上,还“不敢自暇自逸”,“罔敢湎于酒”。可是,到了商代的晚期,统治腐败不堪,民风也败坏到了极致。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人对饮酒误事的反思亦大量存在。如《尚书·酒诰》中这样记载:“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罔爱予殷,惟逸。”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说,当时不只官僚都“湎于酒”,普通老百姓也各自自由自在地在那里饮酒享乐,酒气冲到天上,上帝也闻到了酒腥,最后决定取消殷王朝的天命。道理很简单,商王朝之亡,全在于一个“逸”字上。
商王朝时的饮酒成风,可以从当时的墓葬中得到佐证。1969年到1977年对殷墟西区墓地进行了发掘。那是一块平民墓地。在其中的第八墓区的55座墓中,随葬品基本上是酒器觚和爵。因为是平民,这些酒器不是青铜制品,而是陶制品。这反映了当时殷民的意念:活着时以酒为乐,死后还是要以享用酒食为福。
中国习惯地称善于交易的人为商人。而士农工商中的商人,与历史上说的商代人有何干系呢?有关系的,从历史的某些踪迹看,商代人的确善于经商。那时他们已懂得——
商王朝灭亡后,周统治者把殷人中的部分人员赏给有功的周王室人员。最著名的是分给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很显然,这些“六族”“七族”中人,大多是以“匠”(手艺)著称的。举例来说,条氏、索氏,当是不同类别的绳索工匠;萧氏,当是乐器工匠;长勺氏、尾勺氏,当是不同品类的酒器工匠;陶氏,当是制陶工匠;施氏,当是制作旌旗的工匠;繁氏,当是制作马缨的工匠;樊氏,当是篱笆工匠;锜氏,当是制凿工匠。
可以想见,当时手工业的分工已经相当细致,不只是有了专人专业,还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工匠族群。匠人匠族的出现,是商代商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些手工业者也就是后来称作“匠人匠族”的,必然要以自己的产品来和别人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许多文献表明,商时城市中普遍设有交易市场。《六韬》记载说:“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百里,是说城市的规模之大,九市,是说城市中市场之多。《帝王世纪》也说商代“宫有九市”。
在交易市场靠何物实施交易呢?看来他们靠的是一种宝贝——海贝。此贝作为当时的一种货币。其要求贝如白雪或是牙齿那样洁亮,于是引出了“悬珠编贝”的成语,意说悬挂的明珠,编排整齐的贝壳,以此形容人眼睛明亮美丽和牙齿洁白整齐。在东汉班固《汉书·东方朔传》有“目若悬珠,齿若编贝”。
考古发现,商代的墓葬中经常随葬海贝,即使寻常百姓家也如此。殷墟西区的939座中小墓中,有340座葬有海贝,而且这些都是平民百姓的墓葬。1958年到1961年殷墟发掘的中小墓葬302座,其中也有相当部分随葬有海贝。大海离殷都安阳有千里之遥,在平民百姓手中会有那么多海贝,显然当时海贝已经充当了商品交易中介的作用。普通的海贝,变成交易中的宝贝,这在商业发展中跨出了很大的一步。
姜子牙可是商周交替时期的一个大名人。人们知道得较多的是他在渭水边遇到了周文王,后来成了文王师,再后来助武王灭殷,封于齐。殊不知,他在此前可是个行走商道的商人。他曾对人说,他晚年政坛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早年的——
商朝末年,建立了商朝的殷商部族很善于买卖,他们常到毗邻周族的地区去做买卖。久而久之,在周人的心目中,做买卖的就是商人。后来,周武王灭商,殷商遗民的政治地位从此一去不再复返,他们便更多地投身到商业活动中去。传说,由此,周人便习惯地用“商人”这个名称去称呼做买卖的人。这种称呼,本身就充满了不屑与鄙视的口吻。因歧视被征服了的商人遗族,所以连累进而歧视到当时所有从事买卖活动的商人,这当然只是一种学术见解。
商业和商人,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受到鄙视,但是,它们却是人类社会经济生活趋于繁荣的标志。姜子牙在还没有发迹之时,有过一段经商的人生历程。《盐铁论·讼贤》是这样记述的:“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当此之时,非无远筋骏才也,非文王、伯乐莫知之贾也。”这里的“远筋骏才”是指有远大志向和特殊才干的人。这段话是说,当年姜子牙穷困的时候,背负着商品在朝歌到孟津的商道上经商,来往于商周之间,十分辛苦,连那些头发散乱(所谓“蓬头”)的贫民都聚在一起嘲笑他,以为他是不会成功的。实际上,他从事艰难的经商活动,不是说他没有志气,也不是说他没有这方面的能耐,而只是暂时还没有被周文王与伯乐这样的人发现,暂时还无人懂得他的才能和价值罢了。
“负贩朝歌”在姜子牙的人生历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他在商的大都市朝歌一带贩过货物,开过肉铺,也干过卖酒一类的营生。积累了很好的经商、营业、处世经验,为日后的政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姜子牙的“负贩朝歌”,说明了当时有商一代的商业之盛,把地处西陲的周地的人也吸引过来了。据说,管仲与他的好友鲍叔牙也曾合伙做过买卖,从事商业活动,不过,这是他们在进入仕途前为生活困窘一时的被迫所为,未必是他们真志。
商业的发展与道路的畅通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的领导人历来把道路建设看成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帝在统一天下过程中“披山通道”,大禹一面治水,一面“通九道”。商统治者继承了这一好传统,环绕各中心城市修建了四通八达、宽广平坦的国道,被广大民众赞誉为——
王道平平,形容治理有序,出自《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
《尚书·洪范》中所说王道荡荡、王道平平,原本的意思是指“遵王之路”,也就是走王家筑的国道,后扩义为指治国之道,强调为政者应以国事为重,大公无私,而不应拉帮结派,褊狭行事。从道路的角度讲,商代的道路建设的确是很有成就的,言之为平平(路面平正)和荡荡(路面宽广)一点也不为过。
筑路建设自黄帝时期始,《史记·五帝本纪》有黄帝“披山通道”的赞语。大禹治水,一面治水,一面筑路,《夏本纪》说他“开九州,通九道”。商代人在此基础上发展了道路建设。河南偃师是早期商都城遗址,现已发现了11条“王道”,路面各宽达6米,最宽处达到了10米,道路与城门连结,也就是王道可以接通乡村和其他城市的道路,这样就构成了棋盘式的国家道路网。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商后期国都)刘家庄发现了三条商代的“王道”,其中两条南北向,一条东西向。南北向的道路各宽10米以上,最宽处达24米,此外还有很宽的人行道。双向多车道,道路用碎陶片和泥土填铺,坚实、平整,说其“王道平平”、“王道荡荡”,一点也不为过。这南北向的“王道”与东西向的“王道”相交叉,有的形成十字路口,有的形成丁字路口。这些“王道”分别延伸到城外,形成全国性的交通网络。
在商代的方国里,也有道路的修筑,可供方国与方国、方国与中央之间的交通。这些都为政治的统一和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影响力传播至四海,各地诸侯方国都来商都朝贡(《诗经·玄鸟》),商代王都和方国之间的相互来往联系应该就是通过王道完成的。正因为殷商的王都有很好的道路设施,箕子在商朝灭亡后见到了周武王,向其夸耀商的“王道”的正、直和平坦。(《尚书·洪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