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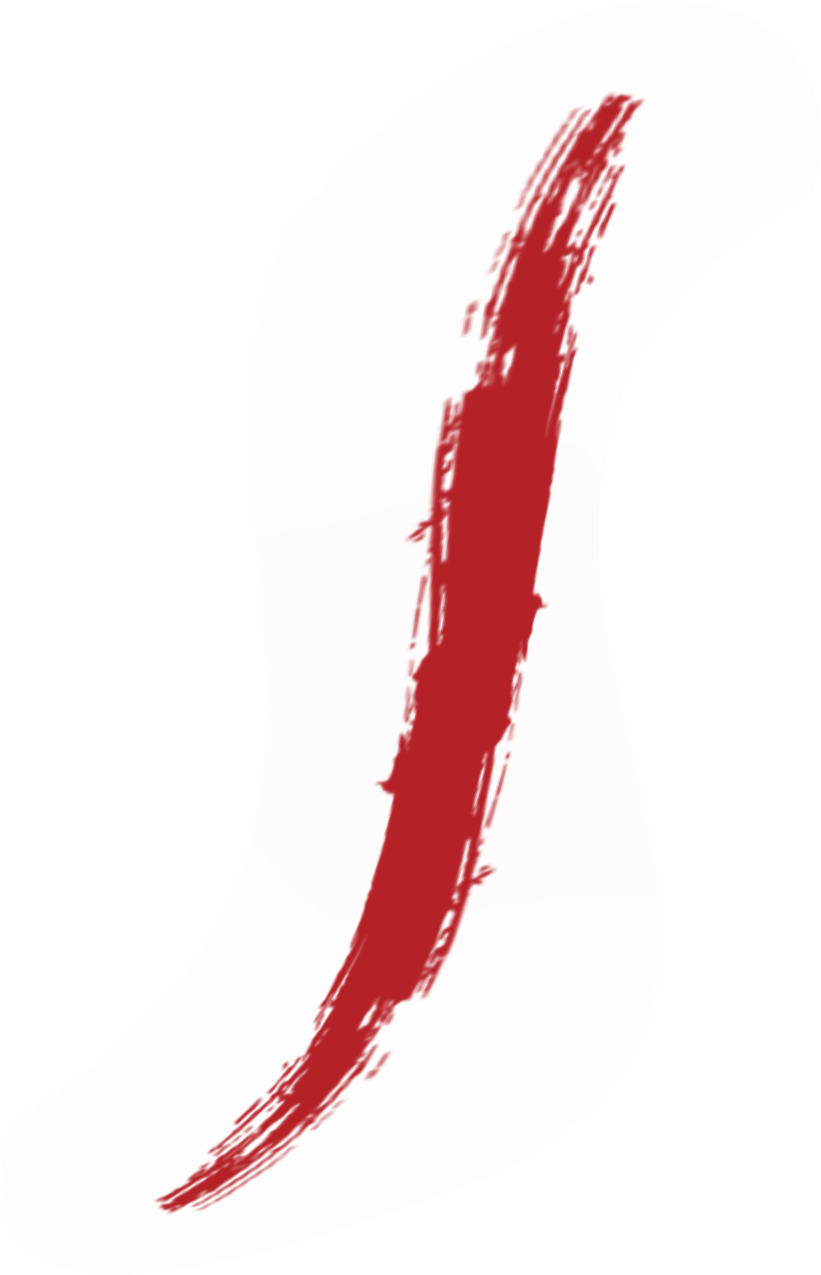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道之以政”,“道”可以理解为宣导、引导,“以政”就是用行政命令作为手段。“道之以政”,指的是用行政命令作为手段,来引导、治理百姓。
“齐之以刑”,“齐”是约束,即用刑法来约束百姓,以刑罚来处理问题。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当时法家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不用谈理,不用谈义,谈的是规矩,只要符合规矩、法度就行了。这也是很多现代国家所使用的手法。
孔夫子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民免而无耻”,老百姓可能因为畏惧责罚而不去犯罪。
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甚至到汉朝,都是用严苛的刑罚来管理百姓的。大家不要被刘邦的“约法三章”给骗了,刘邦表面上说约法三章,实际上汉朝沿袭了秦朝的很多制度,比如犯了错要割鼻子、砍手脚、脸上刺字等,各地方都有不同的酷刑。
当使用严苛的刑罚来治理国家时,老百姓自然会为了逃避罪责尽量不犯法,但心中“无耻”,也就是内心并不觉得很多不好的行为是有问题的,没有羞耻心。
我们要怎么理解以上内容?
我在美国的大街上经常看到很多年轻人,手执牌子站着,牌子上写着“我需要一个房子”“我需要一些面包”……可是他们有手有脚,却站在那里向他人索求,就是不愿意去工作。
在洛杉矶、纽约的街头,都能看到这样的流浪汉。
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简直不可想象,但是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没犯法,这是个人的自由。甚至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说:“在美国,有人不穿衣服走在大街上也是可以的,这是个人权利,警察不能将其逮捕。”
这就是孔夫子最担心的状态:“民免而无耻”。只要不犯法,一个人在内心对自己没有任何约束,没有道德感,也没有向上的力量。
“道之以德”讲究的是德行,“齐之以礼”指的是我们靠“礼”来约束。
人们不能仅用法律、规则判定一个人的行为到底合理不合理,有的事情,要看在心上是否过得去,是否符合道义。
《白鹿原》中,就反映出了中国的变化。在白嘉轩的时代,出了问题,大家就会有个公论,人的行为要由整个宗族进行判定,做错事的人后脊梁骨冷飕飕的,觉得自己在村里再也无法待下去了。这是宗族礼法给人带来的约束。
与之相反的是,用德行、礼仪去引导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孔子认为是“有耻且格”:老百姓不仅有羞耻心,还能够守规矩。“格”可以理解为守规矩,讲品格。
孔夫子的理想,是每个人拥有真正美好的品格。
关于这个观点,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胡适先生就认为,在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矩而不是空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那么,是否应该多讲法律,少讲道德?
在论证之前,其实有个前提,也就是社会背景如何,是国泰民安,还是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处于乱世,价值观会更加遵从原始的生存本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多吃多占,来满足膨胀的私欲,游走在道德的边缘。
道德是弱约束,是倡导人们要去做的事。法律才是强约束,强调的是人必须去做的事。
胡适先生提出的,是在乱世中法律的重要性。在人们生活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去做事,这是空谈,是不现实的。
孔夫子的理想是天下大同,当社会已经规范时,人们在社会安定的环境下如何才能拥有美好的品质和德行。
再看看当下的社会。比起美国,中国的犯罪率已经非常低了。
我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过这样的一组数据:在美国的监狱里,关了全世界约25%的犯人,而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的5%。过去30年,美国人口增长不到30%,监狱人口增长却达到了800%。美国吃牢饭的人超过220万。
美国是一个靠法律说话的国家,触犯各种法条都有可能被抓进监狱。就是这种完全用法律说话的制度,却导致了“民免而无耻”。
我们不必拿孔子的理论跟胡适先生去辩论,这是不同环境之下的不同执政理想,是两种不同的治国境界。
孔夫子的理想是,当国家制度已经相对规范,人民生活安定,社会秩序良好时,则应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让老百姓有更高的追求,在精神和道德上进行修炼。
比如,“樊登读书”的使命,就是希望在社会稳定的当下,我们一起来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实现慎终而追远,民德归厚,有耻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