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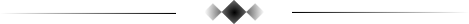

通过第1章我们了解到,若想深入了解人类的性征,我们必须先要抛开人类狭隘的视角。人类的父母发生性行为之后通常会继续待在一起,并双双投入养育后代的工作中。就这一点而言,人类这种动物的确颇具特色。没有人敢断言,男性和女性在养育后代这件事上所做出的贡献是等价的。在绝大多数婚姻中,甚至在绝大多数社会中,两性对生儿育女这个过程的付出都极不平等。而父亲多少都会为孩子做些事,哪怕只是提供食物、保护和住所,也算是尽了些做父亲的义务。人类将父亲对孩子的付出视为应尽的义务,并将这些义务写入了法律:离婚后,父亲也被要求继续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未婚母亲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证明孩子与父亲的亲子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父亲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
然而,这一切都仅是从人类的视角来看待性行为的。在其他动物眼中,尤其在哺乳动物看来,性别平等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猩猩、长颈鹿以及其他哺乳动物能够表达自己的态度,它们一定会认为人类的儿童抚养法案荒谬至极。绝大多数雄性哺乳动物在完成交配任务之后,就会和自己的伴侣及孩子分道扬镳,因为它们要忙着追求其他雌性,以继续自己的交配大业。普遍来看,在育儿这件事上,不仅是雄性哺乳动物,实际上所有的雄性动物付出的都比雌性少得多,有些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也存在一些超脱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沙文主义模式的例外情况。比如矶鹞和斑鹬等鸟类都由雄性来负责孵化并养育幼鸟,而雌性会离开它们去寻找下一只雄性进行交配,并为其产下相应的卵。在一些鱼类(如海马、棘鱼)和两栖动物(如产婆蟾)种群中,雄性负责在巢穴、口腔、囊袋或后背上照料受精卵。那么,有什么理论既可以解释雌性养育后代的普遍模式,又可以解释少数例外情况,而且不会自相矛盾呢?
若想找到答案,我们必须认识到,正如自然选择决定了人对疟疾的抵抗能力和牙齿的数目,它同样决定了调控某种行为的基因。对某个物种有益的且由基因传递的行为模式,对其他物种而言未必有益。回到此前讨论的话题上,刚刚完成交配并创造了受精卵的雄性和雌性需要对后续的行为进行“抉择”。它们是否应该双双离开,让受精卵自力更生,或是结成固定伴侣,抑或是各自寻找下一位对象,努力孕育下一颗受精卵?一方面,因养育后代而暂时中断的性行为可能会提高第一颗受精卵的存活率。如果事实真的如此,那么这一选择就会带来更多可能性:父母双方均选择照料后代,或者其中一方选择照料后代。另一方面,假设在没有父母照料的情况下,受精卵的存活率是10%;如果将照料受精卵的时间投入后续的繁殖中,可以额外产下1 000颗受精卵,那么最佳策略就是任由第一颗受精卵自生自灭,同时为产下更多受精卵而继续努力。
我将这些不同的策略称为“抉择”。这样的说法听起来就好像动物和人类一样能够主动做出决策,有意识地对不同策略进行权衡,并最终选出最有可能扩大自身利益的策略。当然,事实并非如此。这些所谓的“抉择”大多已被编入物种的解剖结构和生理特征。比如,雌性袋鼠做出的“抉择”是长出一个育儿袋来容纳幼崽,而雄性袋鼠则没有。从解剖学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雌性还是雄性,两者都拥有做出某种抉择的可能性,但本能会引导它们照料或不照料幼崽,而这一受本能驱动的“抉择”行为在同一物种的两性身上是不同的。比如,雄性和雌性信天翁、雄性鸵鸟、雌性蜂鸟会基于本能为幼鸟提供食物,而灌丛火鸡无论雌雄均不会为幼鸟提供食物,但从生理特征和解剖结构的角度来看,这些鸟类中的雌性和雄性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养育后代这一行为背后的解剖结构、生理特征和本能,都通过自然选择被编入了基因中。总的来说,上述特质促成了生物学家口中的“繁殖策略”。这也就是说,鸟类父母身上发生的基因突变或基因重组现象有可能强化或弱化了为幼鸟提供食物这一本能,也有可能对同一物种的雌雄两性造成不同的影响。本能很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携带父母基因的幼鸟的存活数量。毋庸置疑,由父母提供食物的幼鸟,其存活率更大。不过,放弃为幼鸟提供食物的父母也会获得将基因传递下去的其他机会。由此可见,使父母本能地为幼鸟提供食物的基因,是由我们将要讨论的生态和生物因素决定的,其实际结果既有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携带父母基因的幼鸟的数量。
某些特定的解剖结构和本能的出现是为了确保后代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决定这些结构和本能的基因在种群中出现的频率会逐渐增加。换句话说,促进成功生存和繁殖的解剖结构和本能会通过自然选择得以确立,即被写入遗传编码。诸如此类的说法常见于与进化生物学有关的讨论中。生物学家常常采用拟人的手法来简洁明了地描述,比如,某只动物选择做某事,或采用某一策略。这种简略的描述不应该被误解为动物能够有意识地思考和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