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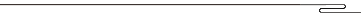
从事喜剧表演的这一年,我比过去通勤的生活多了不少空闲时间。每隔一周我会开车送阿拉什去物理治疗中心。这是我见过最励志的地方。每个人都全身心投入康复治疗当中,每天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他们花费无数的时间顽强地追求一个目标:恢复到曾经的状态。其中很多人都已经被自己的保险公司抛弃,康复的概率很渺茫,但他们仍不肯放弃。其中有很多人像阿拉什一样,需要依靠朋友筹集的善款维持治疗。劳拉是阿拉什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们都想知道,其他脊髓损伤(SCI)的幸存者过得怎样?他们是否会遇到同样的困境?多少幸存者看不到康复的希望?多少人像阿拉什一样,连轮椅这样的基础必需品也要自费购买,保险不能覆盖?他们有怎样的经历,面对人生的转变他们是怎样做的?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花了几个月调查收集资料。我们找到一些媒体朋友,希望能获得更广阔的视野。但结果令人震惊而沮丧,没有任何媒体或记者对此感兴趣。但我们知道必须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仅靠数字是不行的。
在公众演讲和故事会锻炼近一年后,我开始意识到许多人在错误的方向前进了100英里:要讲别人的故事,你必须先讲自己的故事。数字是故事的提炼,但它不鲜活,没有色彩,无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与其通过他人之口,阿拉什应当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
我做得最成功的事,是用所学知识帮阿拉什打磨出一篇讲稿。他的第一批观众是三百名首席执行官,同台的是最知名的演讲人,如作家兼苹果前首席宣传官盖伊·川崎(Guy Kawasaki)。阿拉什以最简短、实际的方式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在适当的地方停顿,用好“3”的法则,对前面的内容进行扣题,并在首尾呼应中强有力地传递出一个观念:生命就是在实现远大目标的征途上,不忘庆祝每一个小小的成就,他称之为“微小的一大步”,虽然他自己还未能起身行走。最后,他展示了一些医生认为他再也做不到的事:暂时甩掉他痛恨的轮椅,凭双脚站立几分钟,来到深蓝色的太浩湖边,在古老的木质码头上向自己美丽的女朋友求婚。不幸的是,她拒绝了……开个玩笑,当然她会答应了。“微小的一大步”,他重复道,随后致谢下台,观众全体起立,掌声持续了二十秒钟。
《福布斯》杂志报道了他在第二次演讲时用到的记忆宫殿技巧,这是我从脱口秀朋友查德·萨瓦特那里学来的,他让寿司师傅和戴着墨西哥草帽的克利须那神鲜活了起来。受到环境的激励,第三次阿拉什会在更高水平的地方演讲。
为什么我要讲这些?我听到你在说:“这和搞笑的公众演讲毫无关系。”你说得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搞笑。一些原始的、亲身经历的、充满情感的故事常常有着惊人的力量,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对你这个讲述者来说,只是讲了一个故事……就像我站在硬木制成的大戏台上,面对1400名观众所做的那样。但对于倾听者,你分享的经历中的某些东西或者产生魔力的瞬间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可能你记不住那1400名观众,但如果你能用好脱口秀演员熟知的技巧,无论台下有4个人还是1400个人,他们都会记住你。
阿拉什的故事明显严肃而有力度,你也许认为这样的故事不适用于搞笑。但情况正好相反,正如我的同胞,来自爱尔兰的马克·波洛克(Mark Pollock)所做的那样。他摇着轮椅登上TED×好莱坞的舞台,开篇直接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有不少问题。我瘫了。我瞎了。我秃了。我从北爱尔兰来。我有不少问题。这点毫无疑问。相信在座的有些人也是一样。”马克用一些严肃、悲伤且毫不相关的话题引发了观众的共鸣。在气氛高度紧张的时刻,笑声是最好的解压阀。梅逊·扎伊德用同样的结构在TED演讲中获得了不错的效果。谈到自己的脑瘫的问题时,她说:“我有99个麻烦,脑瘫只是其中之一。如果世界上有遭受迫害的奥林匹克竞赛,我肯定拿金牌。我是巴勒斯坦人,是穆斯林,我是女性,是残疾人……我住在新泽西。”在旧金山历史悠久的基立剧院(Geary Theater),安雅·里默(Anya Rymer)作为一名作家、摄影师和冒险家登上“飞蛾故事会”的主舞台,向一千多名观众讲述了自己抗击艾滋病的起起伏伏的经历:“当时我只剩8个T细胞了,我称它们为‘脱线家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