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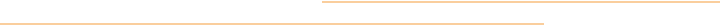

一种绚烂的、奇异的、浓厚的,无法形容的生活,以足够让人惊讶的速度开始了它的行程。我回忆起那段生活,觉得它像是由一个美好而纯朴的天才用动人的话语讲述一个让人潸然泪下的童话。我梳理了一下记忆,有时候连我都无法相信那些事是真的,我很想去否认、反抗,因为在那愚蠢的一家人的压榨下,残酷的事情简直不胜枚举。
不过,真理永远站在怜悯之上,我明白我不是在讲述自己的事情,而是在讲述那个可怕的、令人窒息的狭小地方。这是普通俄国人曾生活的地方,至今还有人在那里生活。
外祖父的家中充满了仇恨的气息,人们都因仇恨而疯狂,甚至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后来,我才从外祖母那里知道,母亲到的时候,我的两个舅舅正在让外祖父分家。母亲的出现让他们分家的想法更坚定了。他们担心母亲会要回原本为她准备的那份嫁妆,虽然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逆外祖父指定的婚事而被外祖父扣留。我的两个舅舅觉得嫁妆应该归他们所有。此外,他们还因为谁到奥卡河对面的库纳维诺区去,谁将在城里开染坊吵闹不休。
我和母亲来后不久,一家人在厨房吃饭的时候就发生了一次争吵:突然,两个舅舅都站起来,探着身子朝桌子那边的外祖父大吼,那样子就像是两只哆嗦的、受了委屈且龇着牙的狗。外祖父红着脸,用汤匙敲打着桌子,像打鸣的公鸡那样声音响亮地叫道:“你们都给我要饭去!”
外祖母一脸痛苦的神色,对外祖父说:“分家吧,这样你也能耳根清净些,都分给他们吧!”
外祖父的眼睛闪着光,嘴里大声喊着:“闭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是个小个子,可声音却很大,真奇怪。
母亲站起来,转身向窗口慢慢走去,不再看这发生的一切。
突然,米哈伊尔舅舅扬起手打了他弟弟的脸一下;另外一个舅舅立即就吼起来,抓住米哈伊尔舅舅扭打起来。两个人在地板上滚来滚去,不时地发出辱骂、喘息的声音。
纳塔利娅舅妈不顾自己怀孕的身子大声喊叫,于是我母亲把她拉走了。其他的小孩子也呜呜地哭,而后一脸麻子的叶夫根尼娅保姆把他们赶出了厨房。厨房里乱糟糟的,椅子都倒在地上;米哈伊尔舅舅被年轻的学徒“小茨冈”
 压着,他的手被手巾捆着,捆他的人是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他是个秃顶、戴着黑眼镜、一脸胡子的人。
压着,他的手被手巾捆着,捆他的人是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师傅,他是个秃顶、戴着黑眼镜、一脸胡子的人。
舅舅喘着气,伸长了脖子,他那并不浓密的胡子来回刮擦着地板;而外祖父跑着,围着桌子转圈,悲哀地喊:“你们是亲兄弟啊!你们啊……”
一开始,我因为害怕就躲在了炕炉
 上,惊恐地看着外祖母端来盛着水的铜盆给一脸鲜血的雅科夫舅舅洗脸。雅科夫舅舅流着眼泪,跺着脚。外祖母用沉痛的声音说:“都清醒一下吧!这帮野种!”
上,惊恐地看着外祖母端来盛着水的铜盆给一脸鲜血的雅科夫舅舅洗脸。雅科夫舅舅流着眼泪,跺着脚。外祖母用沉痛的声音说:“都清醒一下吧!这帮野种!”
外祖父将被扯破的衬衫拉到肩膀上对着外祖母喊:“你看看!老妖婆,你生的是一群野兽!”
外祖母在雅科夫舅舅离开后就躲在角落里颤抖地哀号:“请让我的孩子有点儿人性吧,圣母啊!”
她面前站着侧着身子望着桌子的外祖父。桌子上的东西都翻倒了,上面都是水。外祖父压低声音说:“老婆子,你要看住了,别让他们欺负瓦尔瓦拉,说不定……”
“上帝仁慈!行了,你的衬衫被撕坏了,让我缝一缝……”外祖母抱着外祖父的头,手放在他的脸上,然后亲了亲他的额头;比外祖母矮的外祖父将自己的脸贴在她肩膀上。
“老婆子,这家看来是得分了……”
“分吧,分吧,老爷子。”
外祖父和外祖母聊了很久。开始的时候,谈话还很融洽,后来外祖父就变得像一只准备战斗的公鸡一样,他指着外祖母,脚在地板上来回搓动,吓唬她说:“我明白,跟我相比你更疼他们!但是,米什卡
 他是个阴险的人,雅什卡
他是个阴险的人,雅什卡
 加入了共济会
加入了共济会
 !我们的家产会被他们败光的……”
!我们的家产会被他们败光的……”
我在炕炉上一翻身,因为动作笨拙,碰到了熨斗,它掉了下去,顺着炉梯咕噜咕噜地滚到了脏水盆里。
外祖父跳了上来,然后把我拖下去,仔细打量着我的脸,似乎我是一个陌生人。他问:“谁把你放到这儿的?是妈妈吗?”
“是我自己。”
“撒谎。”
“真的,我害怕就跑上去了。”
外祖父轻拍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推了我一下。
“太像他爸爸了!滚……”
我开心地离开了这里。
我很害怕外祖父,因为他总是用他那双带着锐利目光的绿色眼睛注视我,我看得清清楚楚。回忆里,我总是想方设法躲避这双眼睛。我认为外祖父的脾气很糟糕,无论和谁讲话都会摆出一副挑战的姿态,嘲笑对方,欺负对方,极力挑动对方的怒火。
他时常感叹:“你们这些人啊!”最后这个“啊”字的音会拉很长,我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发冷、无聊的感觉。
外祖父和舅舅们会在我们休息或者吃晚茶的时候回来,他们非常疲倦,头发用带子绑着,手不仅被硫酸盐灼伤,还因为紫檀而被染得通红,大家看起来就像厨房黑暗角落里的圣像。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外祖父的孙子们会很羡慕我,因为他们的爷爷不仅会坐到我对面,还会跟我聊很多话。外祖父长得很瘦但身材很匀称,棱角分明。他虽然穿着破旧的丝线圆领背心,褶皱的印花布衬衫以及膝盖上有两个补丁的裤子,但和他那两个穿着上衣、护胸并将三角绸布围在脖子上的儿子相比,人们会觉得他穿得更清爽得体。
外祖父在我们来了几天后就逼着我去学祈祷。我在所有孩子中是年龄最小的,其他孩子已经在圣母升天大堂的一个助祭
 的指导下学习认字了。教堂离家不远,从家的窗户里就能看见它的金顶。
的指导下学习认字了。教堂离家不远,从家的窗户里就能看见它的金顶。
怯弱且文静的纳塔利娅舅妈教我念祷词,她有一张像儿童一样的小脸,眼睛很明亮。我觉得我可以透过她的眼睛知道她的想法。
我喜欢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眼睛看。她眯着眼睛,不停地转动脑袋,细声细语如恳请一样说道:“请你说,‘我们天上的父亲……’”
假如我向她问道:“‘雅科、热’
 是什么啊?”
是什么啊?”
她小心地看一下四周,忠告我:“别问了!越问越糟糕,你就跟着我说‘我们天上的父亲’……说啊?”
她的话让我很惶恐:为什么会越问越糟糕?“雅科、热”这三个字的意思很隐晦,我故意把它们念走了样:“‘雅科夫、热’,‘雅、夫、科热’
 ……”
……”
浑身发软、脸色苍白的舅妈用她不连贯的声音耐心纠正我:“不对,你简单地说,‘雅科、热’……”
但是,她本人以及她说的话都不简单,不利于我记住这些词,于是我很气愤。
某一天,外祖父问道:“阿廖什卡
 ,你告诉我,今天做了什么?去玩了?你额头上的那个青包可告诉我你干什么了。有这么一个青包算什么本事?你念熟‘主祷经’了吗?”
,你告诉我,今天做了什么?去玩了?你额头上的那个青包可告诉我你干什么了。有这么一个青包算什么本事?你念熟‘主祷经’了吗?”
舅妈轻声回道:“他记性很差。”
冷笑了一下的外祖父开心地扬起眉毛说:“如果是这样就该打。”
接着他问我:“你父亲打你吗?”
我不明白他话里的意思就没有回答,但母亲回答:“没有,马克西姆没有打过他,也不让我打他。”
“为什么?”
“他说教育不是打出来的。”
外祖父气愤地说:“哦!上帝要原谅我这样说一个死人!马克西姆真是个傻瓜!”外祖父的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
我觉得我受侮辱了。外祖父看出来了,于是问:“你为什么噘嘴呢?你这个样子……”
他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红头发,又接着说:“星期六,我要为顶针的事情抽萨什卡
 一顿。”
一顿。”
“‘抽’是什么意思?”我问。
大家听到我的问题后都笑了。外祖父说:“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我心里猜想:“拆开”要染色的衣服应该就是“抽”,而“打”和“揍”显然是一个意思。我见过打猫,打马,打狗,甚至是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小孩儿会被这样打。平日里,舅舅们虽然也会弹一下自己孩子的额头或者后脑勺,但孩子们都只是不在意地挠一挠肿了的地方。我问过他们很多次:“疼吗?”
他们非常勇敢,回答:“不疼。”
顶针的事,被闹得人尽皆知,我也知道。某天晚饭前,我们已经喝过了茶,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正忙着把成幅已经染好了的料子缝成一匹一匹的,然后把厚纸签缀在上面。米哈伊尔舅舅想欺负一下快要看不见的格里戈里,于是把顶针交给九岁的侄子,让他用蜡烛把它烧热。顶针被萨沙用烛花镊子夹着,等烧得滚烫后放到了格里戈里的手底下,接着萨沙就到炉子后面躲起来了。恰巧,外祖父过来想干活,于是就戴上了那个滚烫的顶针。
我记得我听到吵闹声就跑进了厨房里,看到外祖父蹦跶着,样子很滑稽,他那烧伤了的指头抓着耳朵叫道:“是谁?异教徒,你们这群人!”
米哈伊尔舅舅俯下身子,一边对着顶针吹气一边用手指拨弄它;格里戈里师傅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在那里缝东西,他那巨大的秃头上是晃动的影子;跑进来的雅科夫舅舅在炕炉拐角的地方躲着笑;外祖母把生马铃薯擦成糊。
米哈伊尔舅舅忽然说:“是雅科夫的儿子萨什卡做的。”
“撒谎!”雅科夫大叫一声跳了出来。
萨什卡也哭了,在炕炉后面说:“爸爸,你要相信我,是他叫我干的!”
舅舅们吵了起来。外祖父忽然平静了,将手指涂满马铃薯糊之后一言不发地带着我走了。
大家都说这事要怪米哈伊尔舅舅。于是,我在喝茶的时候问外祖父:“要揍米哈伊尔舅舅和萨什卡吗?”
“肯定的。”外祖父生气地回答,还瞟了我一眼。
米哈伊尔舅舅一拍桌子,对着母亲吼道:“瓦尔瓦拉,管管你的兔崽子,不然我就叫他脑袋分家!”
母亲回答:“你试试看!你敢……”
大家都沉默了。
母亲很擅长说这种简短的话,似乎每次说完了人们就会被推开,被甩到远处,变得渺小。
我明白,大家都不敢惹母亲;哪怕是外祖父对母亲说话也要轻声细语的。这让我觉得很畅快,我很开心地向外祖父的孙子们夸耀:“谁都没有我母亲力气大!”
他们没有反驳。
不过,我对母亲的认知因为星期六发生的事情而动摇了。
我犯错了,在星期六之前。
我觉得大人们给布料染色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黄布从黑水里捞出来就会变成宝蓝色;灰布浸入红褐色的水里就会变成樱桃红色。看着很简单,可我不理解为什么。
我想自己动手试一次,于是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雅科夫的儿子—萨沙,他是一个好孩子,总是和大人们待在一起,对谁都很热情,时刻都想方设法为所有人做点儿什么。大人们都说萨沙乖巧、听话,然而外祖父却斜着眼睛说:“就会卖乖!”
雅科夫的萨沙长得黑黑瘦瘦的,眼睛鼓出来,看起来像龙虾,栗色的瞳仁会在他兴奋的时候从一动不动变成跟着白眼珠一起转动。萨沙说话的声音很低而且吐字很着急,总是会被自己哽住。他时常偷偷摸摸地四处张望,似乎随时准备躲到什么地方去。
我很讨厌雅科夫的萨沙。我比较喜欢米哈伊尔那个总被忽略、笨笨懒懒的萨沙。他很安静,眼神很忧郁,笑起来的时候看着很和善,同他温柔的母亲很像。他的牙齿都从嘴里露了出来,长得很难看,上颌还有两排牙。米哈伊尔的萨沙觉得这很有意思,时常将手指放到嘴里去摇晃后排的牙齿,想要拔下来;如果谁想摸他的牙他也会同意。这就是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全部有趣的地方。家里虽然有很多人,但是他很孤单,经常坐在不明亮也不黑暗的角落里,太阳下山的时候会坐到窗户前。和他一起沉默不语还是很开心的—紧挨着他坐在窗户前,一言不发地待一小时,看着窗外天空的火烧云,看着那围绕着圣母升天大堂金色圆顶飞翔的黑色寒鸦,这群寒鸦飞往高空又落下来,突然天空被一张黑色的网渐渐笼罩,而后慢慢消失在无处可寻的地方,只剩一片空白。当不想说话的你看着这些的时候,内心是愉悦的也是忧愁的。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无论讲什么都头头是道,那严肃的神情就跟大人一样。他知道我想自己染布以后,就劝说我把柜子里用来过节的白桌布染成蓝色。
他很认真地说:“白色好上色,我记得非常清楚。”
桌布很沉,我把它拽出来抱到了放着蓝靛桶的院子里。然而,我刚刚把桌布的边缘放到桶里时,“小茨冈”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一把将桌布夺过去,用他的大手把桌布拧干净,然后对着门洞里看我工作的雅科夫的萨沙喊:“去叫你奶奶来!”
头发黑而蓬乱的“小茨冈”摇了摇头,像预感到了不好的事情似的对我说:“你会因为这个被揍一顿的!”
跑过来的外祖母惊讶地叫了一声,甚至还一边哭着一边咒骂:“你这个咸耳朵鬼!别尔米人!我真想把你摔一边去!”
而后,外祖母对“小茨冈”说:“这事别告诉老爷,瞒住这事儿,没准可以糊弄过去……”
“小茨冈”把手在他那五颜六色的围裙上擦了擦,担心地说:“我不会说的,不用担心,就怕萨沙多嘴!”
外祖母说:“两戈比让他闭嘴好了。”然后就带我回去了。
有人在星期六晚祷前把我带到了厨房里;厨房很昏暗,很静。记忆中,窗外是秋天灰色的天空,还下着小雨,房子里的房门和过道都紧紧地关着。一张大椅子摆放在黑漆漆的炉口前,“小茨冈”脸色阴沉地坐在上面,跟往日的样子完全不同;外祖父站在角落里,他旁边有个污水盆和水桶,水桶里面的树条子被外祖父捞起来,测量后再一根一根地摆好,树条子在空气中张牙舞爪的。外祖母闻着鼻烟,在黑暗的地方嘀咕:“害人精……还笑呢……”
厨房中间的凳子上坐着雅科夫的萨沙,他握着拳头,一边擦着眼睛一边拉着长腔说:“饶了我吧……”声音变得跟老乞丐一样。
米哈伊尔舅舅的一儿一女像木头人一样并排站在凳子后面。
外祖父将一根树条子从拳头中间捋过来,平静地说道:“揍一顿再说,脱裤子……”
屋子里有些吵闹,有外祖父说话的声音,有萨沙在凳子上来回动弹的声音,有外祖母的脚摩擦地板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都无法破坏昏暗厨房里那让人刻骨铭心的寂静。
萨沙直起身子,把裤子脱到了膝盖处,然后提着它,弯着腰,踉踉跄跄地走向长凳子。我看着他走路的样子,心里很难过,腿也开始颤抖。
接着,我看见他听话地趴在长凳子上,被“小茨冈”从腋下捆住,然后脖子也被一条宽手巾绑着。最后,“小茨冈”弯着身子用手抓住他的脚踝。我更难过了。
外祖父叫我:“来,列克赛
 ,过来一点儿……抽人就是这么抽的……一下……”
,过来一点儿……抽人就是这么抽的……一下……”
他适当地扬起手,对着赤裸的萨沙打了一下,然后就听到了一声哀号。
外祖父说:“装!刚刚那下根本不疼,这下才疼!”
树条子再次落下来,哀号的表哥身上立刻就起了一条红道。
外祖父接着问:“不乐意吧?不舒服吧?为了顶针!”
他抽打的手很稳,起落很均匀,而我的心也随着他的手一起一落的。
萨沙尖厉地叫喊着,声音非常讨厌:“我错了……我说了桌布的事啊……”
外祖父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念《圣经》:“告密也要罚!而且告密的人要先罚,这一下是为了桌布!”
外祖母向我扑过来,抱着我喊:“你这个魔鬼,我不会把列克赛给你!”
她一边踢门一边喊我的母亲:“瓦尔瓦拉……”
外祖父凶猛地扑向外祖母,把她推倒了,然后把我抢过来抱到长凳子上。被抱着的我不停地挣扎,咬他的手,拽他的红胡子。他生气地吼着,紧紧夹着我,后来把我扔到了长凳子上。被扔的我磕破了脸。他粗野地喊:“打死他!给我绑上……”
记忆里,母亲的眼睛瞪得很圆,脸色也很苍白。她围着长凳子转圈,哑着嗓子喊:“不要……爸爸……把他给我……”
我被外祖父打得失去了意识,然后就大病了一场,一个人趴在暖和的床上,在一间小屋子里躺了好几天;小屋子比较昏暗,只有一扇窗户,墙角处还放着很多玻璃匣子,匣子里面都是圣像,匣子前面的长明灯烧得通红通红的。
对我而言,生病的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日子。或许,我在这段日子里成长了很多,并且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从这以后,我总是不安地看着人们,好像是心的外皮被撕掉了一样,变得敏感起来,无论是谁给的伤害和屈辱我都不能忍受。
最先让我吃惊的是母亲与外祖母的争吵:一身黑,身躯也很大的外祖母在拥挤的屋子里扑向了母亲,将母亲逼到了墙角圣像前,凶悍地问:“你怎么没有把他夺过来?”
“我当时害怕!”
“瓦尔瓦拉,你长得这么高大是白长的吗?我这个老太婆都不怕,你真是……”
“妈妈,不要说,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你不爱你的孩子,不可怜你的孤儿!”
“我自己就是孤儿,一辈子的孤儿!”母亲高声说道,声音很沉重。
后来,母亲和外祖母都坐在墙角的箱子上掉眼泪。母亲说:“如果是我一个人,我就可以远走高飞了,可是,我必须为了阿列克赛在这个地狱里活着。妈妈,我活不下去了……”
“好孩子,我的心肝啊,我的骨肉。”外祖母低声哄着。
我知道了:母亲也很弱小,也和别人一样害怕外祖父。如果不是我,她就能离开这叫人无法生活下去的家庭。这件事让我很难过。果然,母亲没过多久就离开家去别的地方做客了。
不知道为什么,外祖父像从天花板上掉下来一样突然出现在我的小房间里。他坐在旁边,抚摩着我,他的手很冰冷。他说:“小爷子,别生气了……你说说话……你怎么了?”
如果不是身上太疼,我一定会踢他一脚。和以往相比,外祖父的须发要红一些,他来回晃动着自己的头,有些不安的样子;一双明亮的眼睛看着墙壁,好像在搜索什么。他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了很多东西:一个苹果,两个糖角,一个山羊形的甜饼和一包青葡萄干。这些东西被放在枕头上,我的鼻子前面。
“看,我带了礼物来。”
他弯腰亲了亲我的额头,而后他用僵硬的手轻轻抚摩我的头。他的手染了黄色,弯得像鸟嘴一样的指甲上的颜色更黄。外祖父一边抚摩一边跟我聊天:“兄弟,我知道我当时做得太过分了。我气坏了,谁叫你咬我还抓我了呢,我完全被惹火了。不过,你现在挨揍还算好的,我都记着呢。你必须清楚,被自己的亲人打是受教训,不是屈辱!做人不能叫外人打,只要不是外人就行。我也挨过打的,阿廖沙
 ,我当时被打得很惨,比你做的噩梦都恐怖!我被欺负得不像样子,假如上帝看见了,他也会为我掉眼泪的!结果呢?我这个乞丐的孩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熬出来了,成了行会的头儿,管着很多人呢。”
,我当时被打得很惨,比你做的噩梦都恐怖!我被欺负得不像样子,假如上帝看见了,他也会为我掉眼泪的!结果呢?我这个乞丐的孩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熬出来了,成了行会的头儿,管着很多人呢。”
他又瘦又干的身子微微靠着我,用流利又沉重的话一句接着一句地向我讲述他的童年。外祖父的眼睛闪着光芒,头发竖着,用粗重又高亢的嗓音像喇叭一样对我说:“你过来的时候坐的是轮船,蒸汽轮船。而我年轻的时候要用力气去拉货船,赤着脚逆着伏尔加河向上游走,脚下全是石块,从山上崩落的石块,又尖又利的。我从黎明走到黑夜,白天的时候后脑勺会被晒得融化了似的沸腾着,却不能停下;腰像豆芽一样弯着,骨头一直响;眼睛因为流下来的汗而看不清楚路,心里很难过,眼泪也一直流。阿廖沙啊,我都没有地方说苦去!我不停地走,常常滑脱了纤索脸朝下倒下去。倒下来也是好事情呢,完全没有力气了,只要休息一下哪怕是喘一口气也好啊!你看,被上帝和救世主耶稣注视着的人们都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我就这样在伏尔加河上,从辛比尔斯克走到了雷宾斯克,又从萨拉托夫走到了这里,然后还从阿斯特拉罕走了上万俄里到达了马卡里耶夫!我第四年就成了纤夫头,让主人看到了我能干的一面……”
我听着外祖父的话,觉得他在我面前像云朵一样快速变大了,从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儿变成了一个强壮有力的人,他一个人拖着大大的货船在逆流里走着……
外祖父说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会跳下床,甩着胳膊向我演示怎么拉纤,怎么把水从船里排出去;他低低地唱着歌,然后一纵身,利落地跳回床上,整个人都让人忍不住惊讶。他继续讲他的事情,声音也变得更粗重了:“当我们休息的时候,阿廖沙,一切又变得不一样了。在日古里附近的绿山下,我们会在夏季的傍晚生火煮粥,啊,一个悲苦的船夫唱喜爱的歌,其他的人也会跟着他唱,唱得人们都起鸡皮疙瘩,好像伏尔加河的水流也变得急了,像马儿一样狂奔着,而后立起来冲进天上的云层里。所有的悲伤就都被风吹走了,人们开心地唱着,非常起劲儿,有时候粥会被煮出来,那么负责煮粥的人就会被人用勺把儿打。怎么玩都不能把正事忘了的。”
人们好几次都探进头来叫外祖父,每次我都恳求说:“不要走!”
他就笑着冲那些人摆摆手,说:“等一等……”
他讲到了天黑,并在走之前跟我亲切地告别,而我才知道外祖父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可怕、凶恶。可我只要想到他曾那么残忍地打我,就特别伤心而且怎么也无法忘怀。
别人因为外祖父的到访也都过来看我,想办法让我开心。我的床边一整天都有人坐着,但不是每次都能让我开心起来。外祖母是所有人中最为勤快的一个,她甚至和我睡在一起。不过那些日子里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却是“小茨冈”。“小茨冈”的胸脯很宽大,四方身材,头很大,头发很卷曲。某天傍晚,他像是精心打扮了一下才过来的:金黄色的绸衬衫、绒布裤子,还有会发出咯噔声的皮靴。他的头发又黑又亮,一对浓黑的眉毛下长着一双斗鸡眼,小黑胡子很年轻,牙齿雪白,整个人看起来都很闪亮。长明灯柔和的红光照在他的绸衬衫上给人一种正在燃烧的感觉。
他一边说一边把袖子卷起来,让我看到肘弯都是红色伤痕的胳膊:“你看看,之前比这个肿得还厉害!你晓得吧,你外祖父气坏了,要狠狠地抽你,我一看情况不对就用这只胳膊挡着你,指望着挨到你外祖父把树条子打断,然后在他去拿另外一根树条子的时间里让你外祖母或者母亲把你带走。谁知道树条子那么结实,被水泡得太软了……不过这么说你还是少挨了几下,你看看,我的小弟弟,我是不是很机敏……”
他咧开嘴笑,声音非常温暖,像绸子一样,接着看了看自己的胳膊才说道:“我可怜你啊,当时都哽住了喉咙。我就知道事情变得糟糕了,你外祖父这么打你……”
“小茨冈”摇着脑袋,吹响鼻子的时候就像一匹马儿,他对我讲外祖父的某些事情,让我马上觉得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很可亲。
我告诉他,我很爱他。结果,他说的话叫人记忆深刻:“我也是啊,我就是因为爱你才这样做的,我什么时候为别人做过这些事呢?这一切都是因为爱你……”
而后,他一边紧张地看向门口一边向我低语:“记住,下次你外祖父再打你,你不要缩成一团了。你缩成一团会更疼,你必须要放软身子,舒展自己,让自己变得像凉粉似的。而且你一定要深呼吸,使劲儿地叫喊—记住我的话啊!”
我问:“我还会挨打吗?”
“小茨冈”平静地回答:“不会吗?肯定会的,你外祖父应该会经常收拾你的……”
“为什么啊?”
“总之你外祖父会的……”而后他又关心地说,“假如你外祖父的树条子一直落,就那么一上一下地打你,你就放软身子,全身舒展地躺在那儿;假如他用树条子抽你的皮,打下去之后再拉回树条子,你就随着树条子扭身子,知道了吗?这样能少受点儿罪。”
他挤着眼睛对我说:“小弟弟,在这方面,巡长都比不上我的!我的皮啊,已经被抽打得粗硬粗硬的了,用来缝手套都没有问题!”
我看着他那洋溢着快乐的脸,忽然就想起了外祖父讲给我听的童话:伊凡王子和伊凡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