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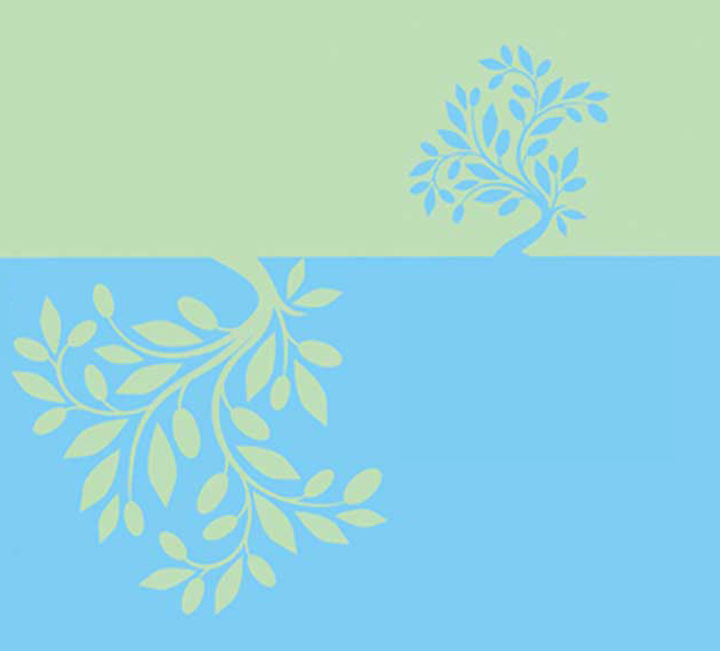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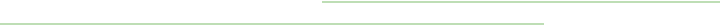

弟弟科利亚死得很安静,就像一颗小星星随着黎明的到来而悄悄地消失了。之前,外祖母、他和我,我们三人在一个板棚里的一堆铺有破布的木柴上睡觉。旁边是一堵由毛板拼成的墙,有许多缝隙,墙外是房东家的鸡舍。每天晚上,我们都听到吃饱了的鸡临睡前拍打拍打翅膀,咯咯地叫两声就睡了。早上又被公鸡那有穿透力的叫声吵醒。
“哎呀,该死!”外祖母醒来后抱怨地说。
我醒了,看着床边的阳光,那是从柴屋缝隙里照进来的。好多银色的灰粒在阳光中飞舞着,像描写童话的字句。几只老鼠在柴堆里吱吱作响,地上爬着几个红色的甲虫,它们的翅膀上有小黑点。
有时候鸡屎的臭味实在难闻,我便走出柴屋,爬到屋顶,看着房里醒来的人,他们好像一夜没睡似的,眼睛都睁不开,变得又大又肿。
船夫费尔马诺夫是个阴沉的醉鬼,他从窗口探出头,头发乱蓬蓬的,肿胀的眼睛半睁不睁地望着太阳,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像一头野猪。外祖父在院子里用两只手捯饬了两下他那棕红色的头发,就匆忙到洗浴室里洗冷水澡了。房东家那个爱唠叨的厨娘,长着满脸雀斑,鼻子尖尖的,像一只杜鹃鸟。房东本人却像一只胖乎乎的鸽子。每个人都让人想起一种天上飞的鸟儿、地上走的牲口或野兽。
这天早上,天很晴朗,而我却有些郁闷,想离开这儿到空旷无人的野地里去——因为我心里明白,人们一样会把这干净的一天搞得乌七八糟。
一天,我正在屋顶上躺着,这时外祖母叫我下去。她对床那边点了点头,轻声说:“科利亚死了……”
那孩子躺在一块毡子上,脑袋在红枕头边上歪着,肤色发青。只见他下身光着,两条腿是歪的,上面满是脓疮,上身的褂子卷到了脖子上,露出膨胀的肚子,两手奇怪地在腰底下垫着,好像要托起自己的身体。
“走了也好。”外祖母一边梳头一边说,“不然这个畸形儿要怎么活下去啊!”
外祖父脚步轻快地走进来,像跳舞似的,他用手指轻轻地碰了碰孩子那闭着的眼睛。外祖母生气地说:“你怎么能用没洗过的手碰他呢?”
他吞吞吐吐地说:“哎,他来到人间……也算活过了,也吃过了……却没什么结果……”
“你去醒一醒吧!”外祖母打断他说。
他一脸无辜地看了看外祖母,走到院子里说:“我可没钱为他办丧事,你看着办吧……”
“呸,你这个倒霉虫!”
我从家里走出来,到了傍晚才回来。
第二天早上科利亚下葬,我没有到教堂去,做弥撒时,我和狗一起坐在母亲坟边,看着雅兹的父亲不停地刨母亲的坟墓。他挖坟的工钱要得比平常少,就总是在我面前自夸:
“这完全是看熟人的面子,否则至少得一卢布。”
黄色的坟墓中散发出一股恶臭,我向下看了看,发现坑底的边上有一些发潮的黑木板。我稍一动,坟墓周边的沙土就往下掉,一直掉到墓底,使边上显露出一些皱襞。于是我故意挪动身子,使沙子盖住那些木板。
“别乱动!”雅兹的父亲一边抽烟一边说。
外祖母双手捧着一口白木小棺材,这时“饭袋”就跳到墓底,接过去那口白木棺材,与黑木板并排放在了一起,然后从墓坑里跳出来,开始用脚和铲子把沙土堆到墓坑里。他的烟斗冒着烟,像教堂里的香炉。外祖父和外祖母也一言不发地帮着填土。没有一个神父和乞丐,在林立的十字架中,只有我们四个人。
外祖母在把钱递给守墓人时,责备他说:“你到底还是惊动了瓦留莎的棺材……”
“这样已经占了别人一些地了,没有办法的,不过没关系。”
外祖母对着坟墓磕了一个头,开始小声抽泣,随后哭声越来越大,哭完就走了。外祖父往下拉了拉帽檐,遮住了眼睛,拍平了身上的旧外套,跟在外祖母后面走了。
突然,外祖父说了一句:“种子都种在荒地里了。”然后像一只乌鸦似的,快速地跑到外祖母前面去了。
我问外祖母:“他怎么了?”
“别管他!他心里有事。”她回答。
天很热,外祖母走路很吃力,脚常常陷进热沙土里。她不时停下来用手绢擦脸上的汗。
我壮着胆问:“刚才坟墓里的那黑东西是妈妈的棺材吗?”
“是的。都怪那只笨狗,这还不到一年呢,瓦里娅
 就烂掉了!也是因为沙土渗水,要是黏土就好了……”外祖母生气地说。
就烂掉了!也是因为沙土渗水,要是黏土就好了……”外祖母生气地说。
“每个人最终都会腐烂吗?”
“是的,都会烂掉。只有圣徒除外……”
“你就不会腐烂!”
她听后停了下来,正了正我的帽子,然后神情严肃地说:“你不应该想这些的,知道吗?不要再想了。”
但我心想:“死亡是一件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哎,真是令人厌恶!”
我感到很伤心。
我们一回到家,发现外祖父已经沏好了茶,在桌上摆好了茶具。
他说:“天气很热,快来喝点茶吧,我已经用我的茶叶泡好茶了,足够大家喝的。”
他朝外祖母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问道:“老太太,怎么样啊?”
外祖母摆了摆手:“没什么可说的!”
“就是啊!主生我们的气了,就把我们的子孙一个个叫走了……要是全家都活得结结实实的,像手上的五根指头那样该多好啊……”
他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这么和善地说过话了。我听着他说话,期望他能驱走我心里的忧郁,帮我忘掉那个深黄色的坟墓坑和那些发潮的黑木板。
可外祖母却厉声厉色地打断了他:“别说啦,老头子!你说这话说了一辈子,别人听了心情只会更加沉重。你这一辈子啊,就像那铁锈,把别人都锈烂了。”
外祖父瞟了她一眼,咳嗽了一声就不作声了。
傍晚,我和柳德米拉在大门口坐着,我很烦闷,就给她讲我早上经历的事情,但她听后反应并不强烈。
“做个孤儿倒好些。要是我成了孤儿,我就把妹妹托付给哥哥,然后自己跑去修道院修行,在那里待一辈子。像我这样的瘸子,不会做工,也没人愿意娶,说不定生出的孩子也是个瘸子呢……”
她和街上其他女人一样,老是讲这些感慨的话。似乎这晚之后,我就不再觉得和她在一起很有意思了,而且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因此我和她走得越来越远了。
弟弟死后没几天,外祖父对我说:“今晚你早点睡,明天天一亮,我就叫醒你,我们一块儿到树林里砍柴……”
“那我也跟着去搂草。”外祖母说。
在距离村子大约三俄里远的一片沼泽地旁,有一片树林,里面是云杉和白桦,地上有许多枯枝和倒下的树木。这片树林一边延伸到奥卡河,另一边扩张到了莫斯科公路,公路另一边依然是这片树林的延伸。在这片林子的上方,还耸立着一片名叫“萨韦洛夫岗”的松树林,郁郁葱葱的,像一个帐篷。
这些树林的主人是瓦洛夫伯爵。但他没有保护好这些树林,库纳维诺区的市民们都已把这些树木据为己有了,他们常到这儿来捡树枝,砍枯树,碰上好的机会时,连好树也不放过。每到秋天要储备过冬柴火时,几十个人便手拿斧子,腰带绳子,进树林砍树去了。
第二天黎明时,我们三个就出发了,走过满是晨露的银绿色草地。在我们左边的奥卡河对岸,在棕红色的啄木鸟山上空,在白色的下诺夫哥罗德城上空,在葱翠的果园的山丘上,在教堂的金色圆顶上,俄罗斯的太阳正慢悠悠地升起。微风缓缓拂过平静而浑浊的奥卡河,金黄的毛莨被晨露压得低着脑袋,轻轻摇晃,紫色的风铃草也低下了头,多彩的蜡菊在荒芜的草地上直直地站着,享有“小夜美人”之称的石竹花绽放出朵朵星形的红花。
树林如一支黑色的军队,朝着我们前进。云杉如一只大鸟,伸展着翅膀,白桦树则像一个少女。沼泽的臭气从田野那边吹了过来。狗走在我旁边,吐着红舌头,不时地停下来嗅嗅地面,然后不知所以地摇晃着它那狐狸似的脑袋。
外祖父头戴一顶没檐的破帽子,身披着外祖母的短上衣,觑着眼睛在笑,让人很不解。他小心谨慎地迈开两条瘦腿,那样子像是在偷东西。外祖母头戴白毛巾,上身穿蓝色的外衣,下身穿一条黑裙子。她走得很快,我快跟不上她了。
越靠近树林,外祖父就越兴奋;他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不时发出感叹声,起先这感叹声时断时续,不太清楚,后来他沉醉了,兴奋地说道:“森林是上帝的花园,不是别人种的,是上帝从嘴里吹出的风把它养育起来的……我年轻的时候到过日古利,当过船夫,哎,列克赛,你是见不到我经历过的事情的!奥卡河一带的大森林,从卡西莫夫一直覆盖到穆罗姆,还有从伏尔加河到乌拉尔的区域,真是太大了,简直看不到边际!”
外祖母斜眼瞥了他一眼,向我使使眼色。他呢,被脚下的石块绊得踉跄着,嘴里还不时地叨念着,这些话都念到了我的记忆深处。
“一次,我们从萨拉托夫出发,坐在一条大油船上,准备开到马卡里去赶集,管家是普列赫人,叫基里洛;船长好像叫阿萨夫,是鞑靼人,家住卡西莫夫……船行到日古利,刮起了上游风,累得我们筋疲力尽,两条腿都打战,于是我们就停了船,上岸做饭吃。那会儿正是五月,伏尔加河的波浪一批一批地向里海翻滚着,像大海上空成群的白天鹅。在春天里,日古利的山郁郁葱葱的,高高的山顶耸入云霄,那白云正好像牧场上的一只只羊。天空中白云飘荡,阳光照在大地上,像铺了层金子。我们边休息边欣赏着风景。寒冷的北风吹过河面,岸上却很温暖,香气扑鼻。到了晚上,上了年纪的基里洛(他很厉害)站了起来,他摘下帽子说:‘小伙子们,我就要到森林里去了,不再为你们管事了,不再做你们的仆人了,你们各自请便吧!’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觉得很惊讶。没有人替老板管事了,这可怎么办啊?虽然这是伏尔加河,但也很有可能迷路的,没有主事的不行啊。这帮人像野兽般冲动鲁莽,什么事做不出来?大家都被吓坏了。但他心意已决:‘我不想再做你们的牧人了,想换种活法,我要到森林里去!’有人把他捆起来,想揍他一顿;有人不知所措,忙喊:‘慢着!’更糟糕的是,船长也走过来说:‘我也走!’这个鞑靼人已经跑了两趟船了,这第三趟也走了一大半了,东家还没付他钱,他走完这趟就可以拿到一大笔钱。大家就这样吵到了深夜,已经有七个人离开了,剩下的不是十六个就是十四个。都是那些森林惹的祸!”
“他们是去做强盗吗?”
“也许吧,也有可能是隐居山林了,那时候没人管这些的……”
外祖母在胸前画了个十字:“至高无上的圣母啊!老百姓都很可怜啊。”
“每个人都是有想法的,怎么会知道魔鬼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呢……”
我们顺着一条潮湿、狭窄的路,穿过了沼泽地的土台和细小的云杉林,走进了树林。我觉得普列赫人基里洛的选择——在森林里待一辈子也不错,在那里没有人絮叨,没有人打架、酗酒;那里会使人忘记外祖父般的吝啬,忘记母亲的沙土坟,忘记所有使人烦闷、痛苦的事情。
外祖母选了一块干燥的地方说:“坐下来吃点东西吧!”
她的篮子里装满了食物,有黑面包、黄瓜、盐以及用布包着的奶渣。看到这些,外祖父愧疚地眨眨眼说:“哎,好老伴,我没有带什么吃的……”
“这些够咱们吃的……”
我们背靠着松树干坐了下来,这古铜色的松树可以用来做桅杆。空气中弥散着松脂的味道。微风从旷野上吹来,木贼草摇曳着。外祖母伸出又粗又黑的手去采野草,还一边对我讲金丝桃、药慧草、车前草的药用价值,还有蕨菜、黏手的柳兰、满是灰尘的水鼠草的神奇功效。
外祖父把倒下的树木劈碎,命令我把这些柴搬到一起,我却偷偷跟着外祖母到密林里去了。在一排排粗大的树木中,她走得很慢,经常像把头扎进水里一般,向铺满针叶的地面弯下腰;还边走边自言自语:“又来早了,蘑菇大多还不能采呢!上帝啊,你总是不体谅穷人,蘑菇可是穷人的美味啊!”
我默不作声地跟在她后面,不让她发现。我不想打扰她与上帝、青草、青蛙等之间的谈话。
但还是被她发现了。
“你怎么从外公那儿过来了?”
然后她又弯下了腰,地上长满了青草,像披着一件美丽的绣花外套。她说道:“上帝有一次发怒,用洪水吞没了大地上的所有生物。”
“但心怀万民的圣母把采来的所有种子藏在篮子里,于是她恳求太阳:把整个大地晒干吧,万民会赞美您的壮举的!太阳晒干了大地,圣母就把藏好的种子播撒在了大地上。不久上帝看见地上又出现了生物:草木、走兽、人类……便问谁做了违背他旨意的事,圣母就承认了。其实上帝心里已经后悔让大地变得光秃秃的了。于是便对圣母说:你做得很好!”
我喜欢这个故事,但又有些不懂,就神情严肃地问:“可这是真的吗?不是洪水过去之后很久,圣母才出生的吗?”
外祖母听后很惊讶:“这话你听谁说的?”
“学校教科书上这么写的……”
她听后便舒了一口气,劝我说:“你忘掉书上的那些说法吧!书上全是胡说的。”
她扭过头开心地笑了。
“蠢货,全是胡乱编造的!有了上帝,母亲却还没有出生,那上帝是谁生的啊?”
“我不知道。”
“这还算学过的呢,到头来学会个‘不知道’!”
“神父说,是亚基姆和安娜
 生了圣母。”“那她是不是叫马利亚·亚基莫芙娜
生了圣母。”“那她是不是叫马利亚·亚基莫芙娜
 ?”
?”
外祖母听后生气了,非常严厉地盯着我说:“以后你要是再这么想,我就狠狠地教训你一顿!”
过了一会儿,她又跟我解释:“圣母的出生早于任何人!她生了上帝,后来……”
“那基督呢?”
外祖母不回答我了,有些尴尬地闭上了眼睛。
“基督……嗯,是啊,嗯?”
我知道我赢了,关于神界的秘密,我把她搞晕了,但我心里并不开心。
我们不断地向树林深处走去,走到一片布满幽暗的地方,几缕阳光照射进来。在这片温暖舒适的树林里,有一种奇怪的、梦境般朦胧的响声,使人充满遐想。交喙鸟发出吱吱的叫声,山雀啾啾地啼鸣,杜鹃发出咕咕声,像是在笑,金莺吹着口哨,嫉妒心强的金翅雀不停地唱歌,蜡嘴鸟深沉地吟唱。翠绿的小青蛙在人的脚边蹦来蹦去,一条黄颔蛇躺在树根前,抬起头,窥视着青蛙。松鼠翘着毛茸茸的尾巴从树梢一闪而过,发出吱吱的叫声。这里有太多可看的新奇事物了,令人有些应接不暇了,即使这样,还是想看更多,想往更深处走去。
一行行松树之间,飘散着半透明的薄雾,像巨人的影子,不一会儿就消失在了绿林中。接着蓝天白云就透了出来。脚下的地毯似的厚青苔,像是绣着一丛丛越橘和干酸果蔓。石莓果的颜色鲜艳欲滴,一个个从草中探出头来。蘑菇浓浓的香气扑进了人的鼻孔里。
“圣母啊!人世的灿烂光辉啊!”外祖母边祈祷边感叹。
她好像是这森林里所有生物的主人和亲人。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像熊,看到任何东西都心存感激和赞许。似乎有一股暖流从她身上发出来,弥漫了整片森林。看着被她踩过的青苔再次舒展开,我觉得很开心。
我边走边想:做一个强盗多好,劫富济贫,让大家不缺食物,每天开开心心,没有仇恨,没有争吵。要是能见到外祖母的上帝、圣母,我就把这个世界揭露给他(她)看:人们遭受着什么样的生活磨难,他们如何通过恶劣的手段,彼此埋葬于贫瘠的沙土里。简而言之,这世上有很多悲惨的事情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圣母相信我,就恳求她赐予我一些智慧,让我有能力将世界变得美好一些。我会带领大家找到一种更加美好的生活。我的年龄不是问题,基督只比我大一岁时就有很多智者听从他的话了
 ……
……
正想得出神,突然掉进了一个深坑里。我的腰被树枝擦破了,后脑皮也被擦掉了一小块。我坐在坑底如松脂般黏的、冰冷的泥里,十分羞愧地意识到自己爬不出去了,却不好意思打扰外祖母。但最后,我还是叫她了。
她急忙把我拉上来,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说:“感谢上帝!幸亏熊洞的主人不在,否则就麻烦了。”
她感激得流出了眼泪。接着带我到一条小溪边洗了洗,在我伤口处贴上一种能止痛的草药,又从她的衣服上撕下一条布带为我包扎伤口,这时我已经筋疲力尽了,身子很虚,根本不能走回家,于是她把我带到了看守铁路的小屋里。
此后,我几乎日日恳求外祖母:“咱们去森林里吧!”
每次她都高兴地答应我。就这样,我们度过了整个夏天,又这样到了深秋,我们一直采摘草药、野果、蘑菇、坚果之类。外祖母靠卖这些采来的东西维持生计。
尽管我们没吃外祖父一点东西,他还是骂我们“饭桶”!
森林给我带来了精神上的安宁,为我驱走了一切烦恼与悲伤,同时也增强了我感官的敏锐程度:我的视觉和听觉变得更加灵敏了,记忆力在长度和宽度方面,都增强了。
对于外祖母,我越来越感到吃惊,我觉得她很高贵,是那种万人都不及的,她是世界上最善良最睿智的人。而且日积月累,她使我越来越肯定自己的这种感觉了。有一次,傍晚我们采完了白蘑菇要回家,刚走出森林,外祖母坐下来休息。我想看看还有没有蘑菇,就进树林里了。
突然听到外祖母的声音,扭头一看,她正坐在一条小道上,平静地揪掉蘑菇的柄,她身旁站着一条灰色的狗,那狗瘦瘦的,吐着舌头。
“走吧,走开!愿上帝保佑你!”外祖母对它说。
不久前,我的狗被瓦廖克毒死了,我很想养这条狗。我跑过去看,发现那条狗却奇怪地弓着身子,脖子也耷拉着不动,只是抬起它那双饥饿的绿眼睛瞅了我一眼,就夹着尾巴跑回树林中了。它的身形和动作并不像狗,我吹了个口哨,只见它迅速地钻进了灌木丛中。
“看见没?”外祖母微笑着问,“一开始我也以为它是一条狗呢,但仔细一看发现它长着狼牙,脖子也是狼脖子!我心里不禁一颤,就对它说:‘如果你是只狼,就离开吧!’幸亏现在是夏天,狼的攻击性还不那么强……”
外祖母每次都能找到回家的路,从没有在森林里迷路。凭借一草一木的气味,她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蘑菇长什么样,那个地方的香菇长什么样。还常常考我:“什么树上长有黄菇?如何区分好的和有毒的红菇?喜爱蕨薇的是哪种香菇?”
她看见树皮上有模糊的爪痕,就告诉我这儿有松鼠洞。我爬上树,从洞里掏出松鼠们储备的冬粮——榛子,有时候一个洞里有十多磅榛子。
有一回我正在掏松鼠窝,一个猎人把二十七颗打鸟的铁砂打进了我的右侧身内。外祖母拿针给我挑出来十一颗,剩余的在我皮里待了好几年,后来也慢慢都出来了。
我忍住了痛,外祖母很欣慰。
她夸奖说:“好孩子,有忍耐力就能练出本事!”
每次卖榛子和蘑菇回来,她都要拿出一点钱偷偷地放在人家窗台上。但她自己,即使到了过节的日子,也穿得很破旧。
外祖父很生气:“你穿得还不如要饭的,真给我丢脸!”
“这没什么,我又不是你闺女,更不是要嫁人的大姑娘。”
他们拌嘴的频率越来越高。
“我的罪孽并不比别人深重,为什么要比别人受更多的罪!”外祖父抱怨道。
外祖母就嘲讽他:“只有鬼才知道谁的罪深,谁的罪浅。”
后来,外祖母偷偷告诉我说:“这老头儿怕鬼,就是因为怕鬼,他才老得这么快……唉,可怜啊……”
这个夏天,由于经常到森林里,我身体变得强壮了,性子也变野了,也就不再对同龄人的生活和柳德米拉感兴趣了,我认为她是一个聪明但无趣的人。
秋天的一天,天正在下雨,外祖父从城里回来,浑身都湿透了,在门口像只麻雀似的抖抖身上的雨水,然后得意地说:“嘿,你这整天无所事事的人,收拾一下吧,明天要去上班了!”
“到哪儿去啊?”外祖母生气地问。
“你妹妹马特廖娜儿子的家里……”
“老头子,哎,你怎么又出了个馊主意!”
“闭嘴,你这愚蠢的家伙,没准儿以后他能成为一名绘图师呢。”
外祖母低下了头,没有再说什么。
傍晚,我告诉柳德米拉我要离开这里进城去了,要在那里生活了。
“不久家里也要把我送进城了。”她若有所思地说,“为了让我身体变好,爸爸打算把我这条腿完全截去。”
过了一个夏天,她的脸色有些发青,瘦了许多,只有眼睛变大了。
我问她:“你害怕吗?”
“害怕。”说完她无声地抽泣起来。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因为我也害怕去城里生活。我俩紧紧地相互靠着,内心充满忧愁,就这样默默地坐了很久。
如果是在夏天,我会劝说外祖母,让她像年轻时候一样出去讨饭,带上柳德米拉,我用小车推着她走……
可这是在秋天,潮湿的风吹过大街,天空中布满阴云,大地也拧着脸,变得肮脏而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