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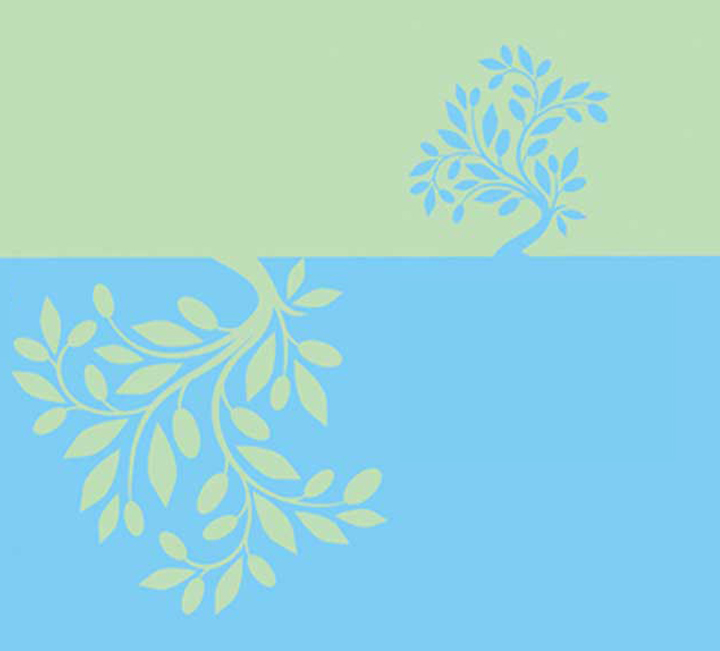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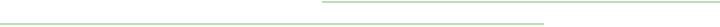

我来到人间,在城里街道旁一家“时式鞋店”里当学徒。

我的老板个头很矮,体形肥胖,他那黑得发红的脸很粗糙,牙齿呈青绿色,眼角塞满了眼屎。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开始扮各种鬼脸。
“不要扮鬼脸。”他声音不大但却很严厉地说。
这双浑浊的眼睛看得我很不自在;但我还是不相信他能看见我,我觉得他只是凭直觉猜出我在扮鬼脸吧。
“我说了,不要扮鬼脸。”声音更低了,但说这话时他那厚厚的嘴唇几乎都没有动。
“别挠手。”又传来了他那低沉、干巴巴的声音,“记住,你现在在城里大街上的一等店铺里做学徒,就应该像一座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地站在店门口……”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从手到臂肘,疥癣虫咬得我的两只胳膊全是红斑和脓疮,难受得我不得不挠手。
“你在家里做什么活儿?”老板盯着我的手问道。
我刚说完,他就摇了摇他那长满白发的脑袋,不屑地说:“捡破烂儿啊,还不如要饭的呢,也比不上那偷东西的。”
听他这么说我立马得意地说:“我以前也偷过东西呢。”
听到我说这话,他突然像猫伸出爪子似的,将两只手往账桌上一撑,吃惊地眨了眨那双瞎子般空洞的眼睛,瞪着我说:“什么?你还偷过东西?”
于是我将偷东西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噢,这倒是小事,我们不会计较的。但你要敢在我这儿偷鞋、偷钱,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送到监狱里,一直关到你长大……”
他说这话时表现得很和气,却着实把我吓坏了,我也因此更加讨厌他了。
店铺里除了老板,还有雅科夫的儿子——我的表哥萨沙,另外还有一个稍大点的红脸伙计,这个人伶牙俐齿,很会招揽生意。而萨沙身着一件红褐色礼服,戴着衬胸,扎着领结,散着裤腿。他态度傲慢,从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时,曾嘱托萨沙凡事要多照应我。萨沙皱着眉头,趾高气扬地说:“那他得听我的话。”
外祖父伸出一只手将我的头按下:“论年龄,萨沙比你大,论职位,萨沙也比你高,你得听他的话啊……”
萨沙顺势瞪着我说:“你可别忘了外祖父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就仗着他有点资格,开始颐指气使地对我摆起谱儿来。
“卡希林,别老瞪眼!”老板说。
“老板,我没有。”萨沙低下了头;然而老板仍继续说道:“别老是板着一张脸,顾客会当你是一头公山羊的……”
那位稍大点的伙计向顾客赔着笑脸,老板也难为情地咧了咧嘴,而萨沙红着脸,灰溜溜地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对话,好多我都听不懂,有时甚至觉得他们在讲外国话。
每当有女顾客上门时,老板便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捋捋他的鬓发,然后堆起满脸甜甜的微笑。这时他的脸上便布满了皱纹,但那双瞎子般浑浊的眼睛却没有一丁点儿变化。那位稍大点的伙计挺直身子,两只胳膊紧贴腰部,然后毕恭毕敬地摊开双手。而萨沙却紧张得不断眨眼,他极力想掩盖那暴出的眼珠。我则站在店门口,一边偷偷地挠手,一边留心观察他们做买卖的规矩。
那位稍大点的伙计走到女顾客面前跪下来,然后张开手小心翼翼地为女顾客量鞋的尺寸,生怕把女人的脚碰坏了。其实这位女顾客的脚很肥,像一个倒放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在为一位太太量脚时,这位太太的脚不停地动,她缩起身子说:“哎呀,你弄得我好痒啊……”
“这个,是出于礼貌,太太!”大伙计连忙解释道。
看着他对女顾客做出的肉麻动作,实在搞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急忙扭过脸去对着玻璃门,可我又忍不住想要观察他们做生意的样子,而同时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学会那样毕恭毕敬地张开手,动作灵巧地为顾客穿鞋。
平时老板常和萨沙待在柜台后面的账房里,只留下大伙计一人招待女顾客。有一次,来了一位棕红色头发的女顾客,他摸了摸那女人的脚,然后将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送到自己的嘴边吻了吻。
“哎——哟—,你这个调皮鬼!”那位女顾客嗔叫道。
大伙计就鼓起腮帮子,使劲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啧啧!”
看到这儿,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站都站不稳了,于是赶紧扶住门把手,门被猛地推开了,我一头撞在了玻璃上,玻璃碎了。那位大伙计冲着我直跺脚,老板用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脑袋,萨沙也要动手拧我的耳朵。傍晚同路回家时,萨沙严肃地训斥我:“这有什么好笑的?你再这样胡闹,人家会把你赶走的!”
他向我解释,大伙计讨太太们的欢心,是为了店里的生意能兴隆起来。
“太太们有时就算不需要买鞋,也会跑到店里来看一眼这个讨人喜欢的伙计,捎带再买双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真叫人操心……”
这话让我很生气,我没让任何人替我操过心,更别说他了。
每天早晨,病恹恹、爱发脾气的厨娘总是先叫醒我,过一小时后才叫醒萨沙。我起来后要为老板一家人、大伙计以及萨沙擦好皮鞋,洗好衣服,烧好茶水,为所有炉子准备好柴火,还要把午饭用的饭盒洗刷干净。到了店铺,我还要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送货,然后再到老板家取午饭。每每这段时间,萨沙便不得不代替我在店铺门口站岗。他觉得站在店铺门口很没面子,就责骂我:“懒家伙,让别人替你干活儿……”
在这里,我嗅到了乏味、沉闷的气息。我已经习惯了从早到晚待在库纳维诺区
 用沙土铺成的道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和树林中的生活。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伙伴,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在这里,生活向我袒露出它那丑恶虚伪的本质,这令我愤怒。
用沙土铺成的道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和树林中的生活。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伙伴,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在这里,生活向我袒露出它那丑恶虚伪的本质,这令我愤怒。
经常有女顾客什么也没买就走了,每次碰到这种情况,他们三个就很气愤。老板会立刻收起他那甜甜的笑容,然后命令萨沙:“卡希林,把货收起来!”
随后便骂道:“呸!这头蠢猪跑到我这儿来啦!这个臭婆娘肯定是自己在家闲得发闷,就跑到人家铺子里瞎逛。她要是我婆娘,我可要给她点厉害尝尝……”
他的老婆有一双黑色的眼睛,鼻子很大,身材又干又瘦,经常像对待下人一样,对他又跺脚又责骂的。
他们经常一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卑躬屈膝,献殷勤,说各种奉承讨好的话,可一送走她们,便用各种脏话骂这些女顾客。每次听到这些脏话,我都恨不得跑出去追回那个女顾客,把他们说的脏话全告诉她。
当然,我也知道背后说别人坏话这样的事很常见,可这三个家伙议论他人的话真的非常可恶。好像觉得他们自己是最了不起的,甚至可以担任全世界的法官。他们嫉妒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也从不夸赞别人,对每个人的缺点都略知一二。
有一次,一个女郎来到店里,她脸色红润,双瞳明亮,身披天鹅绒大衣,上面镶着黑皮毛领,在黑皮毛领的映衬下,她的脸如鲜花一般漂亮。她将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萨沙,如此显得更加漂亮了。她那苗条的身材紧裹在蓝灰色的绸衣里,耳朵上的钻石很耀眼。她使我想起了美丽无比的瓦西莉萨
 ,我断定她是省长夫人。老板和店员们对她点头哈腰,说尽了讨好的话,他们大气不敢出,像捧着一盆火似的。这三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里来回跑,货架上的玻璃掠过他们的影子,好像周围的东西着了火,正在渐渐熔化,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形状,另一种样子啦。
,我断定她是省长夫人。老板和店员们对她点头哈腰,说尽了讨好的话,他们大气不敢出,像捧着一盆火似的。这三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里来回跑,货架上的玻璃掠过他们的影子,好像周围的东西着了火,正在渐渐熔化,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形状,另一种样子啦。
这位女郎很快就选中了一双价格昂贵的皮鞋,然后离开了。
她一离开,老板就吧嗒了一下嘴,吹了一声口哨,骂道:“这只母狗……”
大伙计也轻蔑地随声附和:“她不过是个女戏子!”
于是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这个女郎的一些情人以及她那奢华糜烂的生活。
吃过午饭,老板便到店铺后面的小屋里午睡了,我趁机打开他的金怀表,往里面滴了几滴醋。他醒后惊慌地跑出来,手里拿着那块怀表问:“这是怎么回事?怀表冒汗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难道要出什么乱子吗?”
而我在一旁窃喜。
尽管每天奔忙于店铺和家里的各种杂事琐事中,我仍感到很无聊,很烦闷。我常常自己盘算着:干一件什么事才能让他们把我从铺子里撵走呢?
一些行走在大街上的路人,身上落满了雪花,他们行色匆匆地从店铺走过,像是落了队的送葬人,急着追赶前面的棺材。马蹒跚地拖着车子,吃力地轧过雪堆。店铺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传来凄凉的钟声,告诉人们大斋期到了。那一下一下的钟声就像枕头敲打在脑袋上,不痛不痒,却使人麻木,耳朵发鸣。
一天,我正在店铺门前的院子里清理刚送到的货箱,这时在教堂里看门的歪脖老头儿走到我跟前。他身体很脆弱,软得像布人似的,身上的衣服像被狗撕咬过一般破烂不堪。
他对我说:“上帝啊,可不可以给我偷一双套靴啊?”
我没有回应他。于是他在一个空箱子上坐下,打了个哈欠,然后在嘴上画了个十字
 ,又说:“你给我偷一双吧,好吗?”
,又说:“你给我偷一双吧,好吗?”
“不能偷东西!”我回答他。
“可是有人偷啊,你应该尊重老人!”
我很喜欢他,他和我周围的其他人不一样。我感觉他判定我会为他偷东西,于是我答应他从通风窗里递给他一双套靴。
“那好,你不是在骗我吧?嗯,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会骗我的……”他很平静地说。
他的靴子踩在脏兮兮的泥雪上,他用土烧烟斗抽着烟,静静地在这儿坐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吓唬我说:“要是我骗你呢?我一拿到靴子就去找你的老板,说这双靴子是花半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而事实上这双靴子价值两卢布多,那你怎么办?啊?你只卖了半卢布,那剩下的钱去哪儿了?你买糖吃了?”
似乎他已经照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做了,我呆住了,盯着他。他一边嘴吐青烟,一边瞧着自己的长靴,继续轻声地嘟囔道:“如果是你的老板指使我来试探试探你:看那小子是不是个贼坯子,你怎么办啊?”
“那我不给你套靴了!”我生气地说。
“你已经答应我了,不能说话不算数。”
他一把抓起我的手,将我拽到他跟前,用他那冰凉的手指敲了敲我的脑门儿,懒洋洋地说:“你怎么轻易就说:‘给,拿去吧?!’”
“是你要求我这样做的。”
“我的要求多着呢!那我要你去抢劫教堂你也去吗?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相信陌生人呢?唉,你这个小傻瓜……”
说完,他把我推到一边,站起身来:“我穿不着偷来的套靴,我又不是阔老爷。我就是和你开个玩笑……看你这么老实,你可以在复活节那天到钟楼上敲敲钟,看看这座城的风景……”
“我很熟悉这座城。”
“可从钟楼上望下去,它很漂亮啊!”
他慢悠悠地用靴尖踩着雪,朝教堂的拐角走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不安:这老头儿就只是开个玩笑?还是真的受老板之托来试探我的?我甚至都不敢进店铺了。
突然萨沙闯进院来,朝我大吼道:“你在搞什么鬼?”
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火,抡起钳子就朝他甩了一下。
萨沙和那个大伙计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皮鞋或便鞋藏在火炉的烟囱里,走之前悄悄地往外套的衣袖里一塞,就离开了店铺。我很厌恶这种事,也有些恐惧,我仍记得老板对我的恐吓。
我问萨沙:“你偷东西啊?”
他急忙解释道:“我没有偷,是那个大伙计偷的,我只是帮他个忙,大伙计说‘你要帮我!’,我不得不帮他,不然他会为难我的。其实咱们的老板也是从伙计走过来的,他什么都知道。但你可不能瞎说!”
他一边说,一边学着大伙计的样子在镜子前张开手不自然地摆弄着领结。他总爱在我面前摆谱,还大声训斥我,以显示他的威风。每次支使我干活儿,他总是伸出胳膊,似乎要把我推开。虽说我个子比他高,力气也比他大,但却骨瘦如柴,还很笨。而他油光满面,身材圆润,动作灵巧。他穿着礼服,散着裤腿,给人一种威严气派的感觉,但在我看来却很滑稽,可笑。他厌恶那个厨娘,厨娘也确实很怪,不知道她人是好还是坏。
“这世上的事啊,我最喜欢的就是打架了。”她瞪着那双乌黑的、如火焰般发光的眼睛说,“无论是斗公鸡、斗狗,还是人打架,我都喜欢!”
院子里一有公鸡或鸽子打斗,她就立马放下手中的活儿,然后全神贯注地盯着窗外,直到打斗结束为止。每天晚上她都会对我和萨沙说:“你们俩小子在这儿干待着多没劲啊,还不如打场架呢!”
萨沙很生气:“傻婆娘,我才不是什么小子呢,我是个小店员!”
“哟,是吗?在我看来啊,没娶婆娘的都是小子!”
“你这个婆娘,傻乎乎的……”
“魔鬼倒很聪明,可上帝不喜欢。”
她说的这句谚语惹恼了萨沙,于是他就嘲讽她。可她毫不生气,不屑地瞟了他一眼说:“哼,上帝真是错生了你,你这只蟑螂!”
萨沙经常唆使我趁厨娘睡着的时候,往她脸上抹鞋油或煤烟灰,要不就是在她枕头上扎上一些大头针,或是想其他一些捉弄人的办法。可是我很怕厨娘,她睡觉很轻,经常会醒过来,一醒来她就点亮油灯,呆呆地盯着墙角。有时候,她就绕过炉灶来把我叫醒,声音沙哑地请求我:“我睡不着,列克赛伊卡
 ,我很害怕,你能陪我说说话吗?”
,我很害怕,你能陪我说说话吗?”
于是我只好半睡半醒地和她说点什么,她静静地坐在那儿,摇晃着上身。从她那温热的身体上散发出的蜡味和神香味
 ,让我感觉她快要死了,可能马上就会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死掉。想到这儿我很害怕,说话声不由得放大了,她立马阻止我说:“小点声!要是把那些坏蛋吵醒了,他们会乱猜疑的,他们肯定会以为你是我的情人……”
,让我感觉她快要死了,可能马上就会一头栽倒在地板上死掉。想到这儿我很害怕,说话声不由得放大了,她立马阻止我说:“小点声!要是把那些坏蛋吵醒了,他们会乱猜疑的,他们肯定会以为你是我的情人……”
她在我身边坐着,一动不动,总是弯着背,两手插在膝盖中间用腿骨夹着。她的胸部扁平,即使穿着厚厚的麻布衫也能显现出那一根根肋骨,像干裂的木桶上的一道道铁箍。静静地坐了很久,突然她低声说道:“还不如一了百了地死了,省得心里烦闷……”
又好像在问别人:“我还不死吗?还没活到头吗?”
我刚说了一句“睡吧!”她就直起腰来,然后她那灰色的身影就默不作声地消失在了厨房的黑暗中。
萨沙在背后称呼她为“巫婆”。
于是我怂恿他:“你当着她的面这样叫一声!”
“你以为我不敢吗?”但他立马又神情严肃地说:“不行,我不能当着她的面这样叫,万一她真是个巫婆呢……”
厨娘很爱发脾气,对谁都很不客气,包括我在内。每天早晨一到六点她就来揪起我的大腿吼道:“快起来!赶快去搬柴火!烧茶!削土豆!……”
萨沙被吵醒了,生气地叫道:“吵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啦!我要告诉老板去……”
骨瘦如柴的厨娘在厨房里很迅速地来回走动,她眨了眨那因睡眠不足而红肿的双眼,瞪着萨沙说:“哼,上帝瞎了眼,错生了你这个东西!我要是你后妈,绝对收拾你。”
“她真该死!”萨沙骂道。在去店铺的路上,他撺掇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让她被老板赶走。这样,悄悄地往所有的菜里多加点盐,菜炒得那么咸,老板肯定撵她走,或是往菜上倒点煤油,怎么样,你干吗?”
“你怎么不干?”
他生气了,哼了一声:“胆小鬼!”
厨娘的死我们都看见了。当时她正弯腰去端茶炊,突然,胸口像被谁推了一下似的坐在了地上,随后无声地向一侧栽倒下去,两只胳膊向前伸着,嘴里流出了血。
我俩立刻意识到——她死了。当时我们吓傻了,盯了她很长时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后来萨沙冲出了厨房,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靠在了窗边有光亮的地方。老板走进来,神情很忧虑,他蹲下来用手指碰了碰厨娘的脸,说:“她真的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对着屋角处的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小圣像,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并做了祷告后,就在前室命令道:“卡希林,快去警察局报警!”
警察来了,在屋里转了一圈,拿了点小费就走了。没一会儿,他带着一个马车夫回来了,他俩分别抬起厨娘的头和脚,把她扔在了大街上。老板娘从前堂里朝这儿看了看,对我说:“把地板擦干净!”
然而老板说:“幸亏她是在晚上死的……”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晚上死好?到晚上要睡觉了,萨沙以从未有过的口吻温柔地对我说:“你别关灯!”
“你害怕吗?”
他用被子盖住头,躺在那儿大气儿也不敢出。夜静悄悄的,似乎在聆听着什么,等待着什么。我隐隐觉得:钟声就要响起,霎时间,全城的人会喊叫着四处奔跑,乱作一团。
萨沙从被子里露出鼻子,轻声地说:“咱们一块儿到炉炕上睡吧,行吗?”
“炉炕上太热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她怎么突然就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难不成她真是巫婆……我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于是萨沙开始讲死人的故事,他讲死人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到城里寻找自己以前居住的地方和亲人的住所,就这样游荡着一直到半夜。
“但死人只记得城市的位置,却记不得具体的街道和房屋……”他小声说。
周围更安静了,也更黑暗了,萨沙稍稍抬起头问:“想不想看看我的箱子?”
我早就想知道他箱子里装的什么了。平时箱子被锁着,每次他开箱子时,总是很小心翼翼,要是我稍微凑近点想看一眼,他就粗鲁地大声问:“你想干什么?啊?”
我同意后,他就从床上坐起来,也不下床,而是命令我把箱子搬到床上,放到他脚跟前。他把钥匙和十字架拴到一条带子上,平时就戴在脖子上。在开箱之前,他朝厨房黑暗的角落瞥了一眼,然后得意地皱起眉头,锁打开了,他对着箱子吹了吹,好像那箱盖烫手似的,然后他从箱子里拿出了几件衣服。
药盒、包茶叶用的五颜六色的商标纸、鞋油盒和鱼罐头盒等足足占了半个箱子。
“这是什么啊?”
“你一会儿等着瞧吧……”
他用两条腿把箱子夹住,上身前倾趴在了箱子上,然后轻声哼唱道:“愿主……”

我期待着看到玩具。我不曾有过玩具,尽管表面上我装作不在意,可看着别人的玩具,心里真的很羡慕。虽然萨沙不好意思地把玩具藏了起来,但我很理解这种害羞的心理,也很高兴他这么大了还有玩具。
他打开第一个盒子,从里面拿出一副眼镜框,然后架在鼻梁上严肃地看着我说:“没关系,这种眼镜就是这样,本来就没有镜片。”
“让我戴戴!”
“这眼镜适合黑眼睛戴,你的眼睛是灰色的,不合适。”他解释着,然后学着老板的样子咳嗽了一声,但马上就胆怯地环顾了一下厨房四周。
一个鞋盒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扣子,他很得意地说:“这些都是我自己从大街上捡来的。到现在已经捡了三十七颗了……”
第三个盒子里有铜大头针,有磨损的皮鞋后跟铁掌、皮鞋或便鞋上完整的和破损的扣子、铜质门把手、坏了的手杖骨雕柄、一把少女用的梳子、一本名为《圆梦与占卜》
 的书,还有很多其他价值类似的东西,这些也都是从大街上捡来的。
的书,还有很多其他价值类似的东西,这些也都是从大街上捡来的。
以前我捡破烂儿的时候,一个月就能轻松地捡到他这些东西的十倍还多。看到这些我很失望,有些恼火,但又觉得萨沙很可怜。可他却像对待珍宝似的全神贯注地欣赏着每一件东西,用手抚摩着它们,神情庄重地噘起那厚嘴唇,暴出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情。然而那副眼镜框却使他稚气的脸显得很滑稽。
“你攒这些东西做什么?”
他透过眼镜框瞥了我一眼,用清脆稚嫩的声音问道:“你想要我送你点什么呢?”
“不,不用了……”
很显然,他生气了,因为我拒绝了他,因为我不是很重视他的这些东西。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低声说:“你去拿条毛巾来,这些东西都满是灰尘了,我得把它们都擦一擦……”
他把每一件东西都擦干净,放好后,就面朝墙钻进了被窝。外面下起了雨,雨水从屋檐上流下来,风吹打着窗户。
他背对着我说:“等着吧,园子一干,我就带你去看一样东西,你肯定会很吃惊的!”
我没理他,准备睡觉了。
没过一会儿,他突然跳起来,双手抓着墙,无比诚恳地说道:“我好害怕啊……主啊,天主啊!可怜可怜我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时吓呆了,一言不发。我好像看见厨娘在正对着院子的窗口那儿靠着,低着头,前额紧贴着玻璃,背对着我站着,像极了她活着的时候看公鸡打架时的样子。
萨沙号啕大哭,两只手不停地挠墙,两条腿不停地乱蹬。我吃力地挪动身子,然后像踩在火堆上似的头也不回地穿过厨房,走到他身边躺下了。
我俩一直哭,后来哭累了才睡着。
过了几天,正赶上一个节日,做了一上午生意,中午在家吃完饭后,趁老板一家人睡觉的时候,萨沙神神秘秘地对我说:“咱们走吧!”
我知道自己马上就能见到那件足以让我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我们来到园子里,在两幢房子中间的一片狭窄的土地上,长着十五六棵老椴树,粗壮的树干上长满了青苔,干巴巴的黑树枝毫无生机地在空中伸展着。树枝之间空空的,连一个乌鸦巢也没有,树干光秃秃的,活像墓园里的墓碑。除了这些,园子里什么都没有。小路的地面被踩得很硬实,像生铁一般黑黑的。在铺满去年腐叶的地面上,偶尔会露出一小块儿地面,那露出的地面像一摊死水中的浮萍,长满了霉。
萨沙拐过一个弯儿,来到街道旁边的围栏前,停在了一棵椴树下。他朝邻居那脏兮兮的窗户瞥了瞥,然后蹲下去双手扒开一堆落叶,一个粗大的树根露了出来,树根旁有两块儿埋在土里的砖。他挖出砖,下边是屋顶上用的破烂铁皮,铁皮下是一块儿方形板,最后是一个直通树根底的大洞。
萨沙划了一根火柴,点亮了一根蜡烛,然后将蜡烛探进洞里,对我说:“别害怕,你看……”
他自己倒先害怕起来了,他的手一直哆嗦,脸色发青,嘴巴不自然地张着,眼睛也湿乎乎的;他小心翼翼地把另一只手放到了背后。看到他这样,我也有些害怕了。我小心谨慎地沿树根向洞底望去,粗大的树根为洞搭了个顶。萨沙将三根点燃的蜡烛放在了洞底,那蓝色的光照亮了整个洞。洞很大,有木桶那么深,但比木桶要宽些。洞旁边堆满了彩色的小碎玻璃和茶具碎片。洞中心隆起一个高台,上面铺着一块红布,布上面是一口小棺材,棺材外面糊着一层锡纸。一块棺材罩似的布盖住了半个棺材,布下面露出了麻雀的两只小灰爪子和尖尖的喙。棺材后有一个灵台,灵台上放着一个铜质护身十字架。灵台四周点了三支长长的蜡烛,蜡烛插在用金色、银色糖果纸包裹的烛台上。
烛火向洞口处倾斜。洞里朦胧地闪烁着五彩的光点。蜡烛燃烧的烟气、洞里散发的湿热的霉腐气混着泥土气一齐扑到我的脸上,一道道的小彩虹弄得我眼花缭乱。看着这些,我心里不由得有种惊讶的感觉,这感觉甚至覆盖了我的恐惧。
“好玩儿吗?”萨沙问。
“这是什么啊?”
“小型的礼拜堂啊,怎么样,像吧?”
“我不知道。”
“可以把这小麻雀看成是死人,说不定它会变成不朽的金身呢,因为它的死很无辜……”
“你看到它时,它就已经死了吗?”
“不是,它飞进了货房,我用帽子扑死它的。”
“为什么要扑死它?”
“不为什么……”
他看了看我,又问道:“好不好玩儿?”
“不好玩儿!”
听到我的回答,他立刻弯下腰,盖上洞口的木板和铁皮,然后把砖块埋进土中。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泥土,厉声问道:“你为什么不喜欢?”
“我觉得那只小麻雀很可怜。”
他用那双黯淡无光的眼睛盯着我,然后在我胸口上推了一下,大声骂道:“浑蛋!你是心里嫉妒才说不喜欢。我不相信在缆索街你家院子里,你能做出比这更好的东西,你行吗?”
我想起家里的凉亭,便自信地回答:“当然,我做的比这个更好!”
萨沙气愤地将上衣脱下来往地上狠狠一扔,朝手心里唾了口唾沫,叫道:“既然这样,我们打一架吧!”
我不想打架,心里憋闷得慌,看着表哥那张愤怒的脸,我心里很不好受。
他猛地扑过来,一头撞到我的胸口,把我撞倒了,他骑在我身上吼道:“想活还是想死?”
我很气恼,但我力气比他大,没过多一会儿,我就制服了他,只见他双手抱头,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声音都变哑了。我吓坏了,赶忙扶他起来,可他却不依,两只胳膊乱挥着,腿胡乱蹬着,我更慌了,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他抬起头说:“怎么,算你赢了?我就躺在这儿,让老板的家人看看,然后告你一状,他们肯定会赶你走的!”
他骂我,还威胁我,我被激怒了,于是我跑到洞边,挖开砖块,把那只小麻雀从洞里扔到了围栏外,然后将洞中的东西全部拿出来扔到地上,用脚狠狠地踩碎了。
“看见了吗?”
看着我这残忍的行为,萨沙的表情很怪。他坐在地上,嘴稍稍张开,眉头紧锁,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我干完了,他才慢慢地起身,抖了抖身上的尘土,将衣服往肩上一搭,异常镇定而又恶狠狠地说:“你等着吧,用不了多久你就知道了!这东西都是我专门为你做的,这是魔法!你懂吗?”
我听后,猛地就蹲下了,似乎被他的话吓到了,我像是全身灌满了凉气。而他却头也不回地走了。是他那异常的镇定把我吓到了。
我下定决心明天就逃离这座城市,离开老板一家,躲开萨沙的魔法,从这种无聊又愚昧的生活中逃离出来。
第二天早晨,我被新来的厨娘叫醒了,她一看见我就叫道:“天哪,你的脸是怎么回事啊?”
“魔法起作用了!”我懊恼地想。
厨娘放声大笑,使我也不由得笑了,我拿过她的镜子一照,原来我脸上有一层厚厚的煤灰。
“这是萨沙干的吧?”
“难不成是我吗?”厨娘笑着说。
我正要擦皮鞋,手刚伸进鞋里,手指就被大头针扎了一下。
“又是魔法!”
原来每只鞋里都放了缝衣针和大头针,放得很隐蔽,很难被发现,这些大头针不偏不倚正好扎进了我的手指。于是我拿瓢舀了一瓢凉水,走到了这位魔法师面前,他还没醒,也或许在装睡,我十分解恨地浇了他一头凉水。
可感觉还是不痛快。脑海中老是浮现出那口装小麻雀的棺材,它的爪子弯曲着,暗淡无光的小尖嘴可怜地向上伸着,还有周围闪闪的彩色光点,快要形成彩虹了却没有形成。棺材在不断变大,小麻雀上伸着的爪子也越来越大,颤动着,它活了。
我心里计划着当天晚上就逃走。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午饭前在煤油炉上热汤时,我因为走了神,汤烧开了也不知道,接着又因为急忙关火,把汤锅打翻在自己手上,于是我被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那段噩梦般的日子至今仍存留在我的脑海里:一些身穿尸衣的白影子和灰影子在黄斑斑的空荡荡的地方来回游荡着,低声呻吟着。其中有个拄着拐杖的大高个男的,又粗又长的眉毛好像两撇髭须,他甩着大黑胡子,咆哮道:“我要到主教大人那儿去告状!”
那儿的病床像是一口口棺材,而躺在上面的,鼻孔朝上的病人就是那只死麻雀。黄色的墙壁在颤动着,天花板也凸了出来,像鼓起的船帆,地板松动着忽上忽下。并排着的病床嘎吱嘎吱的,一会儿合拢,一会儿分开,这里的一切都是活动的,可怕极了。不知什么人像摇晃打人用的皮鞭似的摇晃着窗外的树枝。
屋外有一个棕红色头发的死人,身材瘦小,挥动着两只小手,撕扯着自己的尸衣在跳舞,还不断地尖叫:“让这些疯子都远离我!”
这时那位拄着拐杖的大黑胡子嚷道:“我要到主教大人那儿去告状……”
小时候我从外祖父、外祖母和其他人口里得知:医院往往会把人折磨死。我顿时心灰意冷,心想我这条命肯定完蛋了。一个戴着眼镜、穿着尸衣的女人走过来,在我床头的小黑板上写了些东西,粉笔断了,粉末掉在我头上。
“你叫什么名字?”她问。
“什么也不叫。”
“你总有个称呼吧?”
“没有。”
“别胡闹,信不信我打你!”
就算她不说,我也知道自己会挨打,于是我干脆不理她。她像猫一样哼了一声,又像猫一样无声地离开了。
这里点了两盏灯,两束黄色的火苗挂在天花板下,像人的一双眼睛,眨呀眨的,没有神,似乎想要靠在一起。照得我眼花缭乱,烦躁得很。
屋角落里有个人说:“咱们打牌吧?”
“我就一只手怎么打啊?”
“哦,对,你的一只手被人锯掉了。”
我立刻想:他们锯掉了这个人的一只手,就因为他爱打牌,那他们会用什么方式把我折磨死呢?
我的手很痛,像着了火似的,那感觉像是有人在活生生地抽我手上的骨头。恐惧加上疼痛,使我忍不住轻声哭了起来。我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流泪,就闭上了眼,但泪水从眼角溢了出来,顺着太阳穴流到了耳朵里。
夜来了,所有人都躺在病床上,躲在灰色的被子里,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周围越来越安静。只听到墙角那儿有人嘟囔:“不会有好结果的,男的是废物,女的也是废物……”
趁我还没死,我想给外祖母写信,叫她赶快来偷偷把我从医院接走。可是我没有纸,手又写不了字。我想试试,能不能逃离这里呢?
夜晚更加安静了,让人觉得好像光明永远不会到来。我悄悄地下了床,走到门口,门半掩着。借助灯光,我看到在走廊里的一张带靠背的长木椅上,坐着一个灰色的、脑袋像刺猬一样的人,这人喷着烟,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睛盯着我,我已经来不及躲了。
“是谁在那儿?过来!”
这声音很轻,我并不感到害怕。我走了过去,这人圆圆的脸上长满了络腮胡子,又长又乱的头发竖立着,使他的头周围有一圈银色的光环。他的腰上挂着一串钥匙。如果他的头发和胡子再长一点,那就和彼得
 没什么区别了。
没什么区别了。
“你的手被烫伤了?你半夜出来溜达什么?有规定允许这样吗?”
他把烟喷到了我的脸和胸脯上,又伸出一条温暖的胳膊搂着我的脖子,把我拉到了他身边。
“你害怕吗?”
“害怕。”
“刚到这儿的人都害怕,但其实不用怕,尤其是和我在一起,我从不会让任何人觉得委屈……你想抽烟吗?噢,不抽,你还太小了,再过两三年吧……你的父母呢?都去世啦?哎,没有了也没事,没有父母我们照样能活下去。但你得胆大些,知道吗?”
我很长时间没有遇到这样好心的人了,他讲的话很朴实,很在理,很亲切,听他说这些话,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喜悦。
他送我回到病床上,我请求他:“你陪我坐会儿吧!”
“好。”他同意了。
“你是做什么的?”
“我?我是一个兵,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加索兵,我打过仗,可不打仗也不行啊,当兵的目的就是要打仗嘛。我打过切尔克斯人,打过匈牙利人,打过波兰人
 ,总之和许多人打过仗!小老弟啊,打仗真是一种无法收拾的大灾难啊。”
,总之和许多人打过仗!小老弟啊,打仗真是一种无法收拾的大灾难啊。”
我闭了会儿眼,等我再睁开眼时,发现外祖母穿着黑色的衣服,坐在那个兵坐过的位置,当兵的正站在她身旁说:“那些人全死了吗?”
阳光照进病房,把病房里的一切都染成了金色,它像一个在嬉闹的小孩儿,一会儿把自己藏了起来,一会儿又明晃晃地照亮所有物体。
外祖母弯下腰问我:“我的小心肝儿,怎么样,伤得严重吗?我已经和那个红胡子魔鬼说过了……”
“我现在就去办出院手续。”那个当兵的说完就走了。外祖母擦了擦眼泪说:“这个兵以前是我们那儿的,是巴拉罕纳人……”
我一直觉得我在做梦,不敢说话。医生进来为我换了烫伤部位的纱布。之后,外祖母便带我坐上一辆马车走了,走在城里的街道上,她说道:“咱家的那个老头子简直疯啦,吝啬透了,真令人厌烦!前两天,他的新朋友——一个毛皮匠,人送外号‘马鞭子’,把他夹在赞美诗里的一张一百卢布钞票偷走了。结果他和人家没完没了,唉!”
阳光很亮,一朵朵云像一只只白天鹅,在天空中飞翔,我们的马车沿着铺在伏尔加河冰面上的木板路向前走着,冰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正在不断扩张,哗啦哗啦的水流声从木板下传来。几个金黄的十字架,位于市场中大教堂的红色屋顶上,正发出耀眼的光芒。这时走来一个妇人,脸盘宽宽的,手捧一大把柔嫩的柳枝——春天到了,复活节快到了。
我的内心像云雀一样激动起来:“外祖母,我好爱你啊!”
听到我的话,她并没有多大反应,只是平静地说:“因为我们是亲人啊。不是我说大话,就连外人都很喜欢我,啊,感谢圣母!”
她微笑着继续说道:“圣母喜欢的那一天马上就要来临了,她的儿子就要复活了!可是我的女儿呢,我亲爱的瓦留莎
 呢……”
呢……”
说到这儿,她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