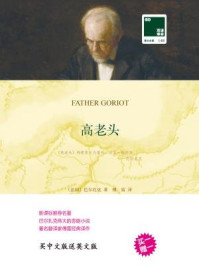1832年12月17日
在结束了巴塔哥尼亚的考察之后,我打算说一说初抵火地岛的情形。正午刚过,我们绕过圣地亚哥角,进入了著名的勒梅尔海峡。我们紧靠火地岛航行,然而埃斯塔多斯岛
 那怪石嶙峋、凶险的轮廓却在云雾中隐约可见。下午时分,我们在顺遂湾抛锚停泊。在驶入海湾时,我们便见到了这个蛮荒之地的典型居民。一群火地岛人停歇于突出在海里的尖岬上,身子半掩在枝蔓横生的密林里;当我们经过时,他们突然跳了出来,挥舞着破破烂烂的斗篷,向我们大声地喊叫。这些土著人追着船跑,刚到傍晚就见他们亮起了火把,接着又听见了他们狂野的呼喊声。港湾里的水相当澄澈,被一片低矮平缓的泥板岩山半围着,山上浓荫覆盖,幽林一直延伸到水边。只凭一瞥我就知道,眼前的风景与往日所见的其他景致截然不同。晚上刮起了一阵大风,从山顶刮来的风暴横扫过我们。这时候要还是在海上就糟糕透了,因此我们称这个给了我们庇护的港湾为“顺遂湾”。
那怪石嶙峋、凶险的轮廓却在云雾中隐约可见。下午时分,我们在顺遂湾抛锚停泊。在驶入海湾时,我们便见到了这个蛮荒之地的典型居民。一群火地岛人停歇于突出在海里的尖岬上,身子半掩在枝蔓横生的密林里;当我们经过时,他们突然跳了出来,挥舞着破破烂烂的斗篷,向我们大声地喊叫。这些土著人追着船跑,刚到傍晚就见他们亮起了火把,接着又听见了他们狂野的呼喊声。港湾里的水相当澄澈,被一片低矮平缓的泥板岩山半围着,山上浓荫覆盖,幽林一直延伸到水边。只凭一瞥我就知道,眼前的风景与往日所见的其他景致截然不同。晚上刮起了一阵大风,从山顶刮来的风暴横扫过我们。这时候要还是在海上就糟糕透了,因此我们称这个给了我们庇护的港湾为“顺遂湾”。
清晨,船长派出了一个小队与火地岛人沟通。当我们迎着他们的欢呼声向前时,四个土著人代表中的一个上前迎向我们,极为热烈地对着我们大吼大叫,想要引导我们从哪里登陆。我们上岸后,他们看起来十分警戒,然而还是一边喋喋不休,一边快速地比画着手势。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识过的最稀奇、最有趣的情景了。我无法相信野蛮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差距竟有这么大,它比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因为人的进化力要更强一些。领头说话的是一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族之长;另外三位则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约有6英尺高。妇人和孩子已经被送走了。这些火地岛人与更西边那些矮小、不幸的可怜人是完全不同的人种。他们在外貌上要出色得多,看起来更接近于麦哲伦海峡的巴塔哥尼亚人。他们唯一的衣服是一件原驼皮制成的披风,毛面朝外;他们就把披风挂在肩膀上,身子半遮挡半袒露着。他们的皮肤是乌沉沉的赤铜色。
老人头上缠着一圈白色羽毛的头带,略微拢住了他毛糙、纠结的黑发。他的脸上画着两道粗粗的横纹;一道鲜红色,从一只耳朵延伸到另一只耳朵,还覆盖了上嘴唇;另一道,像是白垩画的,在第一道的上方平行地展开,因此连眼睑也染成了白色。另外三个人中有两个的脸上装饰着木炭画的黑色粉状条纹。这几个人待在一起活像舞台上演出的魔鬼,诸如《魔弹射手》之类的。
他们的姿态卑微,脸上则带着狐疑、惊讶和恐惧的表情。我们赠送给他们几块红色的布匹,他们立刻就围在了脖子上,这才变得友好起来。这情谊是通过老人拍打我们的胸部来表达的,同时,他们还发出咯咯响的声音,就像人们在喂食小鸡。我和老人一道走路,这证明友谊的仪式重复了数次;最后以在我前胸后背同时重重地击打三下而告终。然后他向我袒露胸部,让我礼尚往来,待我做过这一套之后,他显得十分称心满意。这些人的语言,在我们听来根本不算是吐字。库克船长曾把它比作是一个人清嗓子发出的声音,然而毫无疑问,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在清嗓子时发出这么多粗糙、刺耳、咯咯作响的声音。
他们是极为出色的模仿者:每当我们咳嗽,或者打哈欠,或者做出什么古怪动作,他们立刻就照样学起来。我们这边的人开始挤眉弄眼;然而一个年轻的火地岛人(整张脸都涂黑了,只在眼睛这里横抹了一道白色的带状纹)成功地做出了一个更骇人的鬼脸。他们能分毫不差地重复我们对他们说的一字一句,还能把这些单词记上好一阵子。可是我们欧洲人都知道,要分辨一门外语中不同的发音有多难。比如说,我们中有哪一位,能跟读一句美洲印第安人超过三个单词的句子呢?未开化的人似乎都拥有这种非凡的模仿能力。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南非的卡非人有一模一样搞笑的模仿习惯;同样的,澳大利亚原住民很久以来都以擅于仿照、描绘别人的步态而闻名,并且以此来辨别外来者。这等天赋又该如何解释?这是否是由于与那些长期处于文明状态的人相比,所有那些未开化的人都有着更加熟练的洞察方式和更加灵敏的感官?
当我们这伙人唱起歌时,火地岛人惊讶得仿佛要跌坐在地。他们以同样惊诧的表情看着我们跳舞,不过有一个小伙子,在我们邀请他时,毫不抵触地跳了一小段华尔兹。虽然他们表面看起来并不适应欧洲文化,但他们还是知道并且害怕我们的火器;没有东西能诱惑他们用手去摸一把枪。他们十分渴求刀子,用西班牙语“库奇亚”来称呼这些刀子。他们还用动作来比画他们想要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嘴里叼着一块鲸脂,然后假装用刀去切,而不是用手撕扯。
观察这些人对待杰米·巴顿(一个火地岛人,在前一趟探险中被带到了英格兰)的举止十分有意思。他们立即意识到了杰米和我们的不同,并就此相互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老人对杰米发表了长篇大论,似乎想要邀请他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杰米只听得懂一丁点儿他们的语言,此外,也根本看不上他的同胞们。当约克·明斯特(另一个到过英格兰的火地岛人)来到岸上时,他们同样注意到了他,并告诉他应该刮胡子了;尽管他脸上并没有多少胡楂,而我们则全都胡子拉碴。他们仔细察看他的肤色,还拿他和我们的做比较。我们中有一位的胳膊露了出来,他们对白皙的肤色惊讶不已,十分艳羡。我们认为他们误把两三位身材更矮小、长相更俊俏的长官错认为我们这伙人里的女士了,尽管他们也留着大胡子。火地岛人当中最高的一位对于有人注意到他的身高显然颇为自得。当他与船上个子最高的那位背对背站着的时候,还极力站在高一点儿的地方,拼命踮着脚。他张开嘴显露他的牙齿,偏过头展示他的侧颜;他乐意之至地做着这些事,我敢说,他一定以为自己是火地岛最俊俏的男子。等我们最初的大惊小怪过去之后,这些原住民每时每刻表现出来的混杂着惊讶和模仿的反应则成为最为搞笑、最为有意思的事。
第二天,我试图深入探索这一地区。火地岛或许称得上是多山地区,它的一部分沉在了海里,因此原本是山谷的地方,就变成了水深不见底的小洲和海湾。除了西海岸寸草不生的山坡,其余山坡从与水面相接的地方开始便被茫茫林海所覆盖。树木生长到1000至1500英尺的高度;随后是一条泥煤带,分布着矮小的高山植物;再往上则是终年不化的积雪了,按照金船长的记录,麦哲伦海峡的雪线高度为3000到4000英尺。想要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哪怕是1英亩
 平整的地都稀罕至极。我只记得在饥荒港附近有一小块平地,另一块面积大得多的则位于戈里路德附近。这两块平地以及其他平地上,地面全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沼泽泥煤。即使在森林里,地面也密覆着大量缓慢腐化的植被,浸透了水,脚一踏上去就会往下陷。
平整的地都稀罕至极。我只记得在饥荒港附近有一小块平地,另一块面积大得多的则位于戈里路德附近。这两块平地以及其他平地上,地面全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沼泽泥煤。即使在森林里,地面也密覆着大量缓慢腐化的植被,浸透了水,脚一踏上去就会往下陷。
在密林中我几乎寸步难行,于是便改道,沿着一条山中径流探寻。起初,飞瀑横流,枯木倒地,简直举步维艰;不过水流冲刷两岸,溪床很快就变得宽一些了。我继续沿着崎岖、多石的岸边缓慢走了一个小时,壮丽的景色令我不虚此行。昏朦幽暗、深不见底的峡谷完美地呼应了无处不在的剧烈变动的痕迹。峡谷两侧尽是一些嶙峋的巨石和折断的树;而其余的树,虽然还直立着,但也已经从中间腐烂,随时可能倒下来。这种生机盎然的树和倒伏的枯树纠葛缠绕在一起的状态让我想起了热带雨林——然而还是有所不同,因为在这一片死寂的荒野之中,看起来是死亡主宰了一切,而非生机。我顺着水流的方向走,来到了一处地方,大滑坡给这里的山坡清出了一片直着向下的空地。沿着这条路,我攀登到相当高的地方,得以视角颇佳地一览周遭树林。这些树全都属于一个种类——桦状假水青冈木(Fagus betuloides),而其他种类的山毛榉和林仙树的数量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这种树的叶子终年不落,然而叶片的颜色呈一种颇为奇异的棕绿色,略微泛出一点儿黄色。由于这里的整个景观都是这个色调,便显得阴郁、沉闷,即使在阳光的映照下,也未见几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