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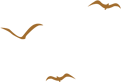
正德五年(1510年),王阳明离开贵州,到江西任庐陵县知县。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王阳明都是在事与思的重合交错中度过的。正是在这种交融中,王阳明对“第一等事”的思考进一步趋于成熟与系统化。
赴庐陵以前,王阳明虽然也多次在吏部、兵部任职,但地方的实际工作较少涉及。在庐陵任上,王阳明获得了展示其实际工作才干的机会。阳明赴任以前,庐陵的社会秩序较乱,案件堆积。王阳明到任后,并不一味依赖严刑峻法。他首先从清理各级政权机构入手,建立了保甲制度,谨慎地选择地方贤达(里正三老),使之劝谕本地。同时又整顿驿站,梳理捐税,杜绝各种管理漏洞。经过这一番整肃,县治面貌为之一变,本来狱案积压的庐陵,“由是囹圄日清”(《年谱一》,《全集》,1230页)。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对心体的作用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这种观念亦体现于其政治实践。庐陵期间,阳明“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同上)。他到任后不久,当地流行病疫,老百姓怕传染,往往骨肉之间也不相互照料,一旦患病,便无人送饭送药,常饥饿而死。王阳明目睹此状,甚感忧虑,即以告示劝谕全县父老:“夫乡邻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于骨肉不相顾。……中夜忧惶,思所以救疗之道,惟在诸父老劝告子弟,兴行孝弟,各念尔骨肉,毋忍背弃。”(《告谕庐陵父老子弟》,《全集》,1027页)其言辞之恳切,令人不能不为之所动。这里并没有诉诸抽象的理论说教,而更多地是以真情相感化,从中已依稀可以看出心体与超验天理的差异。
王阳明在庐陵的时间并不很长。正德五年八月,刘瑾伏诛,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机。同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刑部主事。翌年调至京师,任吏部主事。公事之余,常与友人、学生论学。当时,其弟子徐成之和王舆庵争论朱陆异同,王阳明致书徐成之,阐述了自己的看法。王舆庵认为陆象山专以尊德性为主,徐成之则认为朱晦庵专以道问学为事,王阳明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根据他的观点,陆象山固然重德性,但亦未尝忽视读书;朱晦庵讲道问学,但亦并非不重德性。总之,“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年谱一》,《全集》,1233页)。这里既肯定了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又表现出范围朱陆而进退之的思维趋向。
居京师期间,王阳明与湛若水的交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阳明已结识湛若水。当时阳明开始收弟子讲学,并以立志成圣为讲学宗旨,但却被时人目为标异好名,惟湛若水对此颇为赞赏,二人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相勉。后王阳明因抗疏直谏遭谪,赴谪前,湛若水曾以诗相赠,勉励他继续追求圣学:“愿言崇明德,浩浩同无涯。”(《九章赠别序》,《甘泉文集》卷二十六)自庐陵入京,王阳明与湛若水重逢,并与黄绾相识(黄绾后执弟子礼),三人遂定为至交,“订与终日共学”。在学术上,阳明与湛若水并不完全相同。湛若水为学主随处体认天理,王阳明则自龙场始,便侧重理与心的统一,但这并不妨碍二者在学问上的相互切磋。当湛若水在正德六年出使安南时,王阳明颇为之怅然,特为文相赠。文中写道:“夫惟圣人之学,难明而易惑,习俗之降愈下而抑不可回,任重道远。”(《年谱一》,《全集》,1234页)这既是对湛若水的厚望,也是一种自勉,而其中又蕴含着拒斥流俗(世儒之学),重建和光大圣学之意。
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此时阳明已多年未回越地老家,遂决定顺道回越探亲。恰好其妹婿徐爱亦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于是两人便于翌年初同舟归越。早在正德二年,王阳明赴谪之前,徐爱已执弟子礼,此次同行,又使徐爱获得了问学的机会。在舟中,王阳明着重向徐爱阐发了《大学》宗旨,内容涉及心与理、知与行、心与物等关系,从中已可看到其心学体系的某些基本思想。徐爱“闻之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年谱一》,《全集》,1235页)。归越后,又与徐爱同游四明山,在山林之中继续心学的讨论。事后,徐爱将王阳明的论学内容记录下来,编入《传习录》卷首。
赴南都前,王阳明先至滁州督马政。这是一个闲职,有较多的时间可以从事论学。滁州虽然地方偏僻,但风景秀丽,环境清静,是读书讲学的好去处。居京师期间,王阳明的弟子便已日增,有的虽地位在阳明之上,但闻阳明之学后,深为感佩,乃师事之,如吏部郎中方献夫。至王阳明离开京师前,受业门生已差不多有二十来人。王阳明到滁州后,门生又渐集,日遨游于山水间,在秀峰清泉中相与讨论“第一等事”。有时数百人在月夜环龙潭而坐,“歌声振山谷”,其情景蔚为壮观。学生常当场提出问题,王阳明则随时加以阐释,弟子开悟之后,往往踊跃歌舞,师生间的问答显得十分生动。龙场之后,阳明曾一度让弟子静坐,以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滁州期间,王阳明虽仍提静坐,但同时强调静坐并非禁绝思虑。其弟子孟源曾就“静坐中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请教王阳明,王阳明回答到:“纷杂思虑,亦强禁绝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精专无纷杂之念。”(同上书,1236页)这里已注意到把静与佛家的坐禅入定区别开来,以避免由静流于虚寂。
滁州讲学历时约半年。正德九年,王阳明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当王阳明离滁州时,门生弟子依依难舍,一直送至江边,仍不愿离去,表现了至深的师生情感。王阳明到南京后,周围很快又汇集了众多的门生。师生共聚一处,相与辨析义理,几乎每日都不间断。王阳明在滁州时已隐隐感到过分执著于静,有流于虚寂之虞,这种趋向后来在滁州游学的弟子中确实有所显露。他们立志固高,但实地工夫却较少,有时不免放言阔论,标立新奇,甚而背离阳明所教。这种现象使王阳明感到忧虑:“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同上书,1237页)高明一路,主要侧重悟见本体,仅仅明见本体,则很容易导向疏放。有鉴于此,王阳明在南京较多地强调做“省察克治实功”。对论学和教法的这一类反省总结,也促使王阳明更深入地思考本体与工夫的关系,并逐渐形成本体与工夫统一的论学宗旨。
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阳明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当时江西民变屡屡发生,并渐渐流而为寇,王阳明此行的使命便是平定以上各地的变乱。相对而言,王阳明以往所任大都为闲职,巡抚江西所担负的则是一种军政重任。面对新的任命,王阳明的心境颇为复杂。就“第一等事”(成圣)的追求而言,事功无疑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而过分突出高明一路所导致的偏向,也使实地用力这一面显得更为不可或缺。从这方面看,江西事功似乎可以成为王阳明南京时期注重实功的逻辑延续。然而,此时王阳明早已人到中年,多病之躯,使他常有未老先衰之感;祖母岑夫人年已九十六,作为孙辈,阳明亦时时感到有侍奉之责;同时,尽管王阳明年轻时一度溺于骑射,并曾研习兵法,但毕竟缺乏统兵征战的军旅经历,骤然独任征讨军务,其压力不难想见。正是在这种种的内在紧张中,王阳明开始了南赣之行。
南赣等地的武装变乱为时已甚久,起事者以山势险峻之处为依托,利用诸省交界的特殊环境,出入随意,进退自如。对这样的武装,重兵难以施展,兵力不足又无法奏效,因而明廷对他们一直苦无良策。初到南赣,王阳明首先从整顿地方政权入手,推行十家牌法,断绝平民与民变武装之间的交往;同时挑选精壮骁勇者组成民兵,以配合正规部队;在地方安定之后,才出兵征讨。根据对象的不同,王阳明或正面进军,或间道出奇兵,连战连捷。军事征战之外,又辅之以招抚。通过地方工作与军事行动并举、战与抚双行、强攻与奇袭交用,王阳明先后平定了漳州、大帽山、横水、桶冈等处的民变,前后仅历时一年余。
巡抚南赣的实践,使王阳明进一步意识到“心”上工夫的重要。在征剿过程中,王阳明时时注意对反叛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平漳州后,乐昌、龙川等地尚待征讨,用兵前,王阳明即先告谕对方:“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年谱一》,《全集》,1244页)语词间,颇有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恳切。这种以情感人的劝谕,往往有军事征剿无法取代的效果,武装首领卢珂等经晓谕,“即率众来投,愿死以报”(《年谱一》,《全集》,1245页)。
进兵前的劝谕,当然还只是一种权宜之策。要达到长治久安,便必须从事更基础的教化工作。一俟战事稍定,王阳明便发出文告,要求各县父老子弟,互相诫勉,共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礼。时间长了,地方风俗为之而变,朝夕歌声,不绝于街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王阳明特别注重儿童的教育,肯定一方面要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引导儿童,但又强调不能以生硬强制的方式对待儿童,而应适合其特点,循循善诱:“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同上书,1252页)这里已注意到道德教育中应贯彻自觉与自愿相统一的原则。
王阳明统兵征战期间,门人数十,依然聚集在一起,相与论学。回军休士之际,王阳明将注重点又转向了弟子,在军营中探讨心性之学。当时讲论的中心是《大学》,其旨在指示入道之方。早在龙场期间,王阳明已怀疑朱熹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后辑录《大学》古本,反复研读深思,逐渐悟到《大学》之旨本来简易明白,《大学》一书也无经传之分,格物致知本于诚意,无需再补一传。至此,王阳明正式公开刻印古本《大学》。宋明时期,《大学》这一儒家经典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而朱熹的《大学章句》则几乎成为标准读本。王阳明心学体系的形成,与《大学》的重新诠释自始有着内在的理论联系。在经典具有权威意义的时代,论学立说往往需要借重经典的权威,王阳明既在朱学之外另辟新径,便自然需要获得另一权威范本的依据。
与《大学》古本付梓几乎同时,王阳明又刻印了《朱子晚年定论》。此书是王阳明在南京时期所编定,其策略似乎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亦即以朱熹的所谓晚年之论否定其所谓中年未定之说,并以此论证阳明自己所立新说与朱熹并无冲突。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王阳明写道:“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同上书,1254页)依此理解,似乎便有了两个朱子:晚年朱子与中年朱子。事实上,所谓晚年朱子在很大程度上是经过王阳明改铸过的朱熹,《朱子晚年定论》这一选本尽管都是朱熹的原话,但这些“原文”却是王阳明依据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加以选择的,它已多方面地渗入了王阳明的先见。
也许是出于巧合,在王阳明刻印《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之时,门生薛侃印行了王阳明的《传习录》。这似乎是对王阳明的一种呼应,它使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以正面的形式得到了展现。此书虽只收入了王阳明部分讲学记录(即今本《传习录》上卷),但从中已可看到王阳明体系的大致轮廓,它的刊行,无疑扩大了阳明思想的影响。随着论学声名的远播,四方前来问学者日众,原来的营地已无法容纳,于是王阳明特意修建濂溪书院,作为讲学之所。军中论学的这种盛况,确乎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事(事功)与思(心学)的融合。
正德十四年(1519年),福建发生兵变,王阳明奉命前往勘查。行至中途,得知宁王朱宸濠叛乱。宁王受封南昌,久怀野心,后见其异志为明廷所知,遂以得太后密旨“起兵监国”为名,举兵叛乱。王阳明闻变,立即决定返回。当时形势颇为危急,宁王拥兵六万,号称十万,连克南康、九江,兵锋直指南京。王阳明先以计疑惑宁王,使之迟疑不敢妄动,随后星夜兼程,赶到吉安。时宁王势盛,人心浮动,但王阳明却慨然应难,略无彷徨之意:“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这种从容态度,既表现了政治上的信念,也体现了一种人生境界。
是时宁王率军围困安庆,众将大都主张引兵前往救援,王阳明独认为应先攻宁王之巢南昌,使之失去内据,不得不回救,如此则安庆之围自解,而宁藩可成擒。遂统兵直逼南昌,宁王果然回师。王阳明先攻克南昌,然后挥师迎战宁王于鄱阳湖。接战前,部将多以宁藩兵势强盛,宜坚壁不出,徐图进退。王阳明则对形势作了不同的分析,认为宁藩虽强,但此时进无所得,退无所据,军心已动,若驱兵进击,必不战自溃,“所谓先入有夺人之气也”。后来战况的发展,一如王阳明所料;数战之后,即生擒宁王朱宸濠。一场震动朝野的叛乱,至此为王阳明所平息。
平定宁藩之乱,无疑使王阳明事功生涯达到了巅峰,但这种不世奇功最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相反,却给他带来了种种磨难。宁王叛乱的消息传到京师后,兵部本拟任命将领率军征讨,但武宗却将此视为南巡的机会,遂假威武大将军镇国公之号,统兵亲征。南下途中,王阳明的捷报已到,但武宗却以“元恶虽擒,逆党未尽”为由,继续南进。王阳明闻讯,上疏谏止,武宗未加理会。王阳明遂决定北上献俘,不料随武宗亲征的内官张忠、许泰等竟荒唐地拟追还朱宸濠,然后放回鄱阳湖,让武宗与之亲战,以图立功。王阳明拒绝了这种近乎儿戏的要求,星夜赶到杭州钱塘,将宸濠移交较明大义的内官张永,自己避居西湖净慈寺,称病不出。后武宗下诏命王阳明兼巡抚江西,于是返赣。
内官张忠、许泰到南昌后,终日四处搜罗,骚扰地方。王阳明回南昌后,由张、许统领的北军常常有意挑起事端,动辄肆意漫骂,矛头直指王阳明。王阳明不为所动,且处处待之以理,并告谕市民尽可能避免与北军冲突。时间一长,北军对王阳明内心渐服,而久居南方,也使他们日夜思归。张、许颇忧,遂邀王阳明在校场比箭,以为骑射是其所长,王阳明必处下风。其实王阳明少时即精于此道,结果三发皆中,且每中一箭,北军即为之欢呼。张、许见北军已心向王阳明,不得不班师北还。
张、许离南昌,并不意味着对王阳明的政治陷害就此了结。张、许到南京后,即向武宗诬告王阳明必反,并以若召之,阳明必不至为据。武宗果下诏令王阳明朝见,阳明应诏前行。张、许恐其所说不验,遂将王阳明阻在芜湖,使之无法入见武宗。王阳明无奈,只得上九华山,每日默坐草庵之中。此时王阳明无疑颇有感慨。宁王之乱,固然一战而定,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无尽的劫难。小人当道,功臣遭忌,是非如此颠倒,令人不能不萌生归意。从这一时期的诗文中,我们不难看到这种心境:“百战归来一身病,可看时事更愁人。道人莫问行藏计,已买桃花洞里春。”(《宿清寺四首》,《全集》,755页)“嘉园名待隐,专待主人归。此日真归隐,名园竟不违。岩花如共语,山石故相依。朝市都忘却,无劳更掩扉。”(《杨邃庵待隐园次韵五首》,《全集》,758页)如此郁郁隐居于山中,直到最后奉诏再返江西。
南赣既定,叛乱又平,繁重的军务告一段落,王阳明似乎暂时得到了解脱。然而,武宗羁留南京,耽于巡游之乐;自己则身遭毁谤诬陷,这种政治现实与个人遭遇,又使王阳明感到心情沉重。忧患之余,对山林的向往又渐渐抬头。于是,利用职事之暇,王阳明来到庐山,游历了天池、东林寺、开元寺、白鹿洞等处。置身山林之中,回首往事,王阳明不觉感慨系之:“一年今又去,独客尚无归。人世伤多难,亲庭叹久违。壮心都欲尽,衰病特相依。旅馆聊随俗,桃符换早扉。”(《除夕伍汝真用待隐园韵即席次答五首》,《全集》,760页)年华逝去,归期难定,空怀壮心,一生多难。不测的世间风云,与青山绿水中的宁静,似乎形成了一种对照,而在久涉世间尘土之后,山林的幽清也有了特别的吸引力:“东风漠漠水沄沄,花柳沿村春事殷。泊久渔樵来作市,心闲麋鹿渐同群。自怜失脚趋尘土,长恐归期负海云。”(《繁昌道中阻风二首》,《全集》,766页)然而,在希望回归林下的同时,王阳明又难以真正忘怀世事:“我心惟愿兵甲解,天意岂必斯民穷!”(《三日风》,《全集》,762页)一段时期的军旅征战,使王阳明深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解兵甲的心愿,无疑表现了对民间疾苦的关切。一面是“终当遁名山,炼药洗凡骨”的愿望,一面则是“小臣谩有澄清志,安得扶摇万里风”(《元日雾》,《全集》,762页)的志向,庐山的秀峰奇景,并没有使王阳明的矛盾心绪得到排遣。
艰险的处境与矛盾的心境,也促使王阳明对其心学作进一步的沉思。自龙场之后,平定宁藩之乱及尔后的种种危机无疑是王阳明所经历的最大变故。宁王发难之时,朝有内应,外拥强兵,鹿死谁手,尚难逆料,故人怀观望之心。当此之时,王阳明几乎只身返赣,毅然首举讨逆旗帜,以临时凑集的地方弱旅,抗衡宁藩大军,并一战定乾坤,确实表现出他的大智大勇。时人曾评曰:“平藩事,不难于成功,而难于倡义。”(《年谱二》,《全集》,1275页)平定叛乱后,许泰、张忠辈以天子近臣之位,谗言毁谤,处处设陷,置王阳明于前所未有的险恶之境。钱德洪说,“平藩事不难于倡义,而难于处忠、泰之变”(同上),多少反映了这种非常之境。正如遭谪时期的居夷处困引发了龙场悟道一样,平藩前后的百死千难,也促发了他对“第一等事”更深入的体悟,而这种“悟”的结果,便是致良知之教的提出。
在这一时期致弟子邹守益的信中,王阳明写道:“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同上书,1278~1279页)这里他已明确以致良知为教,并将它视为其心学的主脑(如舟之舵)。当然,良知与致良知之说的基本思想并非一夜之间形成于此时,它事实上已经过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早在龙场时期,其某些方面已具体而微;正德八年与徐爱同舟归越时,进而以知为心之本体;正德九年在滁州讲学时,更以良知说为讲学内容;后到南赣,亦“终日论此”。(参见《与陆原静》,《全集》,189页)因之,把致良知说仅仅视为宁藩之变后的产物,并不确切。不过,正是在这一时期,王阳明开始更自觉地以致良知来概括其心学思想,而这种概括同时带有某种总结的意味:它既包含着以往沉思的丰富内容,又是对其体系的一种新的提升。从王阳明自己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年谱二》,《全集》,1279页)“一口说尽”表明了致良知的总结性质,“百死千难”则意味着这种学说既凝结了其人生体验,又是其长期创造性思考的升华。
正德十六年(1521年)六月,武宗病逝,世宗继位,王阳明的政治生涯似乎又出现了一次转机。世宗登基不久,即下诏命王阳明赴京任用,但旋即又为辅臣所阻。王阳明一度对新天子颇怀有希望,以为“圣天子新政英明”,但事实却表明这似乎只是一厢情愿的期望。此时,王阳明因征战在外,已多年未回家归省,思亲之念一直未断,政治上的不得志,也使其归志渐坚。于是,在赴京被阻后,王阳明便再次上疏请求归省。明廷很快批准了其申请,并给了他一个南京兵部尚书的闲职。不久,王阳明便踏上归途,开始其人生旅途中另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