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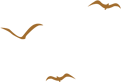
1505年,王阳明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生洗礼。这一年,明孝宗去世,明武宗登基。其时武宗年仅十五岁,朝政控制在内官刘瑾之手。内官专权导致了朝政的昏暗,这种状况自然引起了朝臣的不满,于是而有刘健等联名上疏,要求罢免刘瑾,但结果是刘瑾地位安然未动,刘健却被革职。南京户部给事中戴铣等上疏力主重新起用刘健,亦以“忤旨”的罪名被解京下狱。王阳明时为兵部主事,深知当时内臣弄权的政治形势,也十分清楚一旦触犯刘瑾辈将会导致何种结果,但仍毅然不顾个人安危,抗疏直谏,要求“宥言官”。尽管此疏在内容上只涉及戴铣等人之狱,但其锋芒却同时针对制造冤狱的权臣,因而自然难为刘瑾所容。疏一递入,即被刘瑾矫诏廷杖四十,随即下狱。
在狱中,王阳明的心境颇为复杂。权臣当道,政治昏暗,这种现状无疑使他感到忧愤和失望,从王阳明狱中所作的诗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天涯岁暮冰霜结,永巷人稀罔象游。”(《天涯》,《全集》,675页)险恶的政治环境有如严冬,高压下的万马齐喑则给人以永巷人稀之感。身陷囹圄,前景难卜,也使人不免向往起远离政治漩涡的田园生活:“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不寐》,《全集》,674页)“幽哉阳明麓,可以忘吾老。”(《读易》,《全集》,675页)此外,酷烈的廷杖与狱中生活亦使王阳明多病之躯更为虚弱,孤寂衰病之中,也平添了几分对家人的思念:“思家有泪仍多病。”(《天涯》,《全集》,675页)不过,王阳明并未由此而完全消沉。立志成圣的信念,激励着他在逆境中依然不忘却对道的追求:“孔训之服膺兮,恶讦以为直。”(《咎言》,《全集》,662页)在狱中的日子里,王阳明曾静心研究《周易》,并写下了《读易》一诗;也曾和狱中难友相与讲诵,以求道为乐:“累累囹圄间,讲诵未能辍。桎梏敢忘罪?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全集》,676页)这已多少展示了一种哲人的胸襟。出狱时,阳明以诗赠狱中诸友,再次表达了不为世俗所移之志:“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同上)这既是对狱中诸友的勉励,也是一种自勉。
出狱并不意味着磨难的结束,等待王阳明的是更为漫长的炼狱——远谪龙场。临行前,湛若水咏诗九首为他送行,王阳明作八咏以答之,其中有:“洙泗流浸微,伊洛仅如线。后来三四公,瑕瑜未相掩。嗟余不量力,跛蹩期致远。屡兴还屡仆,惴息几不免。道逢同心人,秉节倡予敢。力争毫厘间,万里或可勉。”(《八咏·其三》,《全集》,678页)诗虽不长,但却包含了对儒学道统的简要回顾:从孔子到周程,道已渐微;周程虽上接孔孟,但其学未能得到光大(“仅如线”);此后数子,已瑕瑜互见。为延续洙泗之道,阳明自己曾曲折探索(“屡兴还屡仆”),而在以后的漫漫长途中,将继续从毫厘入手,以实现万里之志。这里没有对个人命运的悲观,它更多地展示了以绵延道统为己任的抱负。
从京师到贵州龙场,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历程艰险。其艰其险并非仅仅在于沿途山高水长,而且更来自内臣刘瑾的追杀。王阳明被谪贵州后,刘瑾并未就此罢休。他将王阳明等人列为奸党,并遣心腹尾随王阳明,伺机刺杀。至浙江钱塘,为摆脱刺客,王阳明不得已“托言投江”,然后乘船入海。本拟到舟山暂避,但遇风漂至福建,于是潜入武夷山。经过这一番变故,王阳明对内官翦除异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凶险心态有了更真切的了解,而世间的这种种叵测风云,也令他不免有几分心冷,于是一度拟远遁他方。但基于人伦的强烈责任感,很快使他打消了远走之念,并决意不顾个人安危,继续赴谪。在这一期间所作诗中,王阳明写道:“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泛海》,《全集》,684页)“肩舆飞度万峰云,回首沧波月下闻。”(《武夷次壁间韵》,《全集》,684页)它所表现的,已是一种不以险夷为念的超然气度。
经过艰难跋涉,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春抵达龙场,其职务为龙场驿丞。龙场位于贵阳西北的修文县,周围是万山丛棘,十分偏僻闭塞,常有毒蛇走兽出没其间。龙场驿的规模相当小,全部编制只是“驿丞一名,吏一名”,外加“马二十三匹,铺陈二十三副”。王阳明初到龙场,无可居的住房,只好先自己动手盖草庵暂居,虽然草庐高不过肩,但远行疲乏的王阳明已对此感到满足:“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全集》,694页)后又迁到东部山峰,以石穴为室,周围多是动物世界:“鹿豕且同游。”(同上)由于瘴疠弥漫,同行随从都先后卧病,王阳明不仅只能自己做饭,而且不得不歌诗调曲以慰从者。龙场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处,王阳明与他们彼此语言难通,能以语言交流的,只有从内地亡命到此的各类人物。生活环境之困苦,由此不难想见。
不过,虽处困厄之中,但一时远离政治上的是非之地,外在的纷扰倒相对少了,这使王阳明有机会更集中地静心思考多年探索的问题。自遭刘瑾迫害以来,他时常面临如何对待个人荣辱得失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反省,王阳明自己觉得已能超脱得失荣辱的计较,心境较以往更为坦荡洒落。然而,尚有生死一念,未能放下。于是,继续端坐默思,以求贯通。如此反复省思,又回到了成圣这一终极性的问题:“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年谱一》,《全集》,1228页)最后终于豁然有悟。《年谱》对此作了如下描述:“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同上)这一彻悟过程,也就是所谓“龙场悟道”。
《年谱》的记载,不免有过度渲染之处,中夜大悟云云,也多少给人以几分玄秘之感。相形之下,王阳明本人后来的追忆,便显得更为平实真切:“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然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六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之海也。”(《朱子晚年定论序》,《全集》,240页)从中不难看到,王阳明经历了龙场悟道,这确是事实,不过,这并不完全是一种突如其来的神秘顿悟,而是一个长期沉思与瞬间突破交互作用的过程。人的一生中,其认识与境界往往会经历阶段性的跃迁,而困境中的反省,则可成为实现飞跃的触媒。赴龙场以前,王阳明对“第一等事”已上下求索了十余年,龙场的特定境遇,一方面使他有机会对已往的思考作一总结,另一方面也促使他在超越生死之念时,对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作出更深刻的体认。这里既有理智层面的认识飞跃,又有境界意义上的精神升华。
龙场之悟,王阳明究竟悟到了什么?从直接的内容看,不外是对格物致知说的重新理解,而其深层的内涵则似乎更为复杂。如前所述,王阳明曾按朱熹之说,格竹之理;后又依其教,循序致精,但总是面临着物理吾心判而为二的问题。正是心与理的分离,使他在朱学之外广涉各家,出入佛老。尽管立志成圣的讲学宗旨,使他又回归了儒家的道统,但心与理如何适当定位的问题并未解决,而这一问题又始终关联着如何成圣。龙场期间,如何成圣依然是王阳明关心的“第一等事”,当他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时,便已表明了这一点,而化解生死之念,同样旨在通向圣人之境。在历经“百死千难”之后,王阳明终于悟到:“圣人之道,吾心自足。”用更形而上的语言来说,理并不在心外:心即理。于是,圣人之道不再超乎个体存在,成圣获得了内在的根据。如后文将要详论的,相对于朱学,这确乎可以看作是一种哲学的转换。
终极思索上的突破,也使王阳明达到了一种新的人生境界。他不仅自身超乎了荣辱得失的考虑,不为生死之念所动,而且以其坦荡磊落的胸怀影响和感染着当地土著,并逐渐与之建立了一种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关系。见王阳明居所较为潮湿,当地夷人主动为他盖了新的住房,这些新居王阳明后来分别名之为“何陋轩”、“君子亭”、“玩易窝”等。贵州都御史王质曾遣人到龙场,来人对王阳明倨傲不恭,周围夷人知道后,竟为阳明抱不平而驱打差人,由此亦可见当地土著对王阳明的敬重。当然,这也惹怒了州守,有人劝王阳明向当局谢罪,王阳明严词拒绝,回答说:“吾岂以是而动吾心哉!”这既蕴含了王阳明对夷人正义之举的某种肯定,也表现了阳明吾心自足的自信。
王阳明在京师时,已开始收徒讲学;龙场悟道后,更有了一种传道的责任感。于是,以夷人所建新庐为舍,王阳明创办了一个书院,取名龙冈书院。这是王阳明所建的第一所书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边鄙之地,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王阳明在讲学之余所作诗中,已有“门生颇群集”(《诸生来》,《全集》,697页)的描述,可见当时问学者已不少。有的学生为请教一个问题,甚至跋涉百里,仅宿三夜便辞别。为使书院规范化,王阳明还制定类似院规的“教条”,其内容为:“一曰立志,二曰劝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教条示龙场诸生》,《全集》,974页)这也可以看作是京师期间立志成圣的讲学宗旨的具体化。在和诸生讲诵论析之余,还常相与漫步于山林之间,或观月于溪边:“夜弄溪上月,晓陟林间丘。”(《诸生夜坐》,《全集》,699页)当年孔夫子令弟子各言其志,曾点以“浴乎沂,风乎舞雩”作答,夫子叹曰:“吾与点也!”龙场讲学的此情此景,有时竟也使阳明与千年前的夫子产生了共鸣:“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诸生夜坐》,《全集》,699页)显然,这是一种基于乐道的精神沟通。
龙冈书院的讲学,使王阳明的才识逐渐为人所知。先是贵州按察副使兼提学副使毛科邀请他前去讲学,王阳明以“移居正拟投医肆”推辞。后席书在贵州提督学政,特向王阳明请教朱陆异同。王阳明不直接与席书讨论朱陆哲学,而着重谈了他在悟道之后对心物知行关系的重新理解,席书不以为然,“怀疑而去”。次日又来,继续讨论知行之辩,王阳明以五经论证自己关于知行本体的论点,席书的怀疑态度稍有改变。如此往返四次,席书终于“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年谱一》,《全集》,1229页)王阳明不辩朱陆异同而说知行本体,意味着他已无意仅仅纠缠历史公案,而更多地致力于标举新说。接受一种新的学说往往需要转换原有视域,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过程,因此,王阳明的知行学说在当时颇受问难,亦在情理之中。后来王阳明曾回忆道:“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同上书,1230页)然而,这种新的学说自身也有其内在的理论力量,席书之最后接受其看法,即表明了这一点。
这一时期,王阳明虽然尚未以良知与致良知概括其学说,但良知说的一些基本思想已具体而微。王阳明在悟道之后,曾以五经证其说,而这种“证”同时也是阳明以自己的先见重新解释经典的过程。在作于此时的《五经臆说》中,王阳明一再强调心体本明:“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同上书,980页)而这种心体又与作为第一原理的元为一:“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同上书,976页)对心体的注重,尔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和系统化。当席书经过阳明启示,悟到“求之吾性本自明”时,显然亦受到了王阳明以上看法的影响。王阳明晚年曾回顾道:“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传习录拾遗》,《全集》,1170页)这种总结确有道理。
当然,讲习立说并不是谪居生活的全部内容。身处边鄙,远离故土,常常会有一种深深的乡思。在这一时期所作的诗中,王阳明一再流露出这种情怀:“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远客日怜风土异,空山惟见瘴云浮。”“游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浮云塞长空,颓阳不可回。南归断舟楫,北望多风埃。”(《居夷诗》,《全集》,693、696页)与家人的长期隔绝,有时亦使人产生家书抵万金之感,并时时盼望远方的来信:“尺素屡题还屡掷,衡南那有雁飞回?”(同上书,694页)虽然“讲习性所乐”,在与诸生的论析中可以得到一种理智的满足,但理智的愉悦并不能消解情感的需要。闲时漫步前庭,抬眼远望长空行云,顿有此身漂泊、有如浮云之慨;行云尚有时而定,游子却归期遥遥:“山石犹有理,山木犹有枝。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愁来步前庭,仰视行云驰。行云随长风,飘飘去何之?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同上书,698页)与之相近的怀乡诗还有:“惟营垂白念,旦夕怀归图。”“思亲独疚心,疾忧庸自遣。”“岁宴乡思切,客久亲旧疏。”“山泉岂无适?离人怀故境。安得驾云鸿,高飞越南景。”“绝域烟花怜我远,今宵风月好谁谈?”(同上书,697~710页)如此等等。这一类游子之叹,在王阳明的《居夷诗》中几乎随处可见。诗言志,亦见情,从这些乡愁流溢的诗文中,我们既可想见王阳明当年的心境,也可感受到其丰富的情感世界,后者使阳明不同于难露真情的道学家。
谪居边地固然使人思愁难断,但龙场生活也使王阳明获得了难得的自由:“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同上书,702页)龙场虽然文化落后,倒也山清水秀。也许是早年受祖父王伦的熏陶,王阳明素爱山林泉石,遇到佳景,常流连忘返:“平生泉石好,所遇成淹留。”(同上书,698页)读书讲习之余,王阳明往往闲步于山间小径,或观深谷幽草,听林中鸟语;或驻足溪畔,俯视游鱼。每览胜景,常赋诗以记:“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同上书,704页)数年前,王阳明曾游历九华山,那里的奇山险峰使他常难以忘怀,而边地的风光与之相比毫不逊色:“溪深几曲云藏峡,树老千年雪作花。白鸟去边回驿路,青崖缺处见人家。遍行奇胜才经此,江上无劳羡九华。”(同上书,705页)冬日雪景如此,春风中的高岩青壁更令人陶醉:“林下春晴风渐和,高岩残雪已无多。游丝冉冉花枝静,青璧迢迢白鸟过。”(同上书,704页)身处此山此水,每每让人平添几分飘逸,阳明有时竟也“倦枕竹下石,醒望松间月”(同上书,698页)。这已颇有一些陶渊明的风度了。
不过,王阳明毕竟没有忘情于山水。自然的怀抱诚然使人领悟到“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同上书,700页);驿丞这种卑位闲职也似乎形同隐居,但求道与行道之志并未由此而淡忘:“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居夷诗》,《全集》,702页)即使置身林下溪边,也常常会有吾道何成的忧思:“溪水清见底,照我白发生。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同上书,697页)时光易逝,年华如水,此时王阳明已年近不惑,人生的波折,使他华发早生。尽管对“第一等事”的沉思已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但如何将其化为一种普遍的信念,依然是一个尚待努力的问题。也正是基于这种忧思,王阳明一再勉励弟子和友人,以求道秉道为贵:“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同上书,700页)“所贵明哲士,秉道非苟全。”(同上书,701页)阳明终究非渊明,渊明可以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终其一生,阳明却始终难以忘怀经世行道的理想:“寄语峰头双白鹤,野夫终不久龙场。”(同上书,703页)随着谪徙生涯的终结,王阳明确实不久便告别了龙场,在事(经世事功)与思(哲学沉思)的交融中开始了新的求道与行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