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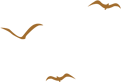
自南昌返归余姚后,王阳明开始了对“第一等事”多向度的沉思。这一时期,阳明极为勤勉,日间与诸生相与论析经义并准备举业,夜晚则广读经史子集,常持续到深夜。苦读如此,当然绝非仅仅为了科举的成功,这一点,其同学诸生亦已经有所意识:“彼(阳明)已游心于举业外矣,吾何及也!”(《年谱一》,《全集》,1223页)他们看到了阳明之志已超乎举业,但并不十分清楚阳明究竟游心于何方。事实上,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王阳明的真正兴趣所在,乃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第一等事”)。
王阳明谒见娄谅时,娄谅曾向他提及“宋儒格物之学”。这使他对宋学,尤其是朱熹的理学发生了兴趣。在一段时间中,阳明曾“遍求考亭遗书读之”,对朱熹的哲学颇下了一番工夫。朱熹以为一草一木,兼含至理,格物要以天下之物为对象。根据朱熹的格物之说,王阳明曾与一位钱姓的朋友一起,面对亭前之竹以格其中之理。钱氏早晚默坐,竭其心思,到第三天,便劳神成疾。王阳明开始还以为他这位朋友精力不足,但自己坚持了七天,也终于因耗神过度而病倒了。对朱熹格物方法的身体力行,不仅没有使王阳明得到任何收获,反而以致疾告终,这种结果不能不使阳明对朱熹哲学产生某种怀疑。从理论上看,青年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如上理解是否准确,固然颇有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种理解中,已蕴含着尔后阳明与朱熹分歧的契机。
不过,格亭前之竹的失败,固然使阳明对朱熹哲学有所怀疑,但当时的王阳明并未就此与朱学分道扬镳。在相当程度上,阳明还将格竹毫无成效归之于自身天赋有限。若干年后,王阳明又读朱熹的著作,对其《上宋光宗疏》一文颇有所悟。在此文中,朱熹写道:“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阳明以此反观往日读书过程,认为自己涉猎虽广,但未能循序以进,故所得甚少。于是,又按朱熹的方法,循序而进,苦读深思。然而,这种方法虽使王阳明在义理的理解上有所长进,但却未能解决物理与吾心的统一问题:“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同上书,1224页)这一问题长久地困扰着王阳明。如此反复潜心苦思,最后王阳明又一次沉郁成疾。循沿朱学所导致的这种结果,无疑加深了王阳明对朱熹哲学的怀疑,并促使他寻找不同的探索方向。
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的兴趣一度转向兵家。当时边报甚急,朝廷迫切需要各种将才,而读书求道又一时苦无所得,这种情势,使王阳明少年时代便已萌发的经略四方之志重又出现。当然,王阳明已不满足于弓箭骑射,他更关注的是军事理论。在他看来,设立武举,至多只能发现骑射搏击之士,却难以觅得韬略统驭之才,而天下之安更依赖具有军事理论素养者。“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一》,《全集》,1224页)每逢友人来访或宴客,常排列果核如阵势状,以此为戏。对兵家和兵法的这种投合,当然并非仅仅出于好武,它始终从属于安天下之志向;而在阳明那里,安天下则是成圣的题中之义。就此而言,切入兵家并未离开对“第一等事”的追寻。
也正因精究兵家不同于偶然的偏好,故其持续的时间颇长。直至王阳明进士及第,任职京师,其军事兴趣依然未减。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以南宫第二名通过会试,随后至工部任职。同年秋天,受命督造威宁伯王越墓。这本是普通的民用工程,但王阳明却借此机会演练兵阵。他首先收集了王越在历次战役中布兵用阵的材料,仔细加以研究,然后将工匠役夫以什伍之法加以编排,得暇即指挥他们演八阵图,以初试兵法。当时瓦剌虎视眈眈于西北边境,王阳明特上《陈言边务疏》,提出了蓄才以备急,舍短以用长,简师以省费,捐小以全大等一整套御边战略。这些事实表明,在青年王阳明那里,成圣的追求始终没有离开外王的关怀。
精究兵家之外,王阳明还用力于辞章之学。如前所述,少年王阳明已初露其过人的文学天赋,经过多年苦读积累,其文学素养又有明显提高。王阳明于二十一岁乡试中举,但此后在举业上却历尽坎坷,1493年与1496年两次参加会试,均告落第。尽管当同舍有人以不第为耻时,王阳明还安慰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同上书,1223~1224页)但两度落第,毕竟不能不使人产生某种惆怅之情,而冷峻的兵法、面壁式的向外格物,显然难以给情感世界以充分的慰藉。于是,游心于诗境,便成为自我排遣的自然方式。第二次会试落第后,王阳明回到余姚,在龙泉山寺组织了一个诗社,时与诗友对弈联诗。前布政司魏瀚平时以雄才自恃,但与王阳明联诗时,佳句却常为阳明所得,以致不得不感叹:“老夫当退数舍。”由此亦不难想见阳明当时横溢的才气。当然,王阳明之志并不在斗诗争胜,对阳明来说,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同时具有陶冶性情的意义。
进士及第后,王阳明来到了作为文化中心的京师。当时的文化界,正是明前七子活跃之时。前七子的领衔人物是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等,他们以复古为旗帜,“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一反明初台阁体,在文坛颇开风气。也许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王阳明此时也十分倾心于诗文,并与李、何等“以才名争驰骋”(《阳明先生行状》,《全集》,1407页)。李、何辈在当时已是文学界名流,阳明能与之彼此驰骋,足见其文学造诣已达到相当境界。后来纪昀在《王文成全书提要》中说:王阳明“为文博大昌达,诗亦秀逸有致,不独事功可称,其文章自足传世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二十四》),这种评语显然并非虚发。
不过,尽管王阳明已可与李、何等辈在文坛上一见高下,但彼此的旨趣却并不完全相同。如前所述,阳明虽泛滥于辞章,但并不自限于此。诗文创作与审美活动在王阳明那里总是关联着求道的过程。王阳明一生留下为数可观的诗与文,它们录下了他探索“第一等事”的心路历程,也映现了他内在的情感世界。尽管后来阳明不再唱和于文坛,但艺术对德性的陶冶作用却始终没有被忽略。直到晚年,王阳明仍然认为,志于道与游于艺并非不相容,道如住宅,艺则是对住宅的文饰和美化,一旦志于道,则游于艺便有助于德性的培养:“如诵诗、读书、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传习录下》,《全集》,100页)从这些方面看,后来湛若水、钱德洪、黄宗羲等说阳明为学数变,并以驰骋辞章为数变之一,固然有见于阳明早年思想的演化,但却似乎未能充分注意阳明思想中前后一致这一面。
当然,诗文作为艺,诚有助于调习此心,但沉溺于此,亦可能偏离“第一等事”。王阳明后来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逐渐疏离当时的文学圈。王阳明弟子王畿曾追叙了阳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弘正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人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等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这一叙录可能来源于王阳明的晚年回忆。尽管这段话也许渗入了阳明某些后期思想,但其中提及阳明以追寻第一等德业为志向,并领悟到仅仅游心于诗文难以满足这种终极的追问,则显然合乎王阳明早年思想发展的逻辑。
根据《年谱》记载,王阳明疏离辞章之学后,便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告病回越,筑室阳明洞,行导引术。导引在当时主要属道教一系的修行方法,阳明潜心于此,显然表现了对道教的某种认同。事实上,早在1488年,王阳明已开始对道教发生了兴趣。这一年阳明到南昌完婚,举行婚礼这一天,阳明信步走入一个名为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静坐榻上,便向他请教有关养生之论。听了道士解说后,阳明若有所得,于是与道士相对而坐,直至破晓。冯梦龙在《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叙录了道士对王阳明所说的一段话:“道者曰:养生之说,无过一静。老子清静,庄子逍遥,惟清静而后能逍遥也。因教先生以导引之法,先生恍然有悟。”这或许不完全是虚构,在阳明日后的教法中,我们似乎仍可隐隐地看到其影响。铁柱宫的这一番经历,也许是王阳明接触道教的开始,而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阳明每每对道教心向往之。
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阳明依朱熹之教循序读书,不仅所得甚微,而且郁思致疾。苦闷彷徨之余,又与道士谈养生,一度产生了“遗世入山之意”。此时距铁柱宫之行已差不多有十年之久,王阳明的思想较十年前无疑更为成熟,因而这种意向显然不同于少年时代的偶然冲动。三年后,王阳明奉命至江北审查案件,事毕,便前往九华山观景览胜,沿路止宿于无相寺、化城寺等处。当时山中有一位道士叫蔡蓬头,善谈仙道,阳明慕名前去拜访。然而,尽管王阳明礼节周到,但蔡蓬头却似乎不愿与阳明深谈,只是一再含糊其辞地说“尚未”。在王阳明的一再恳请下,蔡蓬头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结果二人相视一笑,就此道别。蔡蓬头的评语颇有意味。官相似乎象征着儒家的圣王境界,不忘官相背后所隐含的,是未能忘怀儒家的圣王之境。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心态确乎较为复杂。宋儒的理论进路固然扞格不通,但成圣的志向却又难以放弃;遗世入山诚然有其吸引力,但归隐山林又与平治天下相冲突。蔡蓬头的那一番话,有意无意地触及了阳明思想中的这种内在紧张。
除蔡蓬头外,九华山还有一位异人,居住地藏洞,坐卧于松叶之上,以生果为食。王阳明闻其名,特意攀登危崖险壁前去访问。找到岩洞时,这位异人正蒙头熟睡。阳明静坐其侧,直到他醒来。异人见阳明来访,甚感意外,问他路途艰险,何以至此。谈到何为学问的上乘,异人评价道:“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王阳明后来曾第二次上山拜访这位异人,但异人已远徙他处。据《年谱》说,这使阳明不免有“会心人远之叹”(《全集》,1225页)。异人是道教一系人物,但却肯定儒家中亦有见道者,而王阳明则将其引为知音,这里既有对儒的认同,又有对道的倾心,其心境很难一语道尽。
江北之行差不多历经一年,而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游历道观与寺院中度过的。弘治十五年,王阳明回京复命。此后一段时间,阳明又开始了进一步的沉思探索。常常日间处理案牍,晚上挑灯夜读,从五经到先秦两汉诸书,广为涉猎。尽管此时王阳明已过而立之年,但求道的热忱却丝毫不减当年,几乎每日苦读到深夜。过度的思虑积劳,终于使阳明身染呕血之疾。王阳明的体质一直较为虚弱,向有“咳嗽之疾”,现又加上呕血,这使他不能不下决心作一较彻底的调治,于是便有前文提及的告假养病之举。
王阳明本来便对养生怀有兴趣,身患沉疴更使他寄希望于道教的养生术。归越之后,便居阳明洞,静坐并行导引之术。“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命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年谱一》,《全集》,1225~1226页)阳明是否真修就了如此神奇的先知术,现已无法断论,可以由此推知的也许是,阳明此时对道教的某些方术已有较深契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王阳明对导引术等的身体力行,已不完全是一种义理上的认同,毋宁说,他更多地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术”(养生之术或其他方术)。“先知”(预测未来)固然玄之又玄,但后来王阳明便意识到这种方术徒然浪费精力,“非道也”(同上书,1226页)。而王阳明所追求的,依然主要是作为“第一等事”的道。
道与术的区分,已蕴含了王阳明与道教分道扬镳的契机。尽管由于体弱多疾,加之较长时间隐居静坐,阳明似乎已难堪世间的纷嚣,并一度再次萌发“离世远去”之念,但道教对他来说毕竟非“道”,因而难以满足他对“第一等事”的追求。相反,人伦关怀却如此强烈,以致即使在出世意向萌发之时,他仍无法忘却对父辈与祖辈的责任:“已而静久,思离世远去,惟祖母岑与龙山公在念,因循未决。”(同上)在儒与道的这种冲突中,前者最终压倒了后者。《年谱》对此作了如下记载:“久之,(阳明)又忽悟曰: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同上)不难看出,王阳明对“第一等事”的追寻,蕴含着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即儒家的人伦原则,而对阳明来说,这种原则即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作为告别道教的象征,王阳明于翌年(1503年)离开阳明洞,前往杭城西湖养病。
与出入道教几乎同时,王阳明亦常常游心于佛家。1501年审案完毕游九华山期间,阳明不仅接触了不少道教中人物,而且与佛家禅师也有交往。有时留宿寺院,在清风朗月下与猿鹤同听和尚唱偈参禅:“月明猿听偈,风静鹤参禅。今日揩双眼,幽怀二十年。”(《化城寺六首》,《全集》,667页)此情此景,本身便颇有点禅的意境。遇到熟悉佛教历史的老僧,则与之共话禅家旧事:“微茫竟何是?老衲话遗踪。”(同上)即使在归越养病期间,阳明亦常往来于佛寺:“岩犬吠人时出树,山僧迎客自鸣钟。”(《游牛峰寺四首》,《全集》,663页)间或甚而借居禅房:“一卧禅房隔岁心,五峰烟月听猿吟。”(同上书,664页)这里无疑体现了某种超越的追寻。不过,相对于理论上的契合,诗境与禅意的呼应在此处显然占了更多的比重。如同对待道教一样,王阳明似乎并未完全在“道”的层面上达到与佛家的认同。
王阳明与佛家的如上关系,使他很难自限于佛家的境界。随着与道教的疏离,对佛家的怀疑也逐渐增长。1503年,王阳明在杭城养病期间,曾往来于南屏、虎跑诸刹,其中一寺中有位和尚,坐禅三年,既不开口说话,也不睁眼视物。一次,王阳明对这位禅僧大声喝道:“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僧人为之一惊,于是睁开双眼,并开口说话。“先生(阳明)问其家。对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对曰:‘不能不起。’先生即指爱亲本性谕之,僧涕泣谢。”第二天,这位坐禅三年的和尚便离开了寺院。(《年谱一》,《全集》,1226页)这似乎是一场儒佛之间的交锋。王阳明以儒家的人伦原则克服了道教的“离世远去”,也以同样的原则唤醒了沉沦于禅境的佛界中人物。尽管对禅僧的开悟运用了近乎机锋的方式,但它的真正象征意义却在于诀别佛家。
弘治十七年(1504年),王阳明回京。同年应聘主持山东乡试。在策问中,王阳明已直截了当地批评“佛老为天下害,已非一日”(《山东乡试录序》,《全集》,860页)。这固然是由于官方考试不能不合乎正统的意识形态,但同时亦表现了王阳明自身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这一时期,阳明有鉴于当时学者大多沉溺于辞章,而很少讲身心之学,于是倡导立志成圣人之说。这一为学宗旨在当时也许给人以空谷足音之感,“闻者渐觉兴起,有愿执贽及门者”,阳明遂开始收弟子讲学,由倡成圣之学到讲成圣之学。
自弘治二年(1489年)见娄谅,深契圣人之学,到力倡并开讲成圣之学,在对“第一等事”十余年的探讨思考中,王阳明广涉宋学、兵家、辞章、佛老,最后似乎又回到了出发点:“第一等事”依然被归结为如何成圣。当然,这并不是简单的返归。较之十二岁时“学以成圣贤”的自发意向,十八岁时对“圣人可学而至”的契合,弘治十八年前后的倡立志成圣之学无疑具有更深刻与丰富的内涵:这是一种经过多向度探索之后的认同,而如何成圣作为“第一等事”则相应地获得了更自觉的定位。在出入于各家诸派的过程中,王阳明固然范围众说而超越之,但这一时期的多方面涉猎,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其尔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