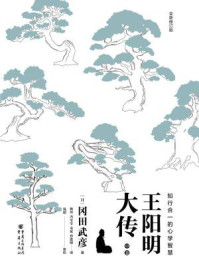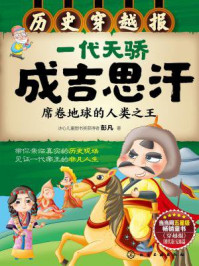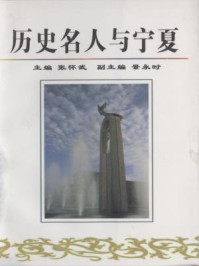来英国仅仅两年,丁文江就从一个英文只有初级水平、刚刚接触自然科学知识的青年,成为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的学生。据李祖鸿说,丁文江在剑桥可能读的是文科专业。剑桥的学术水平是一流的,然而,剑桥大学的学费和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司堡尔丁,“一年用费必得三千金”,后来的银行家独子徐志摩可以悠游康桥,但这笔费用远远不是小康之家的丁家所能负担得起的。因此,在剑桥仅仅过了几个多月,丁文江就退学了。不过,他在剑桥也不是一无所获,李祖鸿说:“他在剑桥大学时,受了名师的指导,于英文一项,竟告完成。”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丁文江就在英国一两家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可见英文已有相当的水准。回国后,丁文江的英文写作水平屡受名家称赞,固然主要由于他出色的语言天赋,但与剑桥的短暂求学也许不无关系。
那时,李祖鸿被老师司拜塞(Spicer)介绍到约克郡董克司多(Doncaster)市的美术学校读书,1906年年底放假时,丁文江去董克司多看望李祖鸿,告诉他因为经济上无法承担,自己不打算再去剑桥了。由于重新考试、进别的学校还需八九个月的时间,丁文江决定利用这段时间去欧洲大陆游历。1907年,他去了德国、瑞士等国,其中在瑞士洛桑住的时间最长。在这一时期,他对欧洲的政治有了更深的了解,法语也有长足的进步,已经可以用法语进行日常交谈。
第二年七月,丁文江结束了在欧洲大陆的游历,回到英国。他在途中给李祖鸿写了封信,邀李祖鸿同去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格拉斯哥坐落于苏格兰中部的克莱德河西岸,离爱丁堡不远,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维多利亚时期有“大英帝国第二城”之称。丁文江说,他已经打听到格拉斯哥有很好的美术学校,李祖鸿可以去那里求学,而丁文江自己则打算报考伦敦的医科学校,在此之前,也会暂时住在格拉斯哥。于是,李祖鸿转学去了格拉斯哥的美术学校,丁文江则在格拉斯哥的一所专科学校选修了课程,为考伦敦大学医科做准备。
本来以丁文江的聪明,考伦敦大学应当没有问题,结果他自恃是考试能手,有点轻敌了,由于准备不充分,有一门考试没能及格,不符合当时伦敦大学“必须所有课程全部及格方能入学”的规定,最终未能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可能是这个挫折来得非常意外,以至于丁文江就此放弃了去伦敦大学学医的念头,第二年秋天考入本市的格拉斯哥大学。
格拉斯哥大学是1451年在当时的苏格兰国王詹姆斯二世建议下创建的,它是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之后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全球最古老的十所大学之一。创办几个世纪以来,不断发展,成为苏格兰的启蒙中心,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发源地之一,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著者)、工业革命之父詹姆斯·瓦特、苏格兰哲学之父弗兰西斯·哈奇森、热力学之父威廉·汤姆森等著名学者都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1905年至1908年任英国首相的自由党政治家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也出自格拉斯哥大学。

1909年丁文江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时,格大作为一所规模庞大的综合性大学,下设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等六个学院。当时格拉斯哥大学规定,选读科学类的学生,第一学年不分专业,先学习数、理、化等基础课程,考试及格后再选择主科一种、副科两种。丁文江第一学年结束后顺利通过了考试,选择动物学为主科、地质学为副科。动物学是当时格拉斯哥大学的优势学科,在格拉斯哥大学古老的巴沃楼内,存有达尔文《物种起源》数页原稿。 1910年,丁文江增加地质学作为主科、地理学为副科,当他于1911年毕业时,获得了动物学和地质学两个学士学位。
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师从地质学家格里高利(J. W. Gregory)教授,格里高利教授不仅是他那个时代英国最杰出的地质学家之一,还是一个出色的探险家。1908年,他进行了一次北非探险,在那次探险过程中,他对人类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位精力充沛的教授还对其他很多领域有强烈的好奇心,1925年他写了一本关于优生学的、名为《色彩的威胁》(The Menace of Colour)的书,1928年出版了《人类的迁徙及未来》(Human Migration and the Future),1931年他又出版了《道路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ad)。对人类几乎一切知识领域都充满好奇心的格里高利教授,对丁文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丁文江回国后还与他保持了多年的通讯联系。1932年6月,当68岁高龄的格里高利教授在秘鲁南部进行探险、研究火山和地震时,不幸由于翻船事故落水淹死,丁文江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悲痛。
在司堡尔丁文法学校,丁文江获得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基础知识,而在格拉斯哥大学,丁文江受到了严格的科学训练。当时跟他住在一起的李祖鸿说:“我记得他有一次不知在哪一个实验室里工作觉得很难,颇感棘手,他归家时对我一方面表示对他师长的佩服,一方面自励说:‘我必须养成这种好习惯,方始有真正求学和做事的才能。’”这种训练使丁文江培养出“科学化性格”,也使他对科学产生了终生不渝的热爱,这种热爱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几乎成为一种信仰。英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国家,20世纪初的英国,还没有遭遇世界大战对“科学、理性、进步”信念的沉重打击,是当时“用科学为人类谋福利的最先进之国”。在这种氛围里,丁文江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还越出实验室之外,深受达尔文、赫胥黎、葛尔登(Francis Galton)等人科学精神的鼓舞,从此,“科学”成为他的精神家园。胡适曾说,丁文江在格拉斯哥大学“最得力的是达尔文、赫胥黎一流科学家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训练”。科学的明晰、确定,科学对于现实生活直接而巨大的力量,以及讲科学、求真理过程中所蕴含的进步与乐观的情绪,使得从昏沉沉的东方“老大帝国”来的丁文江,仿佛拨开迷雾,第一次见到了清朗的景象。与西方那些坚定的启蒙主义者一样,丁文江坚信“科学万能”:
科学……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单简,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的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曾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
傅斯年认为,正是英国的思想与环境,铸就了丁文江的科学化精神。这种“科学化精神”就是:“行为思想要全依理智,而不可放纵感情压倒了理智。”“是是非非要全依经验,而不容以幻想代经验。流传之事物或理论,应批评而后接受,而不容为世间的应声虫。”他还指出,丁文江关于社会合作、社会改革的观念,如“一切事物之价值,全以在社会福利上人类知识上之关系为断”“社会是一种合作集团,人人要在里边尽其所有之能力”“社会之不公、不合理,及妄费之处是必须改革的”,等等,也是在近代英国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在丁文江看来,“科学”应是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而不应狭隘地局限于自然科学研究上。后来,他以“地质学家”名世,但他的兴趣、工作、成就远远超出了地质学甚至自然科学。与日本留学时期相比,在英国读书时,丁文江似乎不再过多谈论“革命”了,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兴趣。英国知识阶层对于政治和经济的广泛关注,不可避免地对丁文江产生了影响。这一时期他看了很多经济学方面的书,但他的朋友后来说他“尤其喜欢凯恩斯(J. M. Keynes)”,凯恩斯的书“每本必看”,则可能是年代有误了,凯恩斯仅仅比丁文江大四岁,在丁文江1911年离开英国前,尚未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丁文江对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很感兴趣,认真阅读过相关文章和书籍,傅斯年判断:“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批思想的影响者。”功利主义不能等同于自私自利,与中世纪提倡奉献、利他、节欲的思想不同,功利主义者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社会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因此,社会治理的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并且“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就是最有效用的”。在儒家道德观熏陶下成长的丁文江,对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接受起来毫不困难,对于“行为的最高目的应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这样与中国传统教诲大相径庭的观念,却也深深认同。后来,他的好友们注意到,丁文江尽管节俭,却总是在自己能力许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自己的生活尽量舒适,比如旅行时能坐一等车决不坐二等车,每年夏天都要带家人去海边休养度假,等等。而他的思想行为,尤其是政治主张,更是严格贯彻了“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利益,就是最有效用的”原则。
与当时的英国知识分子日常习惯一样,丁文江喜欢看报,尤其喜欢看英国有名的严肃大报《泰晤士报》。当时英国正是自由党活跃时期,他对于自由党的政治主张、自由主义的理念想必是了解的,但胡适说丁文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认其为自由主义者,则未必如是了,这从他20世纪30年代访问苏联、对苏联人集体主义观念的赞同可见一斑。他还喜欢读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哈罗德·拉斯基(H. J. Laski)、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及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文章,广泛的阅读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
大学学习是紧张而愉快的,但经济紧张始终是一块笼罩在丁文江头上的阴云。考入剑桥大学时,经济压力骤然加剧的丁家,就曾向丁文江的恩师,当时仍然在当泰兴县令的龙璋求助,请求他代丁文江争取官费津贴。当时一些中国留英学生也曾帮他上书清政府驻英大臣李经方,证明丁文江“经英伦大学选为正科,正今在葛拉斯古实业学校肄习工科。英制惟英伦大学正科生可见纳于各官学校,将来卒业即为该大学之学生”,为丁文江争取官费津贴。
当时中国留洋的学生,除了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生和自费生之外,还有“公费生”,官费生的经费由各省或“学部”出,而公费生的留学经费则由各州县自筹。并且根据当时清政府的规定,只要能考取外国的大学,即使是自费出国的,也可以申请“递补官费”。据李祖鸿说,丁文江在去格拉斯哥之前,家中寄来的钱就已“多半是他本县的公费”,那是在龙璋先生的帮助下,丁臻祺上书给两江总督端方,端方指令泰兴县每年津贴几百元的公费;到格拉斯哥后,驻英公使汪大燮又帮丁文江争取到了每月十镑半的官费。
那时丁文江和李祖鸿仍然“经济通用”,李祖鸿家每年也寄来约800元,这些钱加在一起,勉强解决了两人的学费和生活费问题。尽管经济不宽裕,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丁文江每逢假期都要外出游历,最远去了德国。这也是丁文江坚持一生的原则:不乱花钱,但该花的钱也不会一味节省。他还喜欢帮助朋友,有时会接济遇到经济困难的同学。1933年,丁文江为了去苏俄考察,在柏林办相关手续,偶遇了一位他曾经帮助过的大学同学:
正说话间,忽然又一个中年的人从旁边一个小桌子上走了过来,向我问道:“你是中国人学地质的。你知道有个丁文江吗?”“我就是丁文江!”“什么!丁文江!你不认识我哪,我是尼采!”我仔细一看,可不是二十四年前在苏格兰给我同学的尼采!他是一个极苦的学生,一面读书,一面教俄文为活。1911年他巴黎学法文时,川资用完了,困在那里。我寄了他几镑钱方始渡过难关。不料在此间无意中遇着。于是他从新给我介绍:“这是我的老朋友,是帮助我学费的朋友!请你们大家照料。”
经过在日本时结识的好友张轶欧斡旋,1910年,丁文江和李祖鸿被告知可以“补全官费”。这时,丁文江已经快要毕业回国了,于是他把自己的那部分官费让给了李祖鸿。而李祖鸿知道丁文江有毕业游历的计划,当拿到补给他的一百多英镑官费后,李祖鸿又把这笔钱交给丁文江做盘缠,玉成了丁文江在国内的第一次西南考察。
1911年春天,丁文江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他没有等到毕业典礼举行,便匆匆回国。这时,距离他走出故乡黄桥、走出国门已近九年。九年的时光,从东洋到西洋的半个地球的漂泊,使他从一个步行从未超过三里路、不懂数理化的15岁少年,长成热衷野外考察,通晓英、日、德、法数种外语,具有科学头脑和国际视野的24岁青年。在这九年里,尤其是在英国的七年,他逐渐成为“一个欧化最深的中国人”“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他的生活最有规律:睡眠必须八小时,起居饮食最讲究卫生,在外面饭馆里吃饭必须用开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来洗筷子;夏天家中吃无外皮的水果,必须先在滚水里浸二十秒。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总要寻一个歇夏的地方,很费事的布置他全家去避暑。
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因为他受到英国人生活习惯的影响。英国是近代化进程开始最早的国家,16、17世纪时,培根等人就提出知识要为人的幸福服务,随后工业革命兴起,三个世纪后,丁文江所见的英国,已是当时世界上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个与他传统落后的家乡形成鲜明对比、判若两个世界的国度,即使不能说重新铸就了丁文江,至少也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过,英国也有守旧的一面,普通英国人守旧、自大、摆架子等毛病,丁文江却一点也没有,正如多年后傅斯年所观察到的:
英国有很多极其可恶的思想,不过在君所受者却是最上层精粹。因为在君能读法德文书,走过大陆,他对于英国人之守旧、自大、摆架子、不自觉的自欺,必然看穿。他绝看不起中国人学来一个牛津架子,或者他对于圜桥清谈,也不尽看重吧。
现在,这个“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完全近代化了的中国青年,要回到那个仍然有皇帝、礼教、男人留着长辫子的古老中国去了,而且还将计划由西往东横穿整个中国腹地,他将会有怎样的遭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