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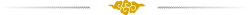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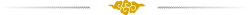
摘要: 1993年10月,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科学工程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被美国众议院投票否决,引起了全球范围很多领域内科学家的强烈震动。这一事件是人类科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方面对当代科学基础科学前沿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象征性地揭示出大科学时代基础科学研究面临的种种问题。本文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过程,并从科学与经济、科学政策与管理、国际竞争与协作等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超导超级对撞机;大科学时代;基础科学研究
超导超级对撞机,即SSC(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曾被认为是自从两千年前古希腊人开始探索物质终极本质以来迈出的最重要一步,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科技建造工程。这项工程寄托着全世界科学界的希望,被认为是“人类最大的梦想”。不幸的是,在技术条件允许的前提下,SSC却由于非科学因素不幸夭折了。这一重大科学史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首先,SSC事件代表性地揭示了,在大科学时代背景下发展大型基础科学研究所面临的资金、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困难,给人类如何摆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地位;如何处理好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展基础科研提供了借鉴。
其次,中国的科技发展也蕴藏着片面发展应用科学、忽视基础研究的潜在危险。SSC事件为中国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启迪。
另外,SSC事件还警示我们:基础科学研究应该置身于纯科学研究机构的管理之下,否则,一旦涉及业务竞争,科学研究必然受到损害,科研工作者的自由探索也无法得到保障。在微观上,SSC事件也表明,研究团体必须在科研工作中保持良好的科研氛围。
那么,SSC究竟是什么样的科技工程?为什么起初要耗费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巨资来建造这一项目?又为什么在计划启动不到5年的时间遭到终结?我们先看一看SSC是什么样的科技工程。
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就开始思考世界的基础物质是什么,他们认为,认识到这种基础物质就等于理解了世界的本质。两千年来,人类一直在不停地探索,希望能找到组成物质世界的“终极砖块”。随着人类对物质结构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就越发现物质是由更基本的层次组成的。一般物质是由原子构成;原子里有电子、原子核,而原子核也是由一些更基本的例子构成;这些更基本的粒子又是由还要更基本的各种夸克构成的。
科学家是如何一步一步得到这些认识的呢?实际上,要获得这些认识,需要将这些小粒子打碎来进行验证。打碎原子很容易,但打碎原子核就需要一百万伏特的电压,需要一百万美元的投入。而要打碎基本粒子,就需要十亿伏特的电压和数千万美元。在探索夸克和统一场论的最初几个阶段,几乎需要一万亿伏特电压和几亿美元。SSC预定提供大约一百万亿伏特的电压,需要大约一百亿美元的费用。
SSC的主环是一台采用超导磁铁、双环结构、周长达80多公里的质子—质子对撞机,每束质子流的能量达到20万亿电子伏特,这样,对撞能量就可以达到40万亿电子伏特。它包括一个长达200米的质子直线加速器,一台周长为0.54km的低能增强器,一台周长4km的中能增强器和一台周长近11公里的高能增强器。注入器提供2万亿电子伏特的质子流,注入SSC的主环。两束质子流以相反方向在两个同心的超导环中旋转、加速,并被引入对撞区发生碰撞。SSC的能量比现有最好的质子对撞机的能量高20倍,而量度则高1000倍。它将使物理学家可能发现新的现象和新粒子,从而有了超越现有科学理论的可能性。
目前,科学家们用所谓的标准模型(standardmodel)
 理论来描述微观世界的结构和相互作用。十多年来,标准模型不断为高能物理的试验所证实。但是,对于标准模型对微观世界的描述,高能物理学家们依旧存有不解之处。两种夸克加上电子与中微子已足够解释通常物质的构成,那么另外8种轻粒子的存在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加州的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佩斯(Robert Peccei)说:“除去其他基本粒子,自然界已运行得相当完美,那么它们究竟为什么必须存在呢?”
[1]
而标准模型通过引入自由参数的方式来对粒子的聚集进行解释也使得标准模型理论与科学家们的一个信念相悖——自然的和谐性:如果通过改变参数来改变解释电子的聚集方式,我们会发现这对于解释其他基本粒子的聚集方式将毫无影响。此外,不少科学家对基本粒子的不同质量也抱有疑问,正如凯斯·埃李斯(Keith Ellis)所说:“我们无法理解顶夸克以及其他夸克为什么以标准模型揭示的方式进行集合——一些质量太大了而一些太小了。”
[2]
值得庆幸的是,依旧有两件事需要物理学家们去奋斗,并为解决上述疑团留下了一线光明。第一件事是寻找标准模型预言的希格斯粒子(Higgsboson);第二件事是寻找标准模型预言的顶夸克(topquark)。
理论来描述微观世界的结构和相互作用。十多年来,标准模型不断为高能物理的试验所证实。但是,对于标准模型对微观世界的描述,高能物理学家们依旧存有不解之处。两种夸克加上电子与中微子已足够解释通常物质的构成,那么另外8种轻粒子的存在究竟又有什么意义呢?美国加州的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佩斯(Robert Peccei)说:“除去其他基本粒子,自然界已运行得相当完美,那么它们究竟为什么必须存在呢?”
[1]
而标准模型通过引入自由参数的方式来对粒子的聚集进行解释也使得标准模型理论与科学家们的一个信念相悖——自然的和谐性:如果通过改变参数来改变解释电子的聚集方式,我们会发现这对于解释其他基本粒子的聚集方式将毫无影响。此外,不少科学家对基本粒子的不同质量也抱有疑问,正如凯斯·埃李斯(Keith Ellis)所说:“我们无法理解顶夸克以及其他夸克为什么以标准模型揭示的方式进行集合——一些质量太大了而一些太小了。”
[2]
值得庆幸的是,依旧有两件事需要物理学家们去奋斗,并为解决上述疑团留下了一线光明。第一件事是寻找标准模型预言的希格斯粒子(Higgsboson);第二件事是寻找标准模型预言的顶夸克(topquark)。
科学家们通过能量级不断增加的粒子加速器对标准模型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丰厚的实验成果,然而从Mev(百万电子伏)量级到Gev(十亿电子伏)量级,顶夸克与希格斯粒子始终不露踪迹。科学家们认为,根据标准模型理论,其二者匿身不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粒子加速器的能量没有达到固有的要求,一旦建成更高能量级别的粒子加速对撞机,我们将更好地观察物质构成的微观景象并将加深对宇宙四种基本作用力的认识从而更好地研究宇宙的起源。而SSC的建造便有可能使科学家找到这两种粒子。
高能物理学家根据标准模型预见,一旦粒子束以数十万亿电子伏的能量进行碰撞将成功模拟宇宙大爆炸。在爆炸瞬间,标准模型中本难以区分的四种基本作用力将先后分离。首先,爆炸10 -43 秒之后,重力分离。其次强相互作用力于爆炸10 -31 秒后分离,而弱相互作用力与电磁力将于爆炸10 -10 秒后分离。接着,科学家们将观察到本质统一的弱相互作用力与电磁力是如何均匀分离的。科学家们认为,弱相互作用力与电磁力的分离十分可能蕴涵着基本粒子如何聚集的奥秘。因为,电磁力被视为一种玻色子——无质量的光子——的变换。而弱相互作用力则被视为重质量的玻色子W和Z的变换。标准模型预言在两种作用力由统一分裂之时,这三种玻色子均无质量,那么W和Z介子的质量如何获得就等着高能物理学家们在万亿伏级的能量碰撞之下去一窥究竟。而至今解释W和Z介子集合的唯一方式便是引入标准模型中的希格斯粒子,因此希格斯粒子在高能粒子束的碰撞中将很有可能被发现,而希格斯粒子也很有可能成为解决一系列高能物理疑难的关键。 [3] 科学家们也相信在万亿伏能量级的粒子碰撞之下,顶夸克的探知也必将引领科学家们进一步对夸克质量的本质进行追问。
于是对顶夸克尤其是希格斯粒子的探知便寄托了科学家们解决高能物理谜团的殷切希望。高能物理在标准模型的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功令物理学家们深信不疑,一旦粒子加速器的能量达到了标准模型给出的级别要求,顶夸克与希格斯粒子想要不现身都难。然而,很难说建造SSC只是为了寻找这两种粒子,更为关键的是,标准模型理论虽然没有指出在粒子束在更高的能量范围内碰撞究竟会产生什么新现象,但它确已指出新的物理现象将会涌现出来。换言之,基于标准模型的“绝对”成功,科学家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建造了能量级更高的粒子加速器,学者们不但可以对顶夸克与希格斯粒子进行测量分析从而解决现有的物理难题,还能够通过研究全新的高能物理现象打开一道通向物理新天地的大门。
除了至今未被科学家们发现的顶夸克与希格斯之外,标准模型所做出的理论预言几乎一一应证。在标准模型的成功下,高能物理学自身却成了牺牲品。标准模型的“绝对”成功给高能物理界带来了绝对的“黑暗”。自古以来,如卡尔·波普尔所说,物理学理论在不断证伪中不断前进。也正因为理论证伪的可能,科学家们饱含着不断探索的热情与渴望。每一次证伪都意味着现有科学理论的缺陷与不足,而它所伴随的必然使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证伪非但不令物理学界沮丧,反而令人鼓舞雀跃。与此恰恰相反的是,不能证伪的理论意味着绝对的真理,而绝对真理便意味着科学的终点,科学将永远停滞不前。所有的科学家也将由此失去存在的意义,穷尽毕生精力的他们将无奈地承认自己已没有任何办法为科学的大厦添上一片砖瓦,他们至多只能做一名掌握精深技术的工匠,绝无可能去体验创造的乐趣。标准模型在现有的研究能量及研究精度范围内恰恰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无法证伪的“完美”理论。美国费米试验室的理论物理学家凯斯·埃李斯叹言:“在CERN(European Laboratory for Particle Physics,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位于日内瓦)他们做了十分精确的测试,以求击倒标准模型。”可新物理学之门并没有打开:“每一个试验结果都可悲的与标准模型相符,我们不知道将来究竟会发生什么。” [4] 哈佛大学物理学家格拉肖(Glashow)坦言,高能加速器一旦只发现希格斯粒子却未发现新现象将是一种最坏的研究结果。这样,标准模型或许将真的成为高能物理学的坟墓。高能物理学家们对物理新现象的渴望,对逃离标准模型的渴望可见一斑。
在更好地解释标准模型中的悬疑并对标准模型进行改进甚至证伪的渴望之下,40万亿伏级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背负着高能物理学界的无限期盼登上了历史舞台。
基于上述科学背景,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即超导超级对撞机SSC的计划最早于1982年由一些有远见的高能物理学家提出,其中包括了美国费米试验室的主管R.R.威尔逊(R.R.Wilson),此时预计美国将以30亿美元建成SSC,1983年7月美国能源部高能物理咨询委员会建议优先建造SSC。在能源部的推动下,URA
 管辖下的R&D小组于1984年开始设计SSC并于1986年完成了详细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以现有的或近期即将达到的加速器技术和工艺建造一台40万亿电子伏质心系能量的高亮度质子—质子对撞机,不会存在技术原则上的困难。
管辖下的R&D小组于1984年开始设计SSC并于1986年完成了详细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以现有的或近期即将达到的加速器技术和工艺建造一台40万亿电子伏质心系能量的高亮度质子—质子对撞机,不会存在技术原则上的困难。
SSC工程得到了里根总统的极力支持。在里根总统于1987年同意SSC的建造计划之后,SSC的选址竞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最终,得克萨斯州南郊的埃利斯县从43处选址中胜出,SSC的部分部件也开始进入了建造阶段。
SSC的造价一直是影响其命运的关键因素。1987年,SSC的估计造价为44亿美元,1993年SSC的估计费用已经涨到了令人咋舌的110亿美元!SSC一步步地取得了技术上的突破,与其相伴随的则是日渐增长的估计费用与反对声音。1989年9月,冲破重重障碍的SSC得到了年度的财政拨款,把SSC的造价限制在50亿内的提案也遭到了国会的否决。1991年,美国众议院讨论SSC的年度预算时,反对者提出了停止建造SSC的提案,但以87票败北。但到了1992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严重的赤字问题使得不少议员不得不再次思考SSC究竟是否应该生存。议员成分结构的变动外加部分支持者的“倒戈”终使众议院以232∶181否决了SSC工程。然而,参议院却救了SSC一命,在布什总统的鼎力相助下,SSC得到了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的支持,得到了1992年的财政拨款。SSC的未来却令人极度担忧。不少人寄希望于得到国际上尤其是日本的资金支持,令SSC走出泥潭。可事与愿违,日方终究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遗憾的是,对SSC极力支持的老布什终究走下了历史舞台。打着缩减财政赤字旗号的克林顿走到了聚光灯下。而能源部新部长欧列莉(O'Leary)在就职前一直在公开场合表示她对SSC毫无兴趣。1993年7月,美国众议院又一次以更大的优势(280∶150)否决了SSC下一年度的预算,URA亦停止了SSC的隧道挖掘以等待命运的最终宣判。与去年相同的是参议院仍然对SSC给以支持,虽然反对者显然增加了(1992年,62∶32;1993年,57∶42)。由此,不少SSC支持者乐观地认为,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必能像去年一样说服众议院放弃否决SSC的决定。然而,在这段紧要期间内,有关SSC的负面新闻却大量涌出。其中包括了对工作场所的摆设与膳食的批评,舆论认为SSC的工作人员生活得太奢侈了。更致命的攻击则集中于URA的管理能力上,反对者认为URA对SSC的建造费用严重估计不足,对SSC遇到的技术困境也缺乏必要的预见性。另外,不少新闻透露,建造同样的超导磁铁,在欧洲要比在美国经济得多。由此,SSC在很多人眼里早已成为一个浪费的、缺乏效率的奢侈工程。而早在7月初,于众议院对SSC的下一年预算表决投票之际,一份从美国能源部透露的资料还表明,能源部对SSC的合法强制性监管曾遭到SSC工作人员的蓄意阻挠。欧列莉坦言,URA在管理SSC上是失败的,美国能源部将会以新的工业管理组织取代URA进行工程管理,URA则退居二线,主要负责科技上的研究。
尽管参议院依旧站在SSC一边,但这一次好运没有再次垂青SSC。虽然起初美国众参两院联席会议要求众议院放弃否决SSC的计划并同意给予SSC工程6.4亿美元的年度拨款。但众议院并没有像1992年一样接受两院联席会议的提议。以斯拉特利(J.Slattery)为首的众议院反对派极力要求驳回关于继续支持SSC的议案,并于10月最终在众议院以282:143枪毙了年轻的SSC。
就这样,已耗资20亿美元的SSC夭折了。众多高能物理学家表示了震惊、悲哀与无奈。“我们被宣判了死刑!”马萨诸塞技术研究所的一位知名物理学家叹言:“SLAC(斯坦福线性加速器)太老了,费米实验室也已步入中年……没有人知道在高能物理领域我们将步向何方。” [5] 一位物理学家愤怒地说:“在我心情最黑暗的时候曾认为,人类最高的梦想之一,竟然被一批胡闹的政客和判断力之恶劣足以比得上其忌妒心之深的科学家所组成的联盟所毁灭。……没有了SSC,我们将向何处去?” [6]
SSC短短的十年寿命异常沉重,高能物理学家们也经历了从天堂到地狱的一次坠落。SSC夭折的原因错综复杂,在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依旧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耗资巨大。建造SSC工程的建议一经提出,针对其昂贵造价的批评声音便纷至沓来。不少人认为在1980年代的背景下,建造SSC是不合适的,它将是美国财政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在美国之前建设的加速器工程中有3/4的实际造价都超过了预算,这也给SSC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事实恰恰如许多人所预料的那样,出于各种原因。在美国财政赤字问题越来越突出的同时,SSC的估计造价不断飙升。考虑到通货膨胀问题,1988年SSC的造价已抬高至53亿美元。而在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美国能源部于1月公布的SSC估计造价已经达到59亿美元。在59亿美元中,美国政府只期望支付其中的39亿美元;另外20亿美元中的一半将由得克萨斯州承担,另一半则将力求来自他国的捐赠。美国曾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对SSC进行支持,可日方一直给予暧昧态度,从未给出可靠的承诺保证。虽然能源部的足迹早已遍布意、法、英、日、瑞士、加拿大各国,可正式的官方捐助只有印度的0.5亿美元。这就意味着这10亿来自国际的建造资金最终很有可能要由美国政府来掏腰包。SSC反对者的声音也伴随着费用的抬高不断增长:SSC将是一个美国无法承受的吞钱黑洞,在每年财政赤字高达百亿美元的美国,造价如此高昂的SSC实在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反对者们建议,巨额的科研经费应投放到更为富有经济效益预期的科技项目中去,此外,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粒子加速器的实际建造费用要比预算高出许多。果然,到了1991年1月,能源部公布的SSC估计造价突然猛涨至82.5亿美元,(此时能源部独立估价小组的非官方报价更是高达117亿美元)。这一次SSC估计费用的大幅上涨主要源于SSC工程的设计更新。技术上的革新需要更多的资金与时间。SSC的估计费用大幅上涨,SSC的竣工日期也从原有的1998年推至1999年。工期的延长又意味着投入的增加,包括工作小组的工资在内,SSC推迟6个月竣工,美国政府就不得不从拮据的口袋中再掏出5亿乃至更多的美元。与此同时,SSC的两个关键部件,两架价值5亿美元的粒子探测器SDC和GEM也面临着技术与资金的双重困境。两架粒子探测器预计耗资10亿美元,美国政府只愿意承担5亿美元,但另外5亿来源于国际援助似乎只是美国一厢情愿的想法。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名物理学家断言:“SDC和GEM想分别从国外得到另外的2.5亿美元简直是做梦,仅仅是做梦!” [7] 而一个SSC的内部预算估计小组则透露:SDC的造价将会高达7.12亿美元。为此,DOE(美国能源部)也表态,如若资金实在困难,我们将只先建造SDC进行物理研究,GEM的建造将被推后。面对力图缩减赤字以求恢复美国经济繁荣的大环境,生不逢时的SSC无奈成了经济的牺牲品。
第二,基础研究。SSC工程与其他众多应用性科技项目相比无疑是一项基础性科研项目,它的目的在于探索宇宙与物质构成的奥秘。SSC的反对者们从中很难得到丰厚的经济回报及军事上的战略回报。众多美国议员显然没有耐心等待SSC的成功运转,也不愿意冒风险对SSC这种基础科研投入巨额经费。美国政府与得克萨斯州真正关心的似乎也并非SSC这一基础科学本身。得克萨斯州等竞选地一开始便把SSC看作一只夹满就业机会及政府资金的热狗并想以此来吸引工业资金与高科技人才。美国政府对SSC的支持也更多地源于政治、战略的需求。与SSC命运不同的是,美国另一大科学项目由NASA(美国航天航空局)主持的自由号空间站却得以保留。空间站与SSC的最大区别莫过于空间站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提供了75000个就业机会,SSC则只是一项基础科研项目,枪毙SSC也只会危及4000人的饭碗。这也难怪“没有人认为SSC不好,也没有人认为美国在当下多么需要SSC,大众也难以理解为何美国必须烧钱去寻找希格斯粒子” [8] 。的确,进行基础研究的SSC并不考虑使用的目的。“它生产的是普遍的知识和对自然及其规律的理解。这种普遍的知识提供了解答大量重要实用问题的方法,但是它不能给出任何一个问题的完全具体的答案。提供这种圆满的答案是应用研究的职责。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对他的工作的实际应用可能完全没有兴趣,但是,如果基础研究长期被忽视,工业研制的更大进展最终将停止。” [9]
第三,SSC的命运从始至终都摆在了政治的天平之上而非立足于科学本身。在竞选SSC建址的各州中,得克萨斯州、伊利诺伊州、科罗拉多州早在SSC计划提出之时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其主要原因在于SSC的到来将伴数以亿计的美元以及上千的就业机会,各州更可利用SSC来吸引高科技的工业投资及出色的科技人才,为此各州都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 Nature 杂志更是“幽默”地将SSC形容为香扑扑的热狗。 [10] 美国能源部声称,为了公平起见,在选址过程中将不考虑当地的经济背景,却允许各州上报愿意为SSC提供的配套设施作为竞选砝码。经过两次筛选之后,美国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公布了8处地址进行最终角逐。最终,得克萨斯州杀出重围,以伊利诺依州为代表的落选各州纷纷表示不满,猛烈抨击这完全是政治操控的结果。 [11] 的确,德州在议员中所占的高额比例极有可能影响SSC的选址结果。而在选址竞赛结束之后,落选各州对SSC表现出的热情大减。更不排除一些议员会针对SSC对得克萨斯州进行报复。再者,美国政府支持SSC在很大程度上出资美国全球战略需要的考虑。冷战期间,美国极其渴望在各个领域击败苏联,SSC亦成了大国争霸中的一块砝码。随着苏联解体,在战略上对SSC的需求骤减。美国一超的世界格局让SSC变得有点“可有可无”。在克林顿代替布什成为总统之后,美国政府的焦点更多在于如何平衡财政收支。参众两院议员成分结构的变动 [12] 也对SSC极为不利。可以说,在政治家的眼中科学的纯粹性是何等不堪一击,科学只是大国争霸的一个手段而已。
第四,SSC备受诟病的管理问题亦发人深省。美国政府与大型工业企业,大型军工企业的关系历来暧昧。企业追逐利益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为什么极力要求由工业、军事管理人才来管理SSC工程的建造。为此URA不得不“脱胎换骨”,被迫与Sverdrup与EG&G等大型公司进行合作。即使在对民族工业控制得相当紧的日本,由大量工业企业参与的科技项目的耗费显然要比欧洲的同等科技项目的耗费高得多。究其原因,无非是工业企业在工程建造过程中必然会将盈利作为最高目的,科学只是他们的一种手段。“SSC工程伊始Sverdrup与EG&G便分别跳过合法的工作人员考核程序,引入了70个、200个亲信。虽然前者的人员书目在后来减少到了10个,可到了1993年EG&G公司的‘亲属’已繁殖了三倍之多,再加上其他工业、军事企业相关人员的介入,1993年,SSC工作人员中的1/3来自‘外在’的公司企业。” [13] 这种杂烩式的结构方式无法保证一个巨型科技项目工作团队的整体素质。由于外来人员的“入侵”,一些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科技工程管理人员被迫出走。“原被委予重要职务的梯格那(Tigner)便是一名典型的受害者,最后无法接受职务降低的他离开了SSC。” [14]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美国能源部新部长欧列莉在承认了URA的失败之后,竟然试图引入更多的工业合同来接替URA!显然,美国能源部一开始为SSC工程承揽者所制定的标准是不符合科学精神的,引入大量的工业、军工部门只会使科学异化为私人牟利的手段而非目的。在一种用业务或生产标准来评价和检验工作的气氛中,SSC的研究工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地充分展开。在这里,科学家们失去了探索的自由,为了开拓科学知识前沿所必需的那种健康的、有生气研究环境荡然无存。“基础科学研究不应该置于一个不把研究工作看作头等要事的业务机构的管理之下。当投入业务竞争时,研究工作总会受到损害。” [15] 美国政府显然把布什博士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说过的话抛在了脑后。
最后,SSC也反映出很多国际合作方面的问题。大科学时代已经来临。科学再也不是在作坊中仅凭一己之力便可完成的天才之作。科学的每一点进步往往都免不了巨额的资金投入。在这样的科技背景之下,有时,单凭一个超级大国的财力无法支撑起一个浓缩人类梦想的伟大工程——尤其是基础学科工程。高效率的国际协作可以说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好途径之一。然而,遗憾的是,本质上SSC最终只是美国的独角戏。1994年在SSC的估计费用显示为44美元时,SSC对国际援助的要求并不十分强烈。许多美国政府官员对国际合作表现出了抵触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不愿意让他国分享SSC的科技成果。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让巨额的生产合同落入他国之手。可随着SSC估计费用的增长,美国政府必须承认单凭一己之力承担SSC的建造存在一定困难,于是美国能源部四处求援,然而美国似乎只乐意由外国生产一些技术含量十分有限的工程配件。换言之,对于外国来说,对SSC的投资很有可能将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而不难想象的是,外国“势力”的介入必然会使美国的工业、军工企业蒙受损失。美国的企业必会极力捍卫自身的“合法”经济利益,对外来“入侵”进行天然的排斥。可遗憾的是,对于已经变质的URA来说,这种干扰是很难排除的,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明明在国外生产某些部件显然要经济得多,可美国人却硬要把它们死锁在国内。无怪乎日本核能研究所负责人山崎(Toshimistu Yamazaki)说:“SSC实质上是一个美国工程而非国际工程。”
[16]
再者,美国希望从欧洲吸引资金显然是不切实际的。CERN主持的科研项目LHC
 与SSC是公开的竞争关系。这也使得一些国家认为,既然LHC更经济,赞助SSC不如赞助LHC。显然,在科学情报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美国与欧洲更多的只是科技竞争对手,而非科学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看,SSC与LHC乃是一种资源浪费的重复建设。再加上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际资金极其有限的吸引力,SSC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国际各界的有力援助,而最终,SSC不得不成为一个不能圆的梦。
与SSC是公开的竞争关系。这也使得一些国家认为,既然LHC更经济,赞助SSC不如赞助LHC。显然,在科学情报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重要的今天,美国与欧洲更多的只是科技竞争对手,而非科学合作伙伴。在很大程度上看,SSC与LHC乃是一种资源浪费的重复建设。再加上基础科学研究对国际资金极其有限的吸引力,SSC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国际各界的有力援助,而最终,SSC不得不成为一个不能圆的梦。
如今距SSC的夭折已有十多年了,高能物理界依然未取得决定性质的突破。在我们为SSC的早逝扼腕叹息并思考SSC之梦破灭的原因之余,我们还应牢记科学史家W.C.丹皮尔在评论罗马科学衰落时说的一句话:“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使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
 希望现代人不要重蹈罗马人的覆辙。
希望现代人不要重蹈罗马人的覆辙。
当下,中国已经跨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科技对于民族振兴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其中也蕴涵着某些危险要素:急功近利地片面发展应用科学,忽视基础科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应用科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其基础科学的发展却远远落后于欧洲。美国认识到:“一个在新的基础科学知识方面依靠别国的国家,其工业发展将是缓慢的,在世界贸易竞争中所处的地位是虚弱的,不管它的机械技术如何。”
 于是,在V.布什博士答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建议下,美国于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以领导美国的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如今,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美国都已经站在了科技的最前沿(尽管在SSC事件上,美国的政客们似乎已把美国发展基础科学的成功历史抛在了脑后)。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究竟该置基础科学研究于何处?在力图发展经济的今天,应用科学是长矛,基础科学是后盾,面对基础科学,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无法回避的。无论从中国当下的高校科研经费分布或是人才的储备状况来看,确有不够充分重视基础科学的嫌疑。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而言,经费和人才储备可谓两大命脉。现今中国,在工科面前,数、理、化等专业逐步变冷,为了培育科学之源,国家必须切实考虑如何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如何更好地在资金上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于是,在V.布什博士答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报告《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的建议下,美国于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以领导美国的基础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如今,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美国都已经站在了科技的最前沿(尽管在SSC事件上,美国的政客们似乎已把美国发展基础科学的成功历史抛在了脑后)。今天,中国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究竟该置基础科学研究于何处?在力图发展经济的今天,应用科学是长矛,基础科学是后盾,面对基础科学,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是无法回避的。无论从中国当下的高校科研经费分布或是人才的储备状况来看,确有不够充分重视基础科学的嫌疑。对于基础科学研究而言,经费和人才储备可谓两大命脉。现今中国,在工科面前,数、理、化等专业逐步变冷,为了培育科学之源,国家必须切实考虑如何让更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如何更好地在资金上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希望我们在SSC事件中能够看到,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的基础科学究竟该何去何从。切记:“基础研究导致新知识。它提供科学资本。它创造储备,知识的实际应用必须从中提取。”

1982年,以R.R.威尔逊为代表的高能物理学家向美国提议建造SSC,估计造价30亿美元。
1983年,美国能源部物理咨询委员会建议优先建造SSC。
1984年,URA管辖下的R&D小组开始设计SSC的建造方案。
1986年,R&D小组完成SSC设计。
1987年,里根总统批准建造SSC,估计造价44亿美元。
1987—1988年,SSC选址。最终,得克萨斯州埃利斯县从43处选址中胜出。SSC的部分部件进入制造阶段。
1989年,DOE公布的SSC造价提升至59亿美元,并预计于1998年竣工。
1990—1991年,SSC工程设计更新,DOE公布的造价为82.5亿美元(此时,有的非官方报价甚至高达117亿美元),竣工日期延至1999年。
1992年6月,众议院以232:181否决SSC工程。但在布什总统与参议院(62:32)的帮助下,SSC得到了1993年度的财政拨款。
1993年1月,工作人员开始挖掘长达54英里的SSC隧道,同时,打着缩减财政赤字大旗的克林顿当选为美国新一届总统。
1993年3月,克林顿要求将SSC工程的竣工日期推迟三年,延至2002年。由此,SSC的估计造价也增加了17亿美元。
1993年10月,DOE公布的SSC官方造价上升为110亿美元。
1993年10月,参议院力图保全SSC的要求(57∶42)被众议院以282∶143驳回SSC工程夭折。高能物理界为此表示无奈、震惊、失望。
作者简介: 古荒(1983— ),男,浙江金华人。南京大学哲学系2002级本科生,曾获江苏省三好学生荣誉,于2006年被推荐保送至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其间赴日本东京工业大学交流访学。现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科学技术哲学》专家组成员。
南哲感悟:
这篇文章记录着求学初心:文字虽有生涩,却饱含着学术热忱。这份涌动,每每回想,都是一种鞭策,亦是一份感动。彷徨之时,都能从中汲取力量。
这篇文章记录着师生情谊:该文从选题到成稿,都是在戴建平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从中,我所感恩的不仅是学术训练,更有人生启迪:“广大”易言,“精微”难致!
[1] Faye Flam,“The SSC:Radical Therapy for Physics,”in Science ,vol.254(October 11,1991),p.194.
[2] Faye Flam,“The SSC:Radical Therapy for Physics,”in Science ,vol.254(October 11,1991),p.195.
[3] Faye Flam,“The SSC:Radical Therapy for Physics,”in Science ,vol.254(October 11,1991),p.194-195.
[4] Faye Flam,“The SSC:Radical Therapy for Physics,”in Science ,vol.254(October 11,1991),p.194.
[5] Faye Flam,“Is There Life After the SSC?” Science ,vol.262(October 29,1993),p.644.
[6] James Trefill, The Edge of Unkown ,Houghton Miffin Company,1996,2,p.13.
[7] David P.Hamilton,“Ad Hoc Team Revives SSC Competition,” Science ,vol.252(June 21,1991),p.1610.
[8] Faye Flam,“Is There Life After the SSC?” Science ,vol.262(October 29,1993),p.645.
[9] V.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10] Steven Dickman,“Texas Amongst Early Contenders in the Race to Subsidize the SSC,” Nature ,vol.325(February 19,1987),p.654.
[11] 根据 Nature 杂志,最终参加角逐的8处选址的地质条件都不存有问题,竞争的关键在于地区资源的优劣(David Lindley ,“Supercollider Site Selection Moves into Final Round,” Nature ,vol.331(January 7,1988),p.2.)。但是,SSC的主要科学家温伯格说,最终地点选择得克萨斯州的埃利斯县是因为那里很适合SSC的“隧道挖掘”(温伯格:《终极理论之梦》,李泳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3年,第217页)。
[12] Jeffrey Mervis&Karen Fox,“A Senate Victory Would Turn The Tide After House Defeat,” Science ,vol.261(July 16,1993),p.288.
[13] David Ritson,“Demise of the Texas supercollider,” Nature ,vol.366(December 16,1993),p.608.
[14] David Ritson,“Demise of the Texas supercollider,” Nature ,vol.366(December 16,1993),p.608.
[15] V.布什:《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 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 ),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85页。
[16] David P.Hamilton,Japan's answer on the SSC:Maybe, Science ,vol.255(January 17,1992),p.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