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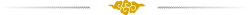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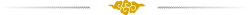
摘要: 休谟以彻底的经验论观点使得因果关系知识的可能性作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凸显出来,而他本人完全从习惯性联想的角度解决这一问题;康德对“客观有效性”做出了先验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又说明了如何从认识主体的角度赢获“客观性”。休谟与康德的回答都立足于认知主体的作用,所不同的是前者从心理学的认识发生论的角度,而后者则是从先验统觉的角度阐释主体的作用。因此对因果关系知识之可能性的追问最终指向了自我的主体性问题,而这正是近代欧洲认识论哲学中的核心问题。
关键词: 因果关系;必然性;客观有效性;习惯联想;先验统觉
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切科学知识都力图揭示认识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真正对人类究竟如何获得因果关系的知识这一重大哲学问题进行反思,正是近代自然科学兴起推动的结果。休谟第一个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解决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的发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的问题具有永恒的意义,对它的探讨深化了人们对自身认识活动的反思,虽然它也许并没有最终的答案。
人们的求知活动自始至终都在追问因果关系,获得新知识。然而把“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如何可能”作为一个并不自明的问题提出来却是对人类的认识活动做出深入反思的结果。这一问题显然让我们感觉无从下手,因此不妨按照休谟的意见把它细化成两个问题:
1. “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这件事是必然的呢?”
2. “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的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特定的结果呢?”
第一个问题不涉及具体的原因和结果,它只要求从对因果概念的分析中对“有开始的存在有一个原因”这个判断给出抽象的论证。但这实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象任何对象在这一刹那并不存在,在下一刹那却存在了,而无须对它加上一个各别的原因或产生原则的观念”,而这丝毫不会产生逻辑矛盾。第二个问题追问特定的原因和特定的结果,因此要求经验来论证。休谟贯彻了彻底的经验主义原则,一切知识仅从感觉而来,而可感知的性质决不会告诉我们对象中含有产生结果的能力,我只能经验到两个对象之间的恒常结合(constant conjunction);而因为首先我的理性不能证明“我们所没有经验过的例子类似于我们所经验过的例子”,因此,尽管我有一万次靠近火感到热的经验,我也不能断定火是热的原因;如果我不先论证“类似”这个前提而直接断定火是热的原因的话,那么实际上我又是把要证明的结论当成前提了。所以在休谟看来,不论是我们的理性还是经验都无法证明我们如何获得因果关系的知识,这确实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
理性通过“观念的关系”推理,经验通过“实际的事情”认识,而它们都不能直接论证因果关系。这在康德表现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区别。单纯逻辑地分析因果概念只是解释概念中已有的东西,虽然因为独立于时时流变着的经验而具有普遍有效性,却丝毫不能扩大知识;经验得来的综合判断使主项和谓项的联结有了新内容,但由于经验自身的不确定性,人们同样不能肯定这种联结是因果关系。我们看到这正是休谟的论证的另一种表述,在现有知识背景下不能确定地论证因果关系,这一点上康德是完全赞同休谟的。因果关系就其普遍有效性而言是“先天的”,就其扩大人类的知识而言是“综合的”,而这种“先天综合判断”就是一种既来自经验而又不依赖于经验的知识。在康德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知识。而“因果关系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成为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休谟还是康德,他们所关注的是因果关系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不是因果关系“是否可能”,因此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非本体论问题。由于休谟的怀疑主义态度,人们就认为他否认了事实上因果关系的存在,这实际是对休谟的误解。在《人性论》中休谟明确承认“自然的作用是独立于人类思想和推理以外的”,但作为一个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他不能理解人们是怎样超出经验之外在认识中肯定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他要求给出关于因果关系的知识具有正确性和客观有效性的证据。事实上,在数学和物理学迅猛发展的近代欧洲,任何人都难以否定因果关系的实存性,休谟的怀疑也只是表现出对人们的认识活动的反思。而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借数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回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则更鲜明地体现出这一反思的理性前提。我认为这也应是休谟的共识,只不过因为他认为自己研究的是关于人性的“精神科学”而对自然界中因果关系的实存性较少提及罢了。
我们所要探讨的是因果关系,但我们在前面已经使用了“因果关系”这个概念,却并没有深究它的意义。而要研究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如何可能,就必须首先弄清楚“因果关系”对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当我说起“因果关系”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一种从因到果的规律性变化。变化是一个时间过程,并且一般地在对象受到另一个对象的直接作用时才发生。因此休谟认为因果关系的观念涵摄着“接近关系”和“接续关系”的观念。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却是不确切的。首先,两个相距很远的对象发生因果联系是很经常的事,并且也不需要如休谟所说的那样,由一连串接近产生的原因联系起来的。我们同样可以认为相距较远的对象具有直接的作用。其次,虽然我们通常认为因先于果,但因果同时发生的事情也是存在的,这就不能简单地用接续关系来概括。在这一点上,康德的认识无疑要深刻得多。他强调因先于果“针对的是时间秩序,而不是时间过程;即使没有任何时间流逝,这种关系仍在”。这种在先实际是逻辑在先而不必然是时间在先。比如火炉是因,房间温暖是果,在过程上几乎是同时的;但如果移走火炉,房间立刻冷下来,这就表明在时间的秩序—逻辑上,火炉作为原因的确是在先的。那么如何解释在秩序上有先后的东西竟然会在过程中“同时”呢?康德借助数学上的无穷小理论,认为从因到果的变化是由一系列更小程度的变化产生出来的,任何一个变化所间隔的时间趋向于无限小,这就使整体的因果关系看起来是同时的。“知觉向时间中跟随其后的东西的每一过渡都是通过这一知觉的产生而对时间的规定,而由于时间总是、并且在其一切部分中都是某种量,则一个知觉作为一个量,其产生就是通过所有的等级(其中任何一个都不是最小的等级)而从零开始,一直达到它的确定的等级。”
 康德认为这就是变化的连续律。
康德认为这就是变化的连续律。
从康德的论证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实际上是把从因到果的变化界定为量的变化,否则这种连续律是不可理解的。康德认为变化只在于实体的状态而不是实体本身,变化必须以一个持久不变的实体为基础,否则如果变化的主体也在变化,那么就仍然需要原因来解释,这样必然会穷追到持久性的实体;至于“创造”,在康德看来只是陌生原因的结果,而决不能作为一个 事件 而存在。而在休谟那里,因果关系不能被理性证明恰恰主要在于质变的存在。休谟认为我们单凭观念间的关系决不能证明“自然的进程是永远一致地继续同一不变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今天发现的“因果关系”明天还适用,自然界一夜之间质的根本变化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说也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在休谟彻底的经验论面前,康德的这一结论无疑是独断的;把根据因果关系的变化统统归之于实体状态的量变的确给康德的理论论证提供了某些方便,却鲜明地表现出其自身理论的局限性。
一个对象可以和另一个对象接近,在时间秩序中在先,我们也承认两个对象之间不仅存在量的变化而且有质的根本变化,但我们仍不能说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乃是包含“必然联系”的观念,两个对象之间的变化只有是规律性的变化——具有必然性时,我们才说这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我们说经验都不能论证因果关系,正是因为在时时变化着的经验中找不到必然性的联系。显然,必然性才是因果关系的真正内涵,也是使因果关系成为一切科学知识之基石的决定性因素。因果关系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这里就转化为因果必然性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在人类的理解中,“必然性”是一个如此具有确定性的概念,以至于人们往往理解这一概念的含义却又无从表述。但是如果把我们讨论的范围限制在科学认识的领域,我们就可以把必然性的知识分解为两个更为基本的判断:
1. 我知道(Know)某些事情是必然的;
2. 我相信(Believe)某些事情是必然的。
我们对于必然的科学知识不仅具有知识,而且具有信念。在非科学认识的领域,这两点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无神论者可以“知道”在神学话语体系中,上帝是全善是必然的,但他不对此具有“信念”。而如果我说我“知道但不相信”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三角形内角和为180度是 必然 的,那显然是荒谬的。可以说,对任何一种科学必然性知识的承认都意味着对这种必然性的信念,虽然这两者并非一回事。
这里的区分是根据休谟的意见,然而这一事实显然是自有科学以来就有了,为什么直到休谟才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与哲学家们对必然性来源的理解有关。休谟之前的哲学家把认识中的必然性观念归结为客观事物自身真实的内在联系。既然我所知道的某些事物“必然如此”的观念是“客观有效”的,那么我同时也就没有了不相信的理由。所以如果必然性同时具有客观有效性,那么对必然性的信念就是自明的,不需要单独再去寻找信念的来源。但是到了休谟这里,情况发生了变化。休谟认为,客观事物真实的内在联系独立于人们的经验之外,而使人们发生必然性认识的只是从经验中发现的一些恒常结合,那么所谓“必然性”就不具有客观有效性,这样人们究竟是如何相信这样的“必然性”——对必然性的信念问题——就凸显成为休谟所着重关注的问题。
当我对一个观念具有信念时,我在这个观念上增添了什么新的东西了吗?休谟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信念实际上只来源于我们想象这个观念的“方式”。休谟把一切知觉(perception)分为印象(impression)和观念(idea)两类,其中印象由感觉直接产生,其强烈和活泼程度比与思维相联系的观念要强,而一切知识必然起源于印象。基于这种理论,休谟认为信念实际上来源于“习惯联想”,即如果心灵在某个印象的影响下经常关联到一个固定的观念,就产生了习惯性的心理倾向;此后这种转移就成为自然的心理过程,同时把起始印象的一部分活泼性转移给这个观念,使得这个观念具有了原来所不具有的强烈程度而从其他观念中突出出来,从而人们对这个观念就具有了“信念”。
休谟的解释从因果必然性不具有客观有效性出发,转而把它归之于完全主观的心理过程。“必然性是存在于心中,而不是存在于对象中的一种东西;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对它形成任何哪怕是极其渺茫的观念,如果它被看作是物体中的一种性质的话。”
 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通过严密的推理论证相信某种知识,但只有当论证符合我们的心理机制时,我们才会真正地“相信”。我认为休谟提示的这条思路有助于以经验科学的方式揭示人的认识思维过程,而这此前是被很多认识论哲学家所忽略的。但这种完全主观化的解释毕竟危及了科学知识确定性的基础,而休谟彻底的经验主义又使对“必然性不具有客观有效性”的论证无可辩驳,因此要重建科学知识之客观的基础,就必须重新阐释“客观有效性”的意义。
我们往往认为自己是通过严密的推理论证相信某种知识,但只有当论证符合我们的心理机制时,我们才会真正地“相信”。我认为休谟提示的这条思路有助于以经验科学的方式揭示人的认识思维过程,而这此前是被很多认识论哲学家所忽略的。但这种完全主观化的解释毕竟危及了科学知识确定性的基础,而休谟彻底的经验主义又使对“必然性不具有客观有效性”的论证无可辩驳,因此要重建科学知识之客观的基础,就必须重新阐释“客观有效性”的意义。
这正是康德解决因果必然性问题的思路。一方面,他把必然性诉诸客观有效性,这就使“知道”和“相信”的矛盾统一起来,而不必像休谟那样专门论证信念的来源;但另一方面,他又必须重新定义“客观有效性”,使之免于彻底经验主义的反驳。事实上,在他看来,休谟所批驳的正是认为单凭理性推理或经验归纳就可以宣称客观事物“必然如此”的独断论,这种“客观性”涉及的是物自身,根本不属于人类的认识范围。但康德认为,虽然物自身不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客观有效性”实是另有所指,而不是像休谟那样,一旦发现“必然性”所涉及的不是物自身内在的真实联系,就立刻退到主观的领域寻找必然性的来源。
直接地被我们的心灵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些杂多的表象,我们虽然没有任何理由把在这些表象中发现的联结——表象向我们呈现出来的相继关系——归之于物自体本身的实际状况,但这并不能说明这种联结仅仅是心理过程。如果我们承认本体界是与我们自身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对任何对象的经验,除非我们首先利用在我们自身之中先于经验的东西建构起对我们而言的客体、经验表象的对象,康德称之为“现象”。我们的认识活动并不直接面对本体界,而只有首先使作为对象的现象被给予出来,一切经验知识才有可能。所以如果认识的“因果必然性”具有“客观有效性”,那就意味着经验表象在时间中的前后相继能够被归结到表象的对象——现象本身杂多的联结。
在这里,处于相继领会中的东西被看作表象,而被给予我的现象,虽然不过是这些表象的总和,却被看作这些表象的对象,我从领会的这些表象中抽出的概念应当与该对象相符合。立刻就可以看出,由于知识和客体的一致即是真理,在这里所能探究的只是经验性真理的形式条件,而现象在与领会的表象的对立关系中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被表现为与表象不同的、诸表象的客体,即:该现象从属于某条使之与任何别的领会相区别的规则,这规则使杂多联结的一种方式成为必然的。在现象中包含有领会的这一必然规则之条件的那个东西,就是客体。

现象作为表象的对象,正是因为它是按照一种必然的规则联结诸表象。单纯就我们所领会到的表象而言,并没有一种必然的秩序联结我所经验到的杂多。比如,我可以任意按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的顺序领会房子的表象,而在杂多表象的相继中我并没有发现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只是我“主观的相继”;但我必然地经历落叶顺流而下这一前后相继的表象,而不可能使落叶在下游的表象先于在上游的表象。我把它归结为必然的因果联系,而其客观有效性就在于我首先按照一种必然的规则构造出现象,其中具有了“客观相继”,然后才经验到表象;而我所认识到的因果必然性实际上就是我们预先放到现象中去的那些规则,它独立于一切经验而又使杂多表象按必然的方式联结,在康德那里就是来源于认识主体的因果性先验范畴。
所以康德对必然性之客观有效性的证明实际以两条理论为基础:一是区分物自体和现象界,物自体不可知,现象作为客体是被主体建构起来的;二是主体按内在的先验规定构造对象,这正是必然性之客观有效性的基础。因果关系的知识作为一种先天综合判断,虽然其综合性要求知识从经验开始,但它的普遍必然性不能从杂多的经验表象中得来,而只能是先验的。既然如此,康德所论证的“客观有效性”就不是真正的客观性,而如果必然性来源于主体的先验规定,那么这种必然性不仍是主观之内的事情吗?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康德的确并没有真正解决休谟的问题,但应看到,休谟虽然谈的是真正的客观性,却只是从经验杂多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客观性,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因而无法发现必然性的客观基础;这在康德看来绝不是认识的真实状况。人们能够作为客体认识的东西必然是自己已经有所断定的东西,对象是被能动地构造出来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康德哲学体现出它的“革命性”特点。而第二条则涉及休谟和康德理论中主体的不同作用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单独加以讨论。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因果必然性的来源问题实际最终与认识主体的作用密不可分,这在休谟那里是“习惯性联想”,在康德那里是因果性的先验范畴。那么主体所起的作用究竟有何不同?为什么同是主观的活动,康德却只把前者看作只有主观的“必然性”而认为后者才是客观有效性的基础?
我认为,康德仅仅是从消极的意义上看到休谟的“习惯性联想”对科学知识之客观基础的消解。但这一理论积极的一面在于它开始试图用经验科学的方式理解人类的认知思维过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抽象思辨地考察人类的认识活动。休谟把这一点准确地概括为“哲学的关系”和“自然的关系”的区别。我们对因果关系的认识直接地是从观念间的比较、判断、推理得来的,我们认为是观念间“哲学的关系”引起了认识;但实际上对某个因果关系从不知到知,从不信到信,只有当那两个观念在我们的心中自然而然地被联系起来才是可能的。“因果关系虽然是涵摄着接近、接续和恒常结合的一种哲学的关系,可是只有当它是一个自然的关系、而在我们观念之间产生了一种结合的时候,我们才能对它进行推理,或是根据了它推得任何结论。”
 所以在休谟那里,主体的作用实际就是心理的作用。从“哲学”观点看,确实无法解释流变着的心理过程如何能“确证”对因果必然性的认识,但除了这一过程之外,人类又能从哪里找到“发生”必然性知识的基础呢?由于休谟从理性和经验中都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他更关注必然性知识如何“发生”的问题。在他看来,概念间的推理只是我们所意识到的认识的形式,而真正使我们产生因果必然性知识的只是习惯性推移的心理过程的作用。
所以在休谟那里,主体的作用实际就是心理的作用。从“哲学”观点看,确实无法解释流变着的心理过程如何能“确证”对因果必然性的认识,但除了这一过程之外,人类又能从哪里找到“发生”必然性知识的基础呢?由于休谟从理性和经验中都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他更关注必然性知识如何“发生”的问题。在他看来,概念间的推理只是我们所意识到的认识的形式,而真正使我们产生因果必然性知识的只是习惯性推移的心理过程的作用。
所以在休谟那里心理过程指的只是人类认识发生的自然机制,而康德所批判的“心理主义”则是单就其主观随意的心理因素而言的。前面提到,康德用对象的先验构造理论来解决必然性来源于主体却又具有客观有效性的矛盾,这种构造活动在一般的意义上就是“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康德承认一切知识必定从经验开始,杂多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感性直观才能被给予出来;但从杂多的恒常结合得出的联结只是“经验性”的,依赖于心理对诸表象的联想,因而是“主观的”。而要真正得出客观有效的必然性知识,就必须首先使分散的经验性表象成为“我的”对象,而这只有在“我思”作为纯粹知性的自发性行动把一个表象综合到另一个表象上时才能发生,先验自我意识(纯粹统觉)的统一性构成了对象客观统一性的基础。“只有通过我能够把被给予表象的杂多联结在一个意识中,我才有可能设想在这些表象本身中的意识的同一性,就是说,统觉的
分析的
统一只有在统觉的某一种
综合的
统一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
 我从红旗、血液、玫瑰花等中抽象分析出“红”这个观念来,但这只有在我首先从直观杂多中把红和其他表象综合出红旗、血液、玫瑰花作为对象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综合的统一对具体认识来说就是“本源性”的。知性把杂多表象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就其先验地构造认识的对象而言,这种认知主体能动性的活动被视为“客观的”。
我从红旗、血液、玫瑰花等中抽象分析出“红”这个观念来,但这只有在我首先从直观杂多中把红和其他表象综合出红旗、血液、玫瑰花作为对象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综合的统一对具体认识来说就是“本源性”的。知性把杂多表象纳入统觉的统一性之下,就其先验地构造认识的对象而言,这种认知主体能动性的活动被视为“客观的”。
显然,这种构造出来的对象实际只是“对象意识”,康德所谓具有客观有效性的因果必然性仍像休谟那样归于主体的作用。但先验统觉本源性的综合统一对主体能动作用的张扬,较之休谟对经验的被动接受而把必然性诉诸依赖习惯的心理联想,更符合人类认识活动的实际,这确实是对消极的“心理主义”的超越。但是,康德并没有认识到习惯性联想的认识发生学意义,这也给他的理论带来了问题。比如,统觉的统一活动中知性的先验范畴究竟如何运用到经验性直观的杂多上?康德以“先验想象力”对内感官杂多的综合作为中介。但接下去知性和感性直观对“先验想象力”分别又有什么关系?这就导致对中介的无限寻求,康德只能“中止判断”,掩盖了他理论上的缺陷。这里的关键在于他没有把人类的认识活动科学地理解为一个自然发生着的过程,我们完全可以追问先验的统一活动究竟是如何 自然地发生 的,从而把它看作认识的心理机制所表现出来的外在形式;这就说明康德并没有超越把心理过程看作认识发生机制的那种积极意义上的“习惯性联想”。而我认为既然心理作为认识发生的基础是认知科学的对象,哲学同样不应当忽视。
我们看到,在彻底经验论影响下,休谟和康德都无法真正弥合主客体分离所造成的鸿沟,也就不能达到真正的主客体统一,只能把因果必然性最终归之于主体的作用。这样主体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就成为他们解决因果关系认识问题的核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简单地说是康德超越了休谟还是休谟更具有永恒的意义,关键在于他们关注问题的方面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各有所长而又能相互补充,对后来的哲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黑格尔所说,真理是全体,是整个过程本身。在因果关系如何认识的问题上,这个判断对休谟和康德的理论无疑是适用的。
作者简介: 徐竹(1983— ),男,山东日照人。南京大学哲学系2001级本科生,清华大学—匹兹堡大学联合培养2005级科学技术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2010级师资博士后。牛津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当代英美知识论与行动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
南哲感悟: 感谢母系让我以这种方式重温大学时代的论文!惊奇地发现,直到今天我仍然在研究的话题,早在本科阶段的文章中就已经关心了。当然文章是不值一提了,今天专业本科生的论文,读来尤感后生可畏!我的大学生活印象最深的是今天回不去的浦口。工作之后回南大到访过仙林的系楼,颇有“物非人是”之感:尽管校园和大楼都是新的,但老师们的教诲谈笑一切如昨,恍若折叠了时空。感恩南哲四年的培养,无论是专业的还是生活的所获,都将受用一生。相信南哲的事业必定蒸蒸日上,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