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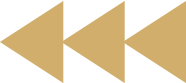
总的来讲,中世纪英国封建君主政体的势力比法国强大许多。诺曼王朝和金雀花王朝所建立的王权国家的权威和效率在欧洲是无可匹敌的。正是英国强大的中世纪君主政体使其得以在大陆上进行损害法国利益的领土冒险。百年战争期间,几任英王及其贵族跨越险阻重重的海上障碍,力图控制并占领法国大片地区。这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武功:岛国结构优势的充满进攻精神的象征。但是,西方最强悍的中世纪君主政体造就的却是最虚弱、最短命的绝对主义。当法国成为西欧最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的发祥地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英国都经历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日渐收缩的绝对主义统治。因此,在英国历史上,从中世纪向近代早期的转变时期,过去封建发展的许多最典型特征发生了深刻而激烈的逆转。尽管当地有各种所谓完整“连续性”的传说。诚然,一些最重要的中世纪模式被保留或沿袭下来,但正是传统力量与新生力量相互矛盾而又相互融合,才形成了文艺复兴时代岛国上特殊的政治断裂。(原书页码:113)
我们知道,最初的武力征服以及国家规模之小,决定了诺曼封建主义的早期行政集权化,并因之造就了这样一个贵族阶级,其人数非常之少,在地区内联合成一体,与大陆上截然不同,从未出现半独立的地方诸侯。遵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市镇从一开始就是王室领地的一部分,由此,它们仅仅享有商业上的特权,而得不到大陆公社的那种政治自治权:在中世纪,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实力上,它们均未强大到足以向其从属地位挑战的程度 [1] 。高级教士也从未占有过大片统一的封建飞地。因此,英国中世纪君主政体从未面临过法国、意大利、德意志封建统治者均遇到过的对一元化政府的反抗。其结果是,在整个中世纪政体内,王权与贵族代表权的同时集中化。事实上,这两个进程相辅相成,而非相互对立。在四分五裂的封建宗主权体系之内,超宗主权的君权只有在特殊的属臣会议的支撑下才得以维持。这种会议能够在个人依附等级制度之外,用投票方式给予王权以特殊的经济、政治支持。如前所述,中世纪等级会议永远不可能直接与君权相对立,反之,它们往往是其存在的先决条件。12世纪的欧洲再也找不出一个与英国金雀花王朝王权和行政部门相仿的模式。不过,出于同样的原因,君主个人权力产生之后,就有了封建统治阶级早熟的、具有非常一元化性质的集体性机构——国会。自13世纪以后,议会当然并不是英国独有的。中世纪英国国会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既是“独一份”又属“混合型” [2] 。换言之,它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国会,即其成员来自全国各地而非一些省份。而且在国会中,没有风行大陆的贵族、教士、市民三个等级的划分。自爱德华三世统治之时起,在英国国会中,骑士与市镇代表通常和贵族、主教们并肩而坐。上下两院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而且两院制并非等级划分的结果,基本上是贵族阶级内部的分工。集权化的君主政体带来了一体化的国会。(原书页码:114-115)
英国封建政体早期集权化还带来两个后果。在伦敦召开的历届一元化国会并未得到对财政细致入微的控制权和定期开会的权力,而这正是后来欧陆一些三级会议的特征所在。不过它们确保了对王室立法权具有一定的否决权。这在绝对主义时代变得非常重要:自爱德华一世以后,未经国会批准君主不得发布新法令已成为既成事实 [3] 。从结构上看,这种否决权与宏观上贵族阶级的迫切需要分不开。实际上,由于英国王室在地理上与技术上的集权化进程的起步都较欧陆早得多,因此,它并不急需法令创制权。换言之,它不能用地区分立主义或诸侯割据等危险为理由要求这种权力。出于同一原因,英国中世纪国王们的实际行政权通常比法国国王大得多,不过,他们从未得到过后来法国国王们享有的相对的立法自主权。英国封建主义第二个相对特征是君主与贵族在地方司法、行政事务中不同寻常的融合。在欧陆上,最为典型的是司法体制被分成王室裁判权和领主裁判权。而在英国,前封建主义民事法庭的继续存在为两者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主持各郡法庭的行政司法长官均由王室任命,而非世代相袭,但他们是从当地乡绅中遴选出来的,而非来自中央官僚机构;法院本身则保有原始的村民司法议会的痕迹,在这种议会中,农村公社的自由民保持着平等的关系。结果,在专业化王室司法机构中不可能发展完整的大法官(bailli)体系。贵族高级裁判权(haute justice)的全面发展也受到遏制。取而代之的是在各郡县出现了义务性的贵族半自制行政机构,这类机构在近代初期演化成治安官吏(the Justices of the Peace)体系。当然,在中世纪,与郡法院并行存在的、与之相抗衡的还有欧陆各地那种正统的封建采邑法院和大领主特权。(原书页码:116)
与此同时,与欧洲各国一样,中世纪的英国贵族是军国主义化的、掠夺成性的阶级:不过其海外扩张的规模和持续性的确比欧陆贵族更为突出。在中世纪末期,没有一个国家的封建贵族能像他们那样,整个阶级毫无顾忌地如此远离自己的领地。百年战争期间对法国的反复劫掠固然是其军国主义最显赫的武功,不过,14世纪的苏格兰和佛兰德、莱茵兰和那瓦尔、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都被英国远征军的铁蹄践踏过。在这一时期,从福斯湾(the Forth)到埃布罗河,到处都是英国骑士们的战斗足迹。这些远征的军事组织反映了封建主义货币化在各地的发展。在封建制度之末,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最后一支封建军队被征召于1385年,它为查理三世在苏格兰冲锋陷阵。百年战争的参战者基本上是受契约约束的军队,是由大领主依照货币契约为国王征召的,只听命于各自的长官。来自各郡的壮丁和外国雇佣军则成为辅助作战的力量。当时尚未出现专业化的常备军。远征军的规模都很小:向法国派出的部队人数从未超过1万名。率军反复劫掠华洛瓦王朝领土的贵族们与打家劫舍的匪徒并无二致,抢劫、敲诈和占领土地是其目标。功勋卓著的军官们大发战争横财。在这些战争中,英国军队一次次地击败了力图将其逐出欧陆的、人数多出数倍的法国军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与人们回顾时所臆想的不同,英国入侵者的战略优势并不在于其对海洋的控制。在中世纪,北海舰队刚刚足以运送兵源,而且大多是临时征募的商船,根本无法负担常规的海上巡逻任务。战船基本仍被局限在地中海内游弋,真正参加海战的是人力划桨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在这一时代,大西洋水域还从未发生过海上追逐战:典型的海战只能在浅水湾或河口[如斯吕伊(Sluys)或拉罗舍尔]一带进行。在这里,参战船只能相互连接以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在这一时代,根本不可能建立什么战略上的“制海权”。英吉利海峡两岸均无足够的防卫能力以抗击敌方的海上登陆。1386年,法国集结了整个战争过程中最大规模的陆军和船只,以期对英国发动全面入侵:在岛国的防卫计划中,竟未考虑到从海上拦截敌人,只寄希望于将英国舰队隐蔽在泰晤士河内以避开法军的锋芒,并诱敌深入陆地以歼灭之 [4] 。结果,这次入侵被取消了。不过,英国在战时毫无防卫能力抗击海上入侵这一弱点昭然若揭。因为在战争中,毁灭性的海上进攻与陆地骑兵(chevauchées)进攻同样令人生畏。法国和卡斯蒂利亚的舰队使用南方式单层大帆船,有着更大的机动性。从德文(Devon)到埃塞克斯,它们占领、洗劫或焚毁一系列英国著名港口。在战争中,除其他城市外,普利茅斯(Plymouth)、南安普敦(Southampton)、朴茨茅斯(Portsmouth)、刘易斯(Lewes)、黑斯廷斯(Hastings)、温切尔西(Winchelsea)、拉伊(Rye)、格雷夫森德(Gravesend)以及哈威奇(Harwich)均遭占领或被洗劫。(原书页码:117)
在百年战争大部分进程中,英国的优势并非来自海上霸主地位,因为在这样一场造成无数损失与废墟、旷日持久的陆战中占支配地位的本应当是法兰西 [5] 。这一优势正是来自英国封建君主政体更高程度的政治一体化和完整性。直到战争接近尾声之时,比起法国王权来,英国封建君主运用其固有财富、动员其贵族的行政能力一直强得多。法国君主正为布列塔尼和勃艮第心怀二意的属臣所骚扰,为最初未能铲除英国在居延的据点所削弱。反之,由一代代尚武的亲王亲自率军所取得的一场又一场的海外战争的胜利更强化了英国贵族的忠诚。只是到查理七世统治之下,法国封建政体在新的财政与军事基础上进行了内部改造之后,战局才发生了逆转。由于勃艮第同盟军的分道扬镳,在较短的时间内,英军被人数更多、装备更精良的法军赶出大陆。英国势力在法国终于垮台的可怕后果便是国内爆发了玫瑰战争。曾经捷报频传的王室一旦无力将大贵族聚合在一起,中世纪晚期的封建战争机器便掉转枪口,对准国内。野蛮的家臣和接受津贴的匪帮因大贵族之间的争斗而在全国各地肆虐。篡位者均想问鼎王室继承权。一场内战终于以在1485年博斯沃斯荒原(the field of Bosworth)战场上都铎王朝的建立而告结束。(原书页码:118)
亨利七世时代为英国“新君主政体”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在兰开斯特家族统治之末,各派贵族为各自的目标发展、扩大了国会,而约克家族的统治者们则在一片混乱之中努力强化王权。亨利七世尽管与兰开斯特家族有血缘关系,却基本上发展了约克家族的行政实践。在玫瑰战争之前,国会基本上是每年召开一次。在博斯沃斯战役后重建的第一个十年中,又恢复了每年召开国会的旧制。不过,一旦国内治安情况好转,都铎王朝得到巩固,亨利七世便抛弃了这一体制:从1497年至1509年,即其统治的最后12年,只召开过一次国会。集权化的王国政府的运转仅仅依靠国王的少数几个私人顾问和亲信,其首要目标是驯服前一时期残留下来的大领主势力。后者招致的祸患包括接受其津贴的匪帮和武装附庸、有系统地收买司法官员以及连续不断的私家战争。自然,比起约克时代来,此项措施的实行要坚决得多。通过运用星室法庭(the Star Chamber)强化了对贵族的最高特殊审判权,使原来仅具有政务法院性质的法庭变成了王室镇压叛乱和分裂活动的主要政治工具。北部和西部的地方动乱(在这些地区,边疆领主要求不经王室册封便拥有对被征服地区的权利)被授权恢复原状的特殊委员会所镇压。削弱了广泛的庇护权和半君主式的个人豁免权,禁止发放私人津贴。通过严格的选官制度和治安官的监督加强了王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粉碎了野心不死的篡位者们一次次的反叛。成立了一支精干的卫队以代替武装警察 [6] 。通过征地而大大扩展了王室领地。在亨利七世治下,此举将王室领地扩大了四倍之多,还最充分地利用了附属于财产的以及习惯上的封建义务。到亨利七世统治末期,王室总收入几乎增长了三倍,国库储备约有一二百万镑 [7] 。在16世纪初,都铎王朝为在英国建立绝对主义奠定了充满希望的基础,亨利八世继承的具有强大的行政权和丰盈的国库的国家。(原书页码:119)
在亨利八世统治的头20年间,都铎王朝在国内的稳固地位没有受到丝毫动摇。在沃尔西(Wolsey)执掌国政期间,在体制、立法方面无任何重大创新,至多就是红衣主教以教皇在英使节的身份将教权集于一身。这是史无前例的。国王及首相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海外事务上。本阶段的主要事件是在1512—1514年、1522—1525年两度进行了规模有限的对法战争。为支付欧陆战争的开支,两度召开短期国会势在必行 [8] 。因此,当沃尔西强行征税的企图遭到有产阶级反对之后,亨利八世只得废止此行。在英国,在王室政策的走向中尚未见到重大变化。只是到了1527—1528年间,由于国王决定与西班牙籍王后离婚引发婚变危机,以及随后与教皇在关于国内继承权问题上形成僵局才在顷刻之间改变了政治形势。为了消除教皇的干扰——因反对拟议之中的再婚计划,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煽动起各国王室之间的敌意——必须实行新的、激进的立法,也必须将全国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与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查理五世对抗。(原书页码:120)
因此,亨利八世在1529年召开了历史上会期最长的国会,以动员地主阶级支持他与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斗争,并支持政治上受英国国家控制的教会。起用被忽视已久的国会并非是亨利八世或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在体制上作出的让步(克伦威尔在1531年成为国王政治策划人):此举非但不是王权被削弱的证明,而且还是强化王权的一次新的努力。在宗教改革问题上,国会不仅同意将整个教会的控制权交给国王,从而极大地强化了王室的保护权和权威,还在克伦威尔的指导之下,通过取缔地方领主特权阶层的自治权(其中包括取消地方领主任命治安官的权力)而将边境地区拥有王室特许权和地区管辖权的贵族领地并入各郡,将威尔士从立法、行政上并入英格兰王国。更有意义的是,解散修道院并将其广阔的地产收归国有。1536年,政府的政治集权化和宗教改革的双重举措激发了北方蓄谋已久的可怕的暴乱——参觐圣恩运动(the Pilgrimage of Grace)。这是地方主义对强化王权国家的反抗。这是西欧当时非常典型的反抗形式 [9] 。暴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成立了常设北方委员会以控制特伦特河(the Trent)流域。同时,克伦威尔扩大并改组了中央官僚机构。他使王室秘书成为最高级的首相职位 [10] ,并使常规枢密院初具规模。在克伦威尔失宠后不久,枢密院在君主政体内作为行政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被正式确定下来,由此成为都铎王朝国家机器的核心。权力法案(Statute of Proclamations)显然是为将最高立法权交给君主而设计的,使它在将来摆脱了对国会的依赖,但它最终为下院所废除 [11] 。这一挫折当然不能阻止亨利八世对王公贵族进行血腥清洗,也不可能妨碍他建立告发和就地逮捕为手段的秘密警察系统。在他的统治下,国家镇压机器稳步发展:到亨利八世统治末期,一共通过了九个叛国法案 [12] 。一开始,亨利八世信心十足地依法利用国会作为达到其自身目的的必要手段。的确,利用这一手段从未给他带来不便。在沿袭下来的已将单一权力交给国会的英国封建政体框架内,正在酝酿着全国性的绝对主义,并不比欧洲大陆任何国家逊色。纵观亨利八世的一生,他在自己王国内实际能够行使的个人权力和其法国同时代人法兰西斯一世不相上下。(原书页码:121-122)
不过,新的都铎王朝君主政体是在有限的基础之上运作的。这使它与欧陆其他王朝有所不同:它没有一个坚实的军事结构。为了解构成16世纪和17世纪初绝对主义特殊形式的原因,必须超越拥有法律创制权的国会这一本地特产去考查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国际大背景。因为在都铎王朝国家政权建设捷报频传之时,英国在海外的地缘政治地位已经悄然经历了一场巨变。在兰开斯特时代,先进的英国君主政体使英国的对外实力可与任何欧陆国家相匹敌,甚至略胜一筹。但是在16世纪上半叶,西欧列强的势力均衡发生了彻底改变。前一时代英国侵略的对象——西班牙、法国均成为充满活力、咄咄逼人的王权国家,正在为争夺意大利而角逐。突然之间,英国被它们抛在后面。三个国家都在国内旗鼓相当地巩固了君主政体,但是,正是这一平衡的出现使当时两个大陆强国的天然优势第一次起了决定性作用。法国人口是英国的四至五倍,西班牙人口则两倍于英国,还不算它的美洲帝国和欧洲属地。除人口与经济优势之外,在永久性基地上发展现代化陆军以适应长期战争这一地缘需要更使它们如虎添翼。正规军、步兵团(tercios)的出现,雇佣骑兵、野战炮兵的运用,这一切导致新型王权军事机器的建立——这是中世纪所没有的规模大、耗资多的举措。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欧陆各君主政体来说,建立强大的军队是生存的先决条件。这种迫切性对于地处岛国的都铎王朝国家却并不尖锐。一方面,近代早期军队规模与军费开支的日益膨胀以及大批士兵隔海作战的运输、补给问题使英国曾经一度辉煌的中世纪跨海远征行动成为明日黄花。成为新的大陆强国的军事先决条件是以更广大的财力、人力资源为基础的,这使得英国不可能重演爱德华三世或亨利五世的武功。另一方面,这种陆地优势并未演化成相应的海上攻击能力。当时海战模式尚未出现重大变化,因此,从海上入侵英国的威胁并不十分严重。结果是,在英国,在向“新君主政体”转变的关键时期,都铎王朝国家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建立与法国、西班牙绝对主义相匹敌的军事机器。(原书页码:123)
不过,亨利八世及其同时代英国贵族从主观上尚不能跟上国际格局的变化。中世纪末期,前辈尚武的荣誉感和对大陆的野心仍然活生生地留在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记忆之中。极端谨小慎微的亨利七世重弹兰开斯特家族对法国王位要求的旧调,奋力阻止华洛瓦王朝吞并布列塔尼,积极筹划夺取卡斯蒂利亚的继承权。在伦敦条约签订后的20年间,指导英国对外政策的沃尔西俨然成为欧洲协调的仲裁人,其野心不亚于意大利教皇。而亨利八世则憧憬着成为德意志皇帝。这些宏大的抱负被后代历史学家们斥为荒唐的狂想。事实上,它们正反映了英国统治者的思想尚不能适应新的外交格局:英国在其中的地位已经大为削弱,尽管与此同时,其国内实力正在迅速增长。的确,举措失当的离婚案掩盖了其国际地位的丧失(尽管本土的领袖们对此毫无察觉)。不论是红衣主教还是国王,都未意识到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仍然居支配地位,教皇实际上只能屈从于查理五世施加的巨大压力。在法国、西班牙争夺对意大利控制权的角逐中,英国已经坐了冷板凳:由于它对罗马教廷毫无兴趣,因而在竞争中成了无能的旁观者。在这一意外发现的推动下,信仰的卫道士参加了宗教改革。不过,亨利八世的外交政策的不幸还不仅局限于这一灾难性的挫折。都铎王朝三次派遣远征军渡过海峡企图干涉华洛瓦—哈布斯堡王朝在法国北部的战争。在1512—1514年、1522—1525年、1543—1546年间派出参战的军队人数相当多,除从英国征募的士兵之外,还有大批雇佣军。1512年达3万人,1544年则达到4万人。调动军队却缺乏严肃的战略目标,也没有取得任何有意义的建树。英国闯入法、西斗争的结果是劳而无功。不过,亨利八世这些“盲目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喜怒无常君主的任性行为,尽管国王本人的决策的确有很强的随意性:它正与意味深长的历史空白相吻合,其时,英国君主政体失去了昔日在欧洲的军事地位,却还未意识到作为海上强国的前景正在向它招手。(原书页码:124)
不过它们也并非没有给英国本土带来一些重要结果。亨利八世最后一次重大举措是1543年与神圣罗马帝国结盟进攻法国。此举为英国王室的最终命运带来了致命的影响,对欧陆的军事干预举措失当,致使战费激增,最后竟高出亨利八世统治初年第一次对法战争十倍之多。为支付浩大的开支,国家不仅仅依靠强制性贷款和货币贬值,还向市场抛售刚刚从修道院没收来的地产——数额占王国土地的四分之一。由于战事一直拖延到亨利临终之时,由王室出售的教会地产也与日俱增。到和平终于恢复之时,这笔本已到手的横财已经丧失殆尽 [13] ,由此而丧失的是英国绝对主义为自己建立一个独立于国会征税制度之外的坚实经济基础的重大机遇。这一笔庞大财产的转移削弱了王室的长远利益,却极大地加强了乡绅阶级的力量。后者作为大地产的主要购买者,其人数及财力从此稳固增长。英国历史上最乏味、最微不足道的一场对外战争因之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尽管当时人们还未能察觉到它对英国社会内部力量均衡带来的影响。(原书页码:125)
亨利时代最后阶段的双重性的确预示着英国整个土地占有阶级的进化。因为1540年的军事冲突实际上是本世纪英国对欧陆进行的最后一场侵略战争。克雷西战役(Crécy)和阿让库尔战役(Agincourt)的幻影已经消失。不过,英国贵族传统职业的逐步消失使其阶级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没有迫在眉睫的经常性入侵造成的压力,英国贵族在文艺复兴时代远离现代化战争机器,不再受到海外敌对的封建阶级的直接威胁。而且,正如一切处于同一阶段的贵族一样,他们不愿意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王权建设——这也是建立大规模常备军的逻辑后果。在岛国孤立主义的环境中,贵族阶级非军事化的现象出现得非常早。1500年,每个英国贵族都拥有武器。到伊丽莎白时代,据统计,只有一半贵族有过战争经历 [14] 。到17世纪内战爆发前夕,只有少数贵族上过战场。贵族与中世纪社会秩序所规定的基本军事职能相分离。这一过程比欧陆要早得多,也自然会在地主阶级内部引起强烈反应。在特殊的海上环境中,无法用崇尚佩剑、抵御金钱诱惑来衡量堕落。这又使贵族转向商业活动的时代大大早于欧陆地主阶级。作为15世纪农业发达部门——牧羊农场的盛行,自然极大地加速了这一转变。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乡间纺织业自然为乡绅提供了投资渠道。引导14、15世纪封建地租演变为17世纪日益扩展的农村资本主义部门的经济道路已经畅通。一旦走上此路,英国贵族在法律上的特性就变得难以为继。(原书页码:126)
在中世纪,与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在原始的封臣、王侯封建世袭制遭到新兴货币化社会关系的冲击、古典封地系统解体后,英国也经历了用新头衔在贵族内部严格划分等级的时期。一旦各地区人身依附关系趋于总解体,对贵族阶级来说,设立名目更为繁多的新等级体系势在必行。在14、15世纪,英国贵族内部就已经设置了一系列新等级——公、侯、男、子等爵位,为确保长子继承权,还第一次从贵族内部分出了“显贵”等级
[15]
。这一阶层从此包括了贵族内部最强大、最富有的集团。与此同时,成立了纹章院,以确认乡绅的法律地位并确立资格审查程序。只有拥有纹章的家族才可跻身乡绅之列。在英国,一个在法律上区别于平民的非常严格的双层制贵族等级,本可以与其他地区一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但是,在都铎王朝时代,因土地买卖以及农业繁荣的刺激,整个贵族阶层日益强化的非军事化倾向和重商主义倾向使得不可能用法律制裁“堕落”
 。结果,严格的纹章标准根本不可能实施。由此,英国贵族阶层的独特性并不与拥有特权的显贵阶层相一致。显贵只是贵族内部拥有法律特权的阶层,而没有名分的乡绅和大贵族家庭中的幼子们控制了所谓平民院。在绝对主义时代,英国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几种特质是历史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其不寻常之处在于,背景是非军事化的,职业是商业化的,而所属阶级阶层则是平民。与这一阶级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仅仅拥有很小的官僚机构、有限的国库、不设常备军的国家机器。如前所述,都铎王朝与生俱来的倾向与欧陆的对手们惊人地相似(连亨利七世与路易十一、斐迪南二世与亨利八世、法兰西斯一世与马克西米利恩一世的个性都十分相像)。但是,其周围贵族的性质为它划定了发展的界限。(原书页码:127)
。结果,严格的纹章标准根本不可能实施。由此,英国贵族阶层的独特性并不与拥有特权的显贵阶层相一致。显贵只是贵族内部拥有法律特权的阶层,而没有名分的乡绅和大贵族家庭中的幼子们控制了所谓平民院。在绝对主义时代,英国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几种特质是历史性地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其不寻常之处在于,背景是非军事化的,职业是商业化的,而所属阶级阶层则是平民。与这一阶级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仅仅拥有很小的官僚机构、有限的国库、不设常备军的国家机器。如前所述,都铎王朝与生俱来的倾向与欧陆的对手们惊人地相似(连亨利七世与路易十一、斐迪南二世与亨利八世、法兰西斯一世与马克西米利恩一世的个性都十分相像)。但是,其周围贵族的性质为它划定了发展的界限。(原书页码:127)
亨利八世最后一次入侵法国的直接遗产是货币贬值、财政压力导致的乡间动乱的爆发、暂时性商业衰退、农村民众的极端贫困化。因此,在爱德华六世成年之前,都铎王朝国家经历了王权和政治稳定程度急速倒退的过程。可想而知,达官显贵为争夺对宫廷的控制权进行角逐。在此十年间,农民起义和宗教危机也时有发生。东部圣公会和西南部的农民起义均被从意大利、德意志招募来的雇佣军所镇压 [16] 。但是,不久之后,就在1551年,为减轻财政压力,解散了这批职业化的军队:镇压近300年内最后一次严重的农村暴动的,是最后一支可由国王在国内任意调遣的外国军队。在宗教气氛紧张、国内局势动荡的同时,在受到各自庇护的小贵族、官员、武装分子支持下,萨默塞特公爵(Somerset)和诺森伯兰公爵(Northumberland)之间的竞争引发了不为大众所知的枢密院内一次又一次的政变与反政变。一时间,都铎王朝国家的一元化结构似乎受到威胁。不过,年轻君主的早逝中止了国家土崩瓦解的危险。局势也不可能按法国贵族冲突的模式发展,因为相互竞争的大贵族都未能掌握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萨默塞特公爵和诺森伯兰公爵统治这一间奏曲的结局反而激化了地方宗教改革、强化了王朝对大贵族的权威。在转瞬即逝的玛丽统治时期,王朝对西班牙的依附以及昙花一现的天主教复辟几乎未能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任何痕迹。随着法国人重新征服加莱(Calais),英国丧失了在欧陆上最后的立足点。(原书页码:128)
在随后长达半个世纪的伊丽莎白统治期间,未进行任何激进的改革,国内原状完全被恢复并得到发展。随着建立驯顺的英国圣公会,宗教的钟摆摆向新教温和教派。从意识形态上讲,随着女王个人威望上升,王权被极大地加强了。但是,政体上的进步不算大。在女王统治前半期,枢密院一直处于国务大臣伯利(Burghley)长期而稳定的统治之下。沃辛厄姆(Walsingham)建立并发展了以镇压天主教活动为主旨的间谍警察网。与亨利八世时代相比,立法活动大为削弱 [17] 。大贵族间的党争主要表现在争夺宫廷荣誉头衔及职位的“走廊阴谋”中。在女王统治末期,对“英国的吉斯公爵”——埃塞克斯领导的最后一次大贵族武装暴动的镇压,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乡绅的政治影响和经济繁荣显然日益成为强化王权的绊脚石,尽管都铎王朝为同大贵族抗衡,曾扶植过这一阶层。主要迫于国外的紧急情况,在45年间召集了13次国会。如今,国会开始对政府政策表示出独立不羁的批评精神。在此世纪中,下院的规模极大地扩展了,议员人数从300人增加至460人,其中乡绅比例稳步增加,享有特权的自治城市的席位则为大地主或其保护人所占有 [18] 。在过去50年中,世俗对教会的控制和教义争端败坏了教会道德。这就使反对派的清教在相当一部分乡绅中逐渐传播开来。都铎王朝统治最后年代的特征之一就是桀骜不驯的国会再度反抗。国会在宗教问题上纠缠不休,在财政问题上设置重重障碍,迫使伊丽莎白宁可出售王室地产也要降低对国会的依赖。与王朝的政治威望和行政权力相比,集权化的国家官僚机器依然微不足道。最重要的是,它没有酝酿陆战的温床——推动欧陆绝对主义发展的动力。(原书页码:129)
当然,文艺复兴时代的战争并非没有影响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从性质上看,亨利八世的军队依然十分混杂,而且是临时七拼八凑而成的。在国内征召的旧式贵族家丁与从海外招募的佛兰芒、勃艮第、意大利、德意志雇佣军混杂在一起 [19] 。在阿尔瓦和法尔内斯(Farnese,1545—1592年,尼德兰摄政——译者注)时代,伊丽莎白王朝经常面临外敌入侵的现实威胁,只好经常不合法地起用英国传统民兵的旧制,以征募足够的兵力赴海外作战。按理说,民兵只用于在国内维持治安。一万二千多名民兵经特殊训练后多用于国防。余者——基本是从流浪人口中拼凑起来的——则被女王派往海外。这一体系的发展并未导致职业化常备军的出现,但的确为伊丽莎白政府无数的海外征伐提供了小小的兵源。身负征兵重任的各郡总兵变得日益重要,团队建制也逐渐发展,火枪取代了当地人们所钟爱的长弓 [20] 。民兵部队通常与苏格兰或德意志雇佣兵相混杂。派往海外的军队人数从未超过2万,这仅仅是亨利统治后期远征军人数的一半。绝大多数是小股部队,在尼德兰或诺曼底作战时总是拖泥带水。战费与其功用相比,惊人地高,根本不可能再在此方向取得任何进展 [21] 。英国绝对主义在军事上的无能仍然妨碍着其在欧陆实现任何扩张目标。伊丽莎白时代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属于消极防御型:阻止西班牙重新征服联合行省,阻止法国在低地国家立足,阻止联盟在法国取得成功。就此而言,尽管英国军队在欧洲犬牙交错的战争中的作用极其次要,但这些有限的目标都达到了。英国在另一战场上取得了对西班牙的决定性胜利:它打败了无敌舰队。不过,它仍无法在陆地上利用这一胜利。由于缺乏积极的大陆战略,该世纪最后10年的分头出击既浪费金钱,又毫无意义。1588年后,拖延日久的对西班牙作战使英国王室消耗了巨额资财,却没有获得任何领土或财富。(原书页码:130)
不过,在这一时期,英国绝对主义还是建立了一项重大的武功。伊丽莎白时代的扩张主义无力与欧陆主要王朝国家进行正面对抗,就将大批军队投入对爱尔兰贫穷、原始的氏族社会的征战之中。到16世纪末期,这个凯尔特人的岛屿还一直保留着西欧,乃至整个欧陆上最古朴的社会结构。用培根的话说,这些“欧洲最后的儿女” [22] 被置于罗马世界之外,日耳曼人的征服未曾触动它的一根毫毛,连北欧海盗在此地也仅仅一掠而过。虽然在6世纪它受到了基督教的驯化,但是,其原始氏族制度却不同寻常地延续下来,没有出现政治上的集中。在这遥远的信仰前哨区,教会干脆放弃了控制社区修道院组织的宗教权力,宁愿顺应当地的社会秩序。世袭酋长统治着聚居在较大的血缘单位中的自由农民。乡间是一派牧歌式的田园生活。没有集权化的君主政体,根本不存在什么市镇,尽管在7世纪到9世纪,即其他地区正处在黑暗时代最黑暗的阶段时,在修道院中出现了学术繁荣。在9世纪至10世纪,北欧人的反复入侵打乱了岛上的文化生活和氏族地区主义。北欧人的飞地成为爱尔兰第一批市镇。在外来压力之下,11世纪初,岛内终于产生了中央王权以抵御北欧海盗入侵的威胁。动荡不定的爱尔兰最高王权国家迅速崩溃,形成一个个战争联盟,但仍抵御不了装备更为先进的入侵者。12世纪后期,英国金雀花王朝从教皇那里取得了在爱尔兰的“宗主权”。盎格鲁—诺曼贵族跨越海峡,对该岛实行征服和殖民化。在随后100年中,拥有重甲骑兵和坚固防御堡垒的英国封建主义逐渐实现了对这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正式控制(极北地区除外)。不过,盎格鲁—诺曼定居点的密度一直不足以巩固其军事成就。在中世纪后期,由于英国君主和贵族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对法作战,爱尔兰氏族社会开始稳步地收复失地。英国的势力范围收缩到都柏林周围面积很小的佩尔地区(Pale)。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地方诸侯的“自由地”。不过,这些被复兴的凯尔特酋长领地环绕的自由地已经逐步盖尔化了。到此时,凯尔特酋长领地已经再次覆盖了该岛大部地区。 [23] (原书页码:131-132)
近代早期,恢复了元气的都铎王朝国家出现后,进行了第一次为恢复、强化英国对爱尔兰宗主权长达一个世纪的努力。1494—1496年间,亨利七世派遣其助手波伊宁斯(Poynings)赴爱尔兰,以打破当地贵族议会的自主权。但与盖尔人名门望族频频联姻的基尔代尔王朝(Kildare dynasty)仍然掌握着封建统治权,头衔是“副君”。在亨利八世时代,克伦威尔政府开始在佩尔引入更正规的官僚统治机构。1534年,基尔代尔被废黜,其子发动的暴动也被粉碎。1540年,亨利八世接受了爱尔兰国王这一新头衔,尽管此时他已与最初授英国君主以爱尔兰宗主权的教皇决裂。不过,实际上,岛屿的大部地区仍然处于都铎王朝控制之外——被“老爱尔兰”的酋长们或与之有亲属关系的“老英格兰”诸侯所控制。在英国宗教改革方兴未艾之时,他们仍然对天主教忠贞不渝。到伊丽莎白统治时代,在佩尔之外只组成了两个县。随着王朝力图将其权威强加于此岛并通过建立“新英格兰”新教殖民种植园来重新安排这个国家,便爆发了猛烈的起义——1559—1566年阿尔斯特(Ulster)起义、1569—1572年芒斯特(Munster)起义、1579—1583年伦斯特(Leinster)—芒斯特起义。在英国与西班牙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期间,在北爱尔兰氏族首领奥尼尔(O'Neill)领导下,终于在1595年爆发了波及全岛的反抗都铎王朝压迫的起义。起义者向教皇和西班牙求援。伊丽莎白政权决定彻底解决爱尔兰问题,因此调动了大批军队以重新占领此岛,以期使这个国家一劳永逸地归化英国国教。爱尔兰人采用游击战术,英国人则以残酷无情的灭绝政策反击 [24] 。到英国司令蒙乔里(Mountjoy)彻底镇压所有反抗之时,战争已经拖延了9年。到伊丽莎白去世时,爱尔兰已经被武力吞并了。(原书页码:133)
不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竟是都铎王朝军队在陆地上取得的独一无二的胜利。历尽艰辛才战胜了一个处在前封建社会的敌人,这在其他地区均不可能重演。英国土地所有者阶级及其整个国家则是在另一个领域使其性质获得了时代性、决定性的发展——在16世纪,逐渐地向海军装备和海上扩张方向发展。到1500年,流行于地中海的长形人力桨单层甲板大帆船(不同于圆形商用小帆船)开始在北方水域中被配备火器的大型战舰所取代 [25] 。在新型战船上,帆取代了桨,士兵让位于火炮,于1494年在朴茨茅斯修建了英国第一座干船坞的亨利七世就造出了两艘这样的战船。不过,亨利八世为英国海军力量带来了“具有实质意义的、空前的扩展” [26] 。在他即位的头5年,就为海军购买、建造了24艘战船,使海军规模增加了三倍。到他统治末期,英国王室已经拥有53艘舰只,1546年正式成立了海军部。在这一阶段,拥有头重脚轻的堡垒并装备了新型大炮的大帆船仍是粗陋的作战工具。海战基本上依旧是军队之间在水面上短兵相接的格斗。在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最后一场战争中,法国战船在进攻索伦特海峡(Solent)时仍然拥有主动权。爱德华六世统治时代,在卡瑟姆(Chatham)修建了新船坞。不过,在随后的几十年中,随着快速大帆船问世,西班牙、葡萄牙的舰船设计水平远远高于英国,都铎王朝的海上力量相形见绌。自1579年以后,在霍金斯(Hawkins)主持海军部时期,皇家海军飞速扩展并加紧现代化。装备着远程火炮的低吊索快帆船的出现使战船变成了运行灵活的炮台,旨在于追击战中在最远射程上击沉敌舰。与西班牙进行的海战刚刚拉开帷幕,就显示出这些新战船的优良技术性能。而英国海盗则早已在美因河(the Main)上用此类战船进行了反复演练。“到1588年,伊丽莎白一世已经成为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海上女皇。” [27] 在英国新式战船的打击下,无敌舰队灰飞烟灭。岛国的安全保住了,未来帝国的基础奠定了。(原书页码:134)
英国新近赢得的海上霸权最终带来了双重结果。海战取代陆战导致军事行动的分工和专业化,万无一失地将战争暴力推向海外(当然,武装舰船成为浮动监狱,苦役劳工受到惨无人道的剥削)。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对海事关心的第一焦点是商业发展,因为陆军永远只能是目标单一的建制,而海军的性质则决定了它具有双重性,不仅可以作战,也可以从事贸易 [28] 。事实上,在整个16世纪,英国舰队的大部分战船仍是在商船上安装大炮临时改装而成的,战后,仍然可以改装回商船。国家对商船设计的奖掖政策就更加促成了这种双重性。这样,海军不仅是英国国家暴力机器的“上等”工具,而且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对统治阶级本质上的变化造成了深刻影响 [29] 。虽然每个单位造价很高 [30] ,但是,用于海军建造、维修的总费用远远低于常备军的消耗。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十几年中,两个军种军费开支的比例是1∶3,而随后几个世纪中,海军的收获却高出几倍:不列颠殖民帝国就是这些成果之集大成。海军至上的全部成果还有待时日,但在16世纪已初见端倪。因此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发展不是与各口岸、郡县的商业资本相抗衡,而是与之相协调。(原书页码:135)
1603年,都铎王朝绝嗣,斯图亚特王朝登基,为君主政体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因为随着詹姆士一世继承大统,苏格兰第一次因个人关系的纽带而与英格兰合并。如今,两个截然不同的政体合并在一顶王冠之下。最初,苏格兰对于英国发展模式的影响微乎其微,其主要原因正是两个社会结构历史上的差异。不过,从长远来看,它对于英国绝对主义命运至关重要。与爱尔兰一样,苏格兰也曾是一个处于罗马帝国控制之外的凯尔特人堡垒。在黑暗时代吸收了爱尔兰、德意志、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混合成分后,11世纪,五花八门的氏族臣服于一个中央王权,除北部外,王权的司法权遍及全国。在中世纪全盛时期,盎格鲁—诺曼封建主义浪潮对本地政治、社会体系也进行了改造。不过,在爱尔兰,它采取了不稳定的军事征服方式,并很快受到凯尔特人回潮的冲击。在苏格兰,土著的坎莫尔王朝(Canmore dynasty)却引入了英国的移民和体制,鼓励臣民与南方贵族通婚,仿效边界另一侧更为先进的王国模式:城堡、郡长、国王内侍和大法官。其结果是苏格兰社会更深刻的封建化。自动推行“诺曼化”进程消除了国内旧有的种族分界线,形成了以语言、社会区分的新界限。在低地,除实行采邑制和领地制外,开始使用英语。盖尔语则仍为高地地区游牧部落所使用。与爱尔兰的情况有所不同,纯凯尔特族被彻底压缩成少数民族,仅固守着西北一隅。在中世纪后期,总的来讲,苏格兰王朝未能在其领地上巩固其统治。低地与高地政治模式之间的相互感染,导致山地凯尔特氏族首领的半领主化和平原苏格兰封建组织氏族化的现象 [31] 。更重要的是,与英国不断的边界战争反复冲击着王权国家。在14、15世纪的无政府状态下,在无休止的边境动乱中,贵族们攫取了郡长职位的世袭权,建立了私人司法权,显贵从王朝手中夺得了各省的最高权力,附庸的血缘网在两者的庇护下得到充分发展。(原书页码:136)
即位的斯图亚特王朝为不稳定的少数民族动乱和摄政政府所困扰,在随后150年中,在遏制国内流行的动乱方面,没有任何建树。与此同时,苏格兰与法国的外交联盟日益巩固,并将其视为抵抗英国压力的盾牌。在16世纪中叶,吉斯摄政王推行了彻头彻尾的法国人统治,激起了贵族和平民的仇外情绪,为地方宗教改革提供了强大动力:城镇、地主和贵族起而反抗法国人政府。1560年,英国海军切断了法国人政府与大陆的联络线,以此保证了新教在苏格兰取得胜利。宗教上的改宗使苏格兰与爱尔兰分离,却几乎未能改变国家的政治局面。在随后一个世纪中,唯一忠实于天主教信仰的盖尔人高地变得更加桀骜不驯,也更加动荡。带玻璃窗的乡间宅第成为南方都铎时代风光的新景色,而在边境及低地则继续修建壁垒森严的城堡。在整个王国内风行私家军队的械斗。只是到詹姆士六世即位之时,即从1587年起,苏格兰的君主政体才真正改变了处境。詹姆士六世运用刚柔相济的手腕,使枢密院变得强大有力,在庇护显贵的同时挑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册封了新贵族,逐渐为教会引入主教制,增加了地方议会中贵族和市民代表成分,通过建立受到严格指导的委员会(the Lords of Articles,贵族法制院)制约地方议会,安定了边防 [32] 。到17世纪初,虽然苏格兰处处是一派万象更新的景象,不过其社会政治结构依然与同时代的英国大相径庭。人烟稀少——人口只有75万,市镇又小又少,畜牧业仍是就业人数最多的行当。最大的贵族家族是那些地方诸侯,其地位是英国人闻所未闻的——汉密尔顿(Hamilton)、亨特利(Huntly)、阿盖尔(Argyll)、安格斯(Angus)等家族控制着国内大片土地,充分行使着王公般的权力,拥有军事扈从和依附性佃农。在小贵族阶层中盛行封建庄园领主权。由国王派出的治安官已不起作用。人数众多的小地主阶层沉溺于小规模武装冲突。在14世纪已从农奴制下解放出来的绝望的农民阶级从未发动过一场像样的起义。经济贫困、文化孤立使苏格兰社会生活保持了浓重的中世纪色彩。苏格兰国家并不比博斯沃斯战役后的英格兰王朝稳定。(原书页码:137)
移植到英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仍然在追求绝对王权的理想。在西欧,这一理想业已变成各国王室的规范模式。詹姆士一直生活在“诸侯即王法、国会微不足道”的国家中。如今他发现,在新王国中,大贵族的武功已成为明日黄花,但他没看到,国会乃是贵族权力中心。一时间,英国社会远为先进的特点似乎使国王对它的统治易如反掌。詹姆士一世的王朝既看不起又不理解国会,也不想缓和英国乡绅中日益发展的对立情绪。宫廷穷奢极欲,同时采纳了无所作为的外交政策,其基础是重新向西班牙靠拢,对于人数众多的土地所有者阶级来说,这两者都相当不得人心。与王室宣传的君权神授理论相呼应的是宗教中高教会派(High Church)的仪式主义。君主的司法特权践踏了习惯法。出售专卖权和官职被当作对付国会拒绝批准赋税的手段。王权的这些举措在英格兰颇遭非议,在苏格兰、爱尔兰却未遇到任何反抗。在这两个地区,地方贵族受到国王精心设计的保护伞的引诱,低地的大种植园主在北爱尔兰进行殖民,以确保新教的统治地位。不过,到其统治末期,斯图亚特王朝的政治地位在中央王国已经是岌岌可危。当它仍在努力追求在欧陆大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的制度目标时,英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已经与王朝相分离。(原书页码:138)
在解散修道院一个世纪以后,在英国人口翻了一番的同时,贵族和乡绅的数量则增加了两倍。他们在国有财产中所占份额还不止增加了两倍。在17世纪初,增长尤为迅猛。当时租金增长率超过物价上涨指数,土地所有者阶层从中获益匪浅:在153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乡绅阶层的净收入大约增加了三倍 [33] 。地主、自耕农、农业工人三位一体的体系——未来英国农村结构的雏形——已经在英国乡间较为富庶的地区初露端倪。与此同时,伦敦出现了空前的贸易与制造业的集中,在查理一世统治后期,其规模比亨利八世时代高出七至八倍。到17世纪30年代,伦敦成为欧洲国家中最大的资本化都市。到该世纪末,英国已经大致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 [34] 。除尼德兰之外,英国农业与商业资本的发展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远为迅速。大批英国贵族——大贵族和乡绅——都顺利地适应了这一变化。因此,封建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再也不能适应作为国家主要依靠对象的那个阶级的社会属性,而且,并没有来自下面的危险迫使君主政体与乡绅加强彼此间的联系。由于没有建立常备军的必要,英国的税收水平一直不算太高,在17世纪初,也许只有法国税收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35] ,落在农民肩上的负担就更轻了。与此同时,教区贫民还能领到由公共基金会发放的一小笔慈善基金。结果是,在16世纪农村动乱之后,乡间出现了相对的社会稳定。此外,比起其他国家的农民来,英国农民不仅受到了轻徭薄赋的待遇,其内部分化也更为剧烈。随着乡村商业刺激日益加强,这一分化使贵族和乡绅有可能放弃领地经营而转向充满活力、有利可图的租地经营。其结果是在农村大众之外,相对富足的自耕农(富农)阶层和人数众多的农业工人阶层得到巩固。对贵族来讲,乡间的局面相对比较保险,他们无须担心发生起义,因此也没有必要拥护国家建立强大的中央强制机器。低税收不仅促成农村稳定,而且由于无须扩展财政体制,也就遏制了庞大官僚阶层的出现。由于贵族自中世纪起便承担了地方行政职能,君主政体就一直不能拥有任何职业化的地方机构。因此,斯图亚特王朝对于发达的绝对主义的追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阻碍。(原书页码:139)
1625年,查理一世开始谨慎地着手建立更发达的绝对主义,不过此举相当愚蠢。因为他所采用的手段根本不可能成功。前一届宫廷的各种余辉也于事无补:詹姆士一世的腐败与查理一世的苛政结合起来——从白金汉(Buckingham)到劳德的统治,激起了广大乡绅的愤怒 [36] 。从查理一世即位之初,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就削弱了王室的地位。英国未参与三十年战争,却又毫无来由地对法国开战并被打得一败涂地。这些全都是白金汉偶发奇想的结果。一旦这一插曲结束,王朝政策的大方向就变得相对稳定。国会被坚决地解散了,因为它曾激烈地否定战争举措、抨击应为之负责的大臣。在随后10年的个人统治时期,王朝力图再度向大贵族靠拢,其手段是授予贵族特权、恢复曾经实行过的贵族血缘爵位世袭制,这是因为在英国不会再出现大贵族军阀了。在城市中,为大城市商人保留了专卖权益,这些大商人构成传统的城市贵族。大批乡绅和新兴商业资本被排斥于王室视线之外。在查理一世统治之下的教会整顿过程中,这种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恢复了教士的纪律和道德规范,却加深了本堂神甫与乡绅之间的宗教隔膜。不过,斯图亚特王朝绝对主义的成就主要局限在国家的思想及宗教领域。在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统治之下,开始重新灌输君权神授理论、强调教会仪式。但是,经济/官僚机构仍然受制于尖锐的财政困难而不能扩展。国会控制了征税权。从詹姆士一世统治之初,它就一直对越过国会征税的企图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在苏格兰,王朝可以随心所欲地增加赋税,对市镇尤其如此,因为等级会议没有就征税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传统。在爱尔兰,严酷的斯特拉福德(Strafford)对从伊丽莎白征服时代起移入的外来乡绅征收土地税和岁入,使这个岛屿第一次成为国家有用的收入来源 [37] 。但是,在英格兰本土,即主要问题所在地却无此类良方。早年都铎王朝对王室领地的恣意挥霍削弱了查理一世的能力,他再次动用了各种可能的封建主义、新封建主义手段寻找税收来源以支撑不受国会制约的扩大了的国家机器:恢复对佃户幼年子女及财产的监护权、对骑士课以罚金、使用王室食品征发权、扩大专卖权种类、扩大荣衔授受范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年间,卖官鬻爵第一次成为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30%—40%。同时,对官位持有者的酬劳在国家开支中也占有很大份额 [38] 。所有这些手段均未能奏效:只是引起了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憎恶,清教主义对新王室和教会的反感在大部分土地所有者中引起共鸣。值得指出的是,查理一世建立强大财政基础的最后举措是力图推广英国一种传统的国防税,即由港口支付的用于维持海军的船费。几年后,由于从中得不到好处的地方治安官拒绝继续推行,这一举措也就夭折了。(原书页码:140-141)
对于这一计划的选择结果暴露出英国版的凡尔赛体制缺乏一些基本的要素。欧陆绝对主义是以军队为基础的。具有奇特讽刺意义的是,只要岛国绝对主义无须征发军队,就只能依赖其微薄的岁入存活。只有国会才能够提供征召军队的财源,而且,一旦召开国会,斯图亚特王朝的权威肯定会被瓦解。不过,出于同样的历史原因,英国日益高涨的对君主政体的政治反抗也不具备举行武装起义的现成的暴动工具。只要不召开国会,乡绅反对派甚至找不到合法攻击国王个人统治的舞台。终于,对立双方的僵局在苏格兰被打破了。1638年,查理一世的教权主义因采取重新占有世俗化的教会土地和什一税的举措,已经威胁到苏格兰贵族,其推行英国圣公会圣餐仪式的举措终于激起了宗教暴动。苏格兰等级会议各阶层联合进行抵制。而且他们的反抗盟约获得直接的物质力量。因为在苏格兰,贵族和乡绅并未实行非军事化。在斯图亚特王朝发祥地的古老社会结构中,依然保留着中世纪后期政体的战争契约关系。因此,盟约能够在几个月内征召到一支强大的部队投入战场,与查理一世一决雌雄。大领主与地主阶层召集其武装佃户,市民们提供了资金,三十年战争后退伍的雇佣兵中则提供了职业军官。受到贵族支持的军队将指挥权交给了从瑞典军队退役的一位将军 [39] 。英国王朝根本不可能召集起与之相匹敌的军队。因此,事实上有一个潜在的逻辑,正是1640年苏格兰进攻最终结束了查理一世的个人统治。英国绝对主义为其结构缺陷付出了代价。它偏离了封建时代末期国家的通则,而这只是从反面证明了这些通则的必要。国王在行将灭亡之际召开国会以解决苏格兰战败的危机。国会宣布回归更为纯正的立宪框架以否定由斯图亚特王朝取得的任何成果。一年以后,爱尔兰爆发了天主教起义 [40] 。维系斯图亚特王朝和平的第二条脆弱的纽带断裂了。为镇压爱尔兰起义必须征召军队,而对英国军队控制权的争夺使国会和国王走向内战。英国绝对主义被其边陲的贵族地方主义和氏族动乱引入危机:它们本是支持它的历史性因素。而商业化的乡绅、资本主义化的城市、平民化的手工业者和自耕农则在中心置它于死地:它们是超越绝对主义的推动力。英国绝对主义在进入成熟期之前就被资产阶级革命腰斩了。(原书页码:142)
[1] Weber在分析英国中世纪市镇时指出,除其他特点之外,突出的一点是,它们从未经历过大陆市镇的那种行会或城市革命: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III,pp.1276—1281。伦敦1263—1265年间曾出现过短暂的起义盟誓,见Gwyn Williams; Mediaeval London. From Commune to Capital, London 1963,pp.219—235,不过,这仅仅是发生在贵族暴动中的例外的插曲。(原书页码:114)
[2] 英国国会最初的司法职能便非同一般;作为最高法庭,它可以受理陈情书,在13世纪,它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处理这类文件。当时,王室官吏在议会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至于中世纪国会的起源与进化,见G.O.Sayles,The Mediaeval Foundations of England,pp.448—457;G.A.Holmes, The Later Middle Ages, London 1962,pp.83—88。(原书页码:115)
[3] 关于这一界限的意义,参见J.P.Cooper,“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ontinental Governments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in J.J.Bromley and E.H.Kossmann(ed.),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 London 1960,pp.62—90,esp.65—71。如他所说,这意味着当近代初期“新君主政体”出现之时,在英国受到了“实在法”制约,而非仅仅受到博丹主权理论提及的君权神授或自然法则的制约。
[4] 关于这一富有启迪性的插曲,参见J.J.Palmer, England,France and Christendom,1377—1399, London 1972,pp.74—76。(原书页码:117)
[5] 参见C.F.Richmond,“The War at Sea”,in K.Fowler(ed.), The Hundred Years' War, London 1971,p.117,以及“English Naval Powe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istory, LII,No.174,February 1967,pp.4—5。人们刚刚开始探讨这个问题。(原书页码:118)
[6] S.T.Bindoff, Tudor England, London 1966,pp.56—66.书中对此进程有一相当简明扼要的叙述。(原书页码:119)
[7] G.R.Elton,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London 1956,pp.49,53.
[8] C.Russell,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s, Oxford 1971,pp.41—42.书中明确叙述了本阶段英国国会因其会期之短暂、召集之间断而成为衰颓的势力;另外,作者准确地强调指出,君主政体和国会之间的制度契合有赖于国内统治阶级的团结。至于英国国会制度的社会基础,参见Penry Williams富有洞察力的评论:“The Tudor State”, Past and Present, No.24,July 1963,pp.39—58。(原书页码:120)
[9] 关于参觐圣恩运动内涵的敏锐论述,见J.J.Scarisbricke, Henry VIII, London 1971,pp.444—445,452。(原书页码:121)
[10] Elton对于克伦威尔的行政“革命”的评价过于夸张,Elton,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Cambridge 1953,pp.160—427,又见Elton,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pp.127— 137,160—175,180—184。其他人又低估了其意义,参见G.L.Harriss,“Mediaeval Government and State-Craft”, Past and Present, No.24,July 1963,pp.24—35。至于近期的评论,参见Russell,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s, p.111。
[11] 在这一时期也提出了建立常备军并册封司法贵族的计划。如果这两个措施真正得以实施,将改变16、17世纪英国历史的进程。事实上,国会对此两项措施均持否定态度,尽管它赞成由国家控制教会并在乡间实现和平,它仍然意识到建立专业化军队和在贵族内部出现司法贵族阶层的逻辑结果必然会是在社会上为其许多成员造成不利。在克伦威尔办公室档案中发现了于1536—1537年间起草的建立常备军的计划草案,此项研究见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XXIV,1951,pp.1—18。至于在有封号贵族中按地产册封司法贵族的建议,参见Holdsworth,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IV ,pp.450—543。
[12] Joel Hurstfield,“Was There a Tudor Despotism after al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67,pp.83—108.该文实际上对现阶段许多文章中出现的辩解式的年代错误提出了批评。Hurstfield强调隐藏在权力法案、叛国法案、王室的官方检查制度以及宣传手段背后的真实动力。Mousnier断然否定了一度为人们接受的“都铎王朝并非绝对主义”的论调,见Mousnier,“Quelques Problèmes Concernant La Monarchie Absolue”,pp.21—26。Scarisbricke详细论述了亨利八世对国会的态度,见Scarisbricke, Henry VIII ,pp.653—654。(原书页码:122)
[13] 到该朝末年,三分之二的地产已经易手,出售教会地产的平均收入高于未出售地产地租的30%。见F.Dietz, English Government Finance 1485—1558, London 1964,pp.147,149,158,214。(原书页码:125)
[14] Stone, 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 pp.265—266.
[15] 关于中世纪早期贵族向中世纪末期贵族的嬗变,以及随之而来的骑士阶层的转变,见N.Denholm_Young,“En Remontant le Passé de l'Aristocratie Anglaise: le Moyen Age”(英国贵族史:中世纪), Annales, May 1937,pp.257—269(在14世纪后期,册封的“贵族”头衔有了与其早期大相径庭的新含义,成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有关巩固贵族体系的分析,见K.B.Macfarlane,“The English Nobilit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XII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 Vienna 1965,Rapports I,pp.337—345,文中强调了这一过程的独到之处和不连贯性。(原书页码:126)
[16] 在这次危机中,政府不可能指望从各郡征募的士兵的忠诚。见W.K.Jordan, Edward VI:The Young King, London 1968,p.467。
[17] 关于法规条文的比较研究,见Elton,“The Political Creed of Thomas Cromwel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56,p.81。(原书页码:128)
[18] J.E.Neale, The Elizabethan House of Commons, London 1949,pp.140,147—148,302.(原书页码:129)
[19] C.Oman, A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37,pp.288—290.
[20] C.G.Cruickshank, Elizabeth's Army, Oxford 1966,pp.12—13,19—20,24—30,51—53,285.(原书页码:130)
[21] Cruickshank认为在这一时代,在亨利八世辞世后近60年中未能产生正规军,其原因在于没有成年男性君主亲率陆军作战。见: Army Royal, Oxford 1969,p.189。
[22] “爱尔兰是欧洲最后的儿女,从废墟与荒蛮(许多地方均如此)之中被唤醒,繁育人口,发展种植业;屏弃野蛮落后的习俗,适应人道与文明的生活。” The Works of Francis Bacon, London 1711,Vol.IV,p.280.关于此类殖民主义感情的其他例证,见pp.442—448。与其同时代人一样,培根完全明白英国在爱尔兰履行文明开化使命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我深信,如果上帝赐予本王国和平与公正,没有一个放高利贷的人能够肯定在17年间本息均能够翻番,如同王国在同样时间内将财富与人口总量翻了一番一样。……即使人与大自然携起手来,在欧陆之上也很难找到一种商品能够带来如此影响的例证。”(pp.280,444)请注意,这里已经明确地把爱尔兰作为向大陆扩张的一个替代性出路。(原书页码:131)
[23] 至于16世纪初叶的情况,参见M.MacCurtain, Tudor and Stuart Ireland, Dublin 1972,pp.1—5,18,39—41。(原书页码:132)
[24] 至于使爱尔兰人就范的策略,参见C.Falls, Elizabeth's Irish Wars, London 1950,pp.326—329,341,343,345。英国人在爱尔兰的暴怒如同西班牙人在尼德兰的暴怒一样,都是毁灭性的。但是,英国人几乎没有任何克制的迹象,而西班牙人至少没有摧毁荷兰人的海堤——腓力二世政权视此为种族灭绝的策略而加以否决。见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pp.134—135。(原书页码:133)
[25] 至于这一发展,参见Cipolla, Guns and Sails in the Early Phase of European Expansion, pp.78—81。Lewis断言的英国在这一发展中的优先地位则证据不够充足,见M.Lewis, The Spanish Armada, London 1960,pp.61—80。
[26] G.J.Marcus, A Naval History of England,I,The Formative Centuries, London 1961,p.30.
[27] Garrett Mattingly, The Defeat of the Spanish Armada, London 1959,p.175.(原书页码:134)
[28] 的确,到18世纪,当海军部成为政府中开销最大的部门时,海军不仅依靠伦敦商业区筹款,而且也为在舰队航行之中商业利益或战略利益孰为先的问题争论不休。参见Daniel Baugh, British Nav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Age of Walpole, Princeton 1965,p.19。
[29] 欣泽(Hintze)的论点简洁明了,当然,也许有点过于简单:“岛国地位决定了英国并不需要常备陆军,至少不必拥有欧陆国家那种规模的陆军,它只需要一支既可用于商业利益又可作战的海军,因此,英国的绝对主义未能发展起来。”在另一精彩段落中他补充道:“陆上力量形成的组织支配着国家机构本身并给予它一个军事形式。海上力量则只是打向外部世界的拳头,不可能用来抗击‘内陆军队’。”Hintze, Gesammelte Abhandlungen, I,pp.59,72.欣泽本人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威廉皇帝海洋帝国主义的热烈鼓吹者,自然很有理由认真研究英国海军史。(原书页码:135)
[30] 在下一个世纪,不论陆军还是海军,每个士兵的费用均增加了两倍,当然,海军还需要先进得多的后勤供给和维修工业。见Clark,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119。
[31] 至于这一进程,参见T.C.Smout, A History of the Scottish People 1560—1830, London 1969,pp.44—47。书中对宗教改革前苏格兰的社会作了深刻的研究。(原书页码:136)
[32] G.Donaldson, Scotland:James V to James VII ,Edingburgh 1971,pp.215—228,284—290.(原书页码:137)
[33] L.Stone, The Cause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529—1642, London 1972,pp.72—75,131.该书对于经济问题以及综合分析的论述非常杰出,是一本对该时代最好的概论。(原书页码:138)
[34] E.J.Hobsbawm,“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in Aston(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1965,pp.47—49.
[35]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London 1961,p.51. 1628年,路易十三从诺曼底攫取的收入相当于查理一世从全英国得到的全部财政收入:L.Stone,“Discussion of Trevor_Roper's General Crisis”, Past and Present, No.18,November 1960,p.32。(原书页码:139)
[36] 斯图亚特王朝的这些方面只能为17世纪初日益发展的政治斗争增添色彩,却不可能为之提供新的线条。Trevor_Roper在其近年来颇有分量的论文中论证了这些问题: Historical Essays, London 1952,pp.130—145。不过如果同意他的观点,即只要运用灵活的政治手段就能解决斯图亚特王朝面临的问题,那就错了。实际上,斯图亚特王朝所犯的错误远不如其前辈都铎王朝盲目出售土地那样致命。使英国绝对主义得不到巩固的不是缺少政治人才,而是没有制度基础。(原书页码:140)
[37] 至于都柏林的斯特拉福德政权的意义以及它在新英格兰地主阶层中激起的反响,参见T.Ranger,“Strafford in Ireland: a Revaluation”,in Aston(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pp.271—293。(原书页码:141)
[38] G.Aylmer, The King's Servants.The Civil Service of Charles I, London 1961,p.248.
[39] 军中上校均为贵族,尉官是地主,士兵们则是他们的佃户——“年轻、健壮的庄稼汉”。见Donaldson, Scotland:James V to James VII, pp.100—102。盟约派军队司令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是瓦萨王朝派驻斯特拉尔松(Stralsund)和奥德河上的法兰克福的总督:他和他的同事把欧陆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带回英国。(原书页码:142)
[40] 有可能是由于查理一世在1641年私下与爱尔兰英国旧贵族谈判从而不明智地激发了北爱尔兰地区的起义。见A.Clark, The Old English in Ireland, London 1966,pp.227—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