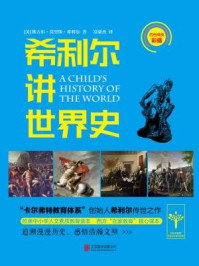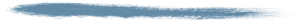
书写历史并非自古就有的犹太传统。近代以前称得上是历史的犹太书写寥寥无几。希伯来语《圣经》(基督教术语叫“旧约”)中有些书卷被当作历史书,但《圣经》作者视历史进程为宗教真理不断展现的过程,体现的是上帝之手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和控制,故历史在犹太传统中并非希腊意义上的探询,而是对神意的演绎。例外自然有,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约瑟夫斯(Josephus),这位公元1世纪的犹太史学家借鉴希腊史学模式,用希腊文撰写了自创世到他那个时代的犹太史,然而,几乎没什么犹太人在18世纪以前阅读过,他的著作能够传世,完全是倚赖基督教教会的保存。
到了18世纪,对犹太人历史的兴趣才显著出现。开风气之先的是基督教作家。雅克·巴纳热(Jacques Basnage)的十五卷本《犹太人历史》(1716)从耶稣时代一直写到18世纪,其副标题明确说这是“充当约瑟夫斯所作历史的延续”。巴纳热是新教加尔文宗在法国的信徒(即胡格诺派),因为宗教信仰而被逐出法国,流亡荷兰。他撰写这部犹太史,除了秉持基督徒一贯有的向犹太人传教的热情,也包含对犹太人在后《圣经》时代流落天下的感同身受的移情。
自19世纪初起,随着历史在德国大学里渐渐脱离神学或希腊罗马经典著作而被单独讲授和研究,犹太学者才开始以学术批判的眼光看待自身过去。其时,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虽然已让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广泛流行,但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的传统偏见依然根深蒂固,犹太人要想切实获得所在国的完全公民权利,仍旧任重道远。另一方面,欧洲犹太人也感到有必要改革犹太教,剔除其中肉身复活等现代启蒙理性视为迷信的成分,以便让传统犹太教在一个宗教已退入私人领域从而可供个人自由选择的时代重现生机。正是在对外和对内这两条战线上,书写犹太史成了一些德国犹太学者顺应时代要求的一把利器。
在亚伯拉罕·盖格(参看本书 此处 )等学者看来,后《圣经》时代的犹太史已没有什么政治内涵。公元70年第二圣殿的毁灭(churban)是犹太传统中莫大的灾难,犹太人因此在巴勒斯坦丧失政治主权,犹太教也从此彻底改变:学习宗教经典一旦取代圣殿中的动物献祭,成为宗教崇拜的形式,犹太教就成了一个可以带往世界各地的宗教,进而为一神思想在万民中的传播迈出决定性一步。因此,犹太教本身并非因循守旧者声称的那样一成不变,改革犹太教不仅在历史上有先例可循,更是促成犹太宗教传统获得更大发展的必由之路。相应地,书写犹太史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记录和分析宗教教义、仪式和制度的历代流变,让当时对犹太教的改革显得可以接受。
对政治维度缺失的强调还带有现实政治因素的考量。在盖格这类德国学者眼中,比第二圣殿毁灭更加重要的是亚夫内(Yavne)经学院的建立。《塔木德》中记载了一则传奇:罗马大军围攻耶路撒冷期间,拉比约哈南·本·扎卡伊预见圣城陷落和圣殿毁灭,便吩咐门徒把他装进棺材抬出城,然后来到罗马统帅面前,凭借机智获得许可,在亚夫内建立学院,确保继续有人研习犹太圣书(参看本书 此处 )。亚夫内为犹太教日后的千秋大业奠定基础。盖格等人以亚夫内为分水岭,重新定义犹太人:在亚夫内经学院建立以前,犹太人是享有政治主权的民族,而此后犹太人只是一个精神上自由的宗教社群。将后《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定性为宗教社群,其当下的政治内涵显而易见。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做一个有犹太信仰的公民是可以接受的,但作为一个民族的犹太人就必然令德国主流社会猜忌他们到底更忠于德国,还是更忠于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只有打消主流社会对这种双重忠诚的顾虑,才有利于犹太人获得所在国完全的公民权利。
于是,最早书写犹太史的德国犹太学者形成了一种共识:犹太人的历史独特性最能够体现在他们的一神观念之中,因此犹太史的本质是犹太信仰的历史。换言之,犹太人近两千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既没有国家又没有土地,犹太史的连续性靠犹太教体现,书写犹太史就是书写犹太教史。
海因里希·格雷茨(Heinrich Graetz)的十一卷本《犹太人历史》(1853—1876年)堪称德国犹太史编纂的最高结晶,也是整个19世纪出现的影响最大的犹太史作品。到格雷茨写作时,犹太史是犹太教史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他更愿意用“民族魂” (Volksseele) 这个比宗教宽泛的观念来统摄犹太史。他既没有脱离犹太民族抽象地去谈论一神观念,也没有关注犹太过去那些纯粹物质的方面。他聚焦思想和文化的发展,饱含激情地刻画出一部犹太集体灵魂的历史。不过,在格雷茨的时代,同化之风在德国犹太社群中越刮越烈,反犹主义也已在德国社会冉冉上升。他要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因此,他书写犹太史,并不是为了拓展启蒙,也不想寻求让基督教社会在政治或智识上接受犹太人,而是要通过揭示犹太人走过的不同历史道路,为被现代性重创和削弱的犹太身份聚气和寻根,以重新恢复犹太人的自信;对于非犹太文化,他很少掩饰自己从道德和审美立场做出的负面评价。这种旨趣当然与渐渐兴盛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南辕北辙,因此格雷茨遭到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厉声讨伐也就不奇怪了。
进入20世纪,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席卷下,德国犹太学者一直小心翼翼回避的用民族界定犹太史连续性的路径终于在东欧开花结果。东欧多民族、多语言共存的现实让西蒙·杜布诺夫(Simon Dubnow)反对犹太人不是民族而是宗教社群的观点,他认为犹太人漂泊了上千年,已成为精神上的民族,无需常规民族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和土地。事实上,这种不植根于土地而以历史与文化为安顿的民族,在他看来恰恰代表了民族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犹太史,就应当研究承载民族精神的民族制度。在他用俄文撰写(但最早用德文出版)的十卷本《世界犹太人史》(1925—1929年)中,历史上形形色色自治的犹太社群 (kehilah) 便取代一神观念,构成体现犹太史连续性的主线。这部巨著也不再是宗教史、思想史或文学史,而毋宁说是一部制度史(杜布诺夫自称是“社会史”)。杜布诺夫笃信,犹太人可以在异族统治的政治框架下通过自治的民族共同体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这恰恰是持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历史学家竭力反对的。他们认为犹太人生活在异族统治中根本没有希望,唯有时刻不忘《圣经》中的“应许之地”,才能确保犹太人幸存,故犹太史的主旋律应当是揭示历代犹太人对“以色列地” (Eretz Yisrael, 这是“巴勒斯坦”的希伯来文术语)的渴望和回归。这种立场的代表自然来自1925年开办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历史学家,他们几乎清一色是来自欧洲的移民。后来当上以色列国教育部部长的迪努尔(Ben-Zion Dinur,1884—1973年)主张,犹太史的核心是以色列地的历史,犹太人在流散地的历史尽管不乏闪光之处,但更多的是迫害和苦难,由此造成的反抗迟早会把犹太人领回犹太史的起点,即以色列地;1700年,一群波兰犹太人在一位信奉犹太神秘主义的拉比的带领下移居耶路撒冷,此事鲜为人知,但到迪努尔眼中就标志着现代犹太史的起点。相形之下,杜布诺夫把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犹太史的起点,因为正是这次革命把政治平等权赋予犹太人。以色列国研究《塔木德》时期历史的头号权威阿隆(Gedalyahu Alon,1901—1950年)认为,亚夫内在历史上实为罗马人拘留战俘和逃犯的集中营,约哈南·本·扎卡伊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送到那里的。这样,在德国犹太学者眼中确保犹太人幸存的纯粹的智识基础,就被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否认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看来,政治奴役没什么好粉饰的,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政治上的不作为和对国家概念的放弃。阿隆的解读还强调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难以调和的对立,这也是这派学者的一个特点。
生活在以色列国之外的同辈犹太学者当然难以认同这些激进的观点。英语世界声望最高的犹太史学者要数萨罗·巴龙(Salo Witmayer Baron),他是美国大学里犹太史学术研究的开创人。在他的十八卷本《犹太人社会与宗教史》(1952—1983年)中,核心不是以色列地,而是犹太人和犹太宗教。巴龙反复声称,犹太人的创造力与某方土地没有任何关系。对于写出多卷本犹太史的前辈,他也与他们明显有别。杜布诺夫虽然承认犹太人可以生活在异族统治下,但他对犹太民族的情感依恋使他不可能将犹太人所受的苦难归咎于他们自己,他们只是无辜的受害者,外部因素对犹太精神生活的影响在他那里也被最小化了。与之对照,巴龙总是结合特定时空下的普遍情况来论述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社群的发展,犹太史始终是内在的犹太因素与外在的非犹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连篇累牍的注释中包含大量非犹太史料。正因为熟悉犹太人生活的外部环境,巴龙坚持认为,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犹太史绝非像格雷茨等人描绘的那样,是“催人泪下的”(lachrymose)受苦受难史;相反,犹太人的整体生活条件起码不低于周围非犹太人的生活条件,就算遇到极端情况,他们也有能力调整适应,并在此过程中激发丰富的创造力。然而,巴龙将犹太史正常化的努力在学界之外影响不大,他对犹太史就是一部血泪史的反驳不幸隐没在纳粹屠犹投下的漫长阴影之中,他沉溺于细节考证的写作风格则牺牲了可读性。
随着后现代思想席卷学术界,民族变成想象的共同体,传统是发明的,书写无非体现了权力,整个世界更像是一个集合各种话语的文本。在这种将一切相对化的智识氛围下,为历史叙述找寻任何一以贯之的稳定本质或核心就显得徒劳无益。虽然历史学科并没有因此而终结,但犹太史编纂却呈现出新的特点。
2002年,美国犹太史学者大卫·比尔(David Biale)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一部新史》 (Cultures of the Jews: A New History) 出版,这部1000多页的著作由国际团队合作撰写,作者主要来自北美,但也包括以色列和法国学者。比尔认为,“民族”与“宗教”如今已不再是一成不变或铁板一块的客观范畴,而更多是主观构建,即历代犹太人相信自己有共同的民族传记和共同的文化。此外,犹太文化与犹太身份的产生还离不开犹太人与其邻居之间的权力关系,所以他主编这本犹太史,目标“是展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以及犹太世界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聚焦的是断裂和非连续性,以及不同地点和不同时代的犹太文化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宗教社群,而只有多种犹太文化,正如“文化”在此书标题中是复数所强调的那样。此书尤其关注了以前被忽视的中下层和欧美之外的犹太文化,却没有单列一章谈论犹太哲学或思想史。尽管比尔认为无法再像前辈那样继续构建种种宏大的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s),但犹太人阶层之间、性别之间以及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共生(symbiosis)和混杂(hybridity)反倒构成此书一以贯之的特色。
今天,书本已不再是人们了解传统的唯一媒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通过博物馆、互联网和影视作品获取历史知识。这些传播历史的新媒介显然已对历史书写本身产生影响。英国人西门·沙马(Simon Schama)的三卷本《犹太人的故事》是为配合同名电视纪录片撰写的,已出的两卷(2014,2017)共超过了千页。此书画面感逼真的精湛开篇完全出人意表:居然不在应许之地,而在埃及,还不是亚伯拉罕、摩西待过的埃及,而是公元前5世纪埃及象岛上驻扎的一支犹太雇佣军(对照本书 此处 )。这在《圣经》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仅靠19世纪末意外发现的纸草才为人所知。象岛犹太人不说希伯来语,不爱读书,关心时尚,与异族通婚,甚至公然违反《圣经》中不得在耶路撒冷以外建造圣殿的禁令,自行建造了一座圣殿。一言以蔽之,这些神圣文本之外的犹太人才构成犹太史可靠的起点。全书的核心论点就蕴含在这个起点里:象岛犹太人迥异于传统犹太史学所塑造的那种虔诚、自闭、饱受迫害、被迫放债的犹太人,他们这类颇适应周遭环境的犹太人同样在历史上生生不息,理应与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犹太叙事等量齐观。沙马光大了巴龙所开创的将犹太史正常化的努力,他在这条路上恐怕比任何前辈都走得要远。他眼中的犹太人不只是精神上的“圣书之民”,因为全书焦点是犹太文明的物质遗存——纸草、陶片、壁画、马赛克地板、羊皮卷写本等。沙马仿佛博物馆馆长,娴熟地讲解着心爱的展品,对自己想到的任何相关背景也一并巨细靡遗地娓娓道来。然而,一件展品与下一件之间未必有时空上的联系,如果说传统的“历史”首先意味着按照线性时间展开叙述,那么这本大作的确名副其实,是一串串饶有趣味的“故事”。
后现代盛行的文化多元主义在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并号召主流社会关怀这些群体的同时,也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诉求。正统派犹太人如今也开始书写他们以前漠不关心的历史,不仅愿意考虑非犹太内容,而且讨论自己的写作立场,并采用注释、参考书目等现代学术形式。这些著作是为正统派犹太人所写,在他们中间甚至颇为流行,其中美国出生、现居耶路撒冷的拉比韦恩(Berel Wein)的著作特别有影响。在韦恩看来,一部犹太史就是在忠于犹太传统还是反叛犹太传统这两极之间来回摇摆的种种表现的集成。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中,他的主角与重点自然是犹太教史上的重要拉比和犹太人内部的重要争论,谁能最终赢得胜利是一目了然的。“我越是阅读和研究犹太史,就越清楚地知道一位作者和策划者在引导以色列走向自己的命运。”这是要逆流回到《圣经》中上帝之手引领人类事务的神学史观。
对照上述犹太史学编纂的种种取向,谢德林这本1998年出版的犹太简史的特点就明朗了。本书不是犹太教史,犹太宗教在谢德林眼中只是犹太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犹太人的语言、制度、书籍和历史本身同样重要。每个时代的主要犹太社群构成这本犹太史的叙事主线,杜布诺夫的遗产依然清晰可见。而在谢德林的视野里,只有与非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不断互动的犹太社群才能繁荣与持久,才构成各个时代的主流犹太社群,这与巴龙的思想一脉相承。谢德林博士毕业于巴龙执教的哥伦比亚大学,后长期任教于纽约的美国犹太神学院,这是保守派犹太教的旗舰学校(见本书 此处 ),其学风素以博采传统和现代学术的精华而闻名。谢德林参加了比尔主编的那本犹太史的写作,与比尔一样,他在本书中也着意揭示不同犹太社群之间的文化差异,并开创性地在通史著作中突破欧美中心论,系统介绍了北非和中东犹太人在近现代犹太史上所起的作用,本书第六章的内容至今能在中文世界填补空白,这方面的学术优势主要得益于谢德林自己就是精研伊斯兰世界犹太诗歌的顶尖学者。本书不是多卷本或大部头的犹太通史,因而更有利于呈现出整个犹太史的发展脉络,而不至于让初学者见树不见林。但即使如此,要把漫长的犹太史精练到这个篇幅,仍难免用到不少令普通读者茫然的专有名词和术语。作者思虑周详,特地为每章配上大事年表、地图和知识要点栏,从而大大有助于读者消化吸收和把握重点。
总之,这本犹太史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观点上不刻意出奇制胜却又能充分反映现代学术发展的潮流,取材上则在围绕流散地和以色列地的叙事之间达成平衡,是对三千年犹太史凝练而精到的综合,堪称引领读者一窥犹太史堂奥的难得佳作。此书出版20年后未经修订仍在不断重印,足见它在构思和写作方面的成熟。
约十年前,当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大卫·斯特恩(David Stern)教授向我推荐了此书,此后我一直用它作为研究生教学的教材或补充读物,对此书的价值体会渐深。张鋆良没有告知我便将它译成中文,令我欣喜,这对他应当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我在他译文的基础上做了校对和修订,这对我自己又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让我对怎样精练、准确地表述犹太史有了新的体会。我请谢德林教授为中文版更新了书后的“犹太史书目”,其中有中译本的我已附上相关出版信息。谢德林教授还修订了原书极个别地方,中译本里不再一一标举。原书无注释,中译本脚注由我添加,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尽可能简短为要。原书历史人物和地名众多,未在索引中出现而又比较生僻者,中译本正文已附上原文。中译本的出版除了需要感谢斯特恩教授当初的推荐,还要感谢汪芳编辑的支持,杨沁龙、乔卉楠也为译稿提出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书目附言】
谢德林教授在书后“犹太史书目”的“通论”下列有犹太史基本书目。关于犹太史学编纂,除了“通论”中推荐的Yosef Hayim Yerushalmi的开创性著作,本文还参考了这个出色的选本Michael A. Meyer(ed.), Ideas of Jewish History (New York, 1974)以及这本近著Michael Brenner, Prophets of the Past: Interpreters of Jewish History (Princeton, 2010)。关于约瑟夫斯,参看泰萨·瑞洁克的《史学家约瑟夫斯及其世界》(周平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通论”中Louis Finkelstein主编的著作是把犹太人设想成宗教社群的代表作,H. H. Ben Sasson主编的著作是反映犹太复国主义立场的代表作。阿隆对亚夫内的解读见 Gedalyahu Alon, Jews, Judaism and the Classical World: Studies in Jewish History in the Times of the Second Temple and Talmud (Jerusalem, 1977), pp. 269-313。谢德林教授建议本书中文版删去原书“通论”中列入的巴龙的多卷本犹太史,显然是因为此书可读性不强,但巴龙的历史观至今在英美学界影响不衰。拉比韦恩的代表作是Berel Wein, Survival: The Story of the Jews in the Modern Era 1650-1990 (New York, 1990)。
中文世界已出版几本犹太史译著。阿巴·埃班的《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部犹太通史译著(中译本缺原书最后一章“今日犹太世界”),原书名为《我的人民:犹太人的故事》(Abba Eban, My People: The Story of the Jews) ,出版于1968年,作者当时任以色列国外交部部长。罗伯特·M.塞尔茨的《犹太的思想》(赵立行、冯玮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出色地梳理了犹太思想和犹太历史的关系,原书名为《犹太人民,犹太思想:犹太历史经验》(Robert M. Seltzer, Jewish People, Jewish Thought: The Jewish Experience in History, 1980)。塞西尔·罗斯的《简明犹太民族史》(Cecil Rot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ish People; 黄福武、王丽丽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译本根据第六版译出,写到1967年六日战争,作者是庶几与巴龙齐名的英国犹太历史学家,史学观点也与巴龙相近,反对犹太史就是血泪史。西门·沙马三部曲的第一卷《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中译本已经出版(黄福武、黄梦初译,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沙马写作此书的缘起正是多年前受邀续写塞西尔·罗斯一本未竟的犹太史。伯纳德·J.巴姆伯格的《犹太文明史话》(Bernard J. Bamberger, The Story of Judaism, 1970;肖宪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是一位美国改革派拉比写的犹太教史。另有两本图文并茂的犹太史图录的中译本(出版信息见“通论”),也有助于普及犹太史。
宋立宏
2019年2月
于香港道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