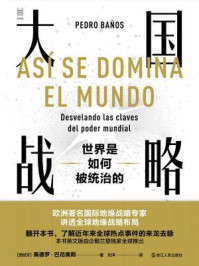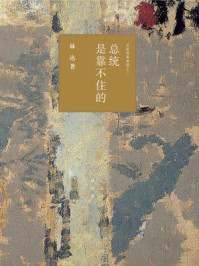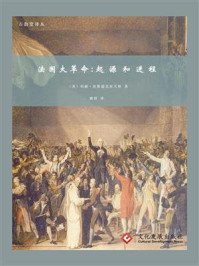美国刑事制度中有一个极具影响力的“神话”,那就是轻微案件的逮捕和定罪对一个亲历者而言其实微不足道,没那么耸人听闻。一起轻罪案件会召集资历最浅的检察官及公设辩护人,他们共同将认罪答辩的被告人“包装”成明智的样子,然后躲过复杂而昂贵的法庭辩论。这既证明了轻罪案件的处置过程有多么草率,也解释了为什么联邦最高法院会养成从轻罪案件被告人那里克扣宪法性权利的习惯——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可能被判处六个月以下监禁的被告人无权接受陪审团审判。如果他们不是因触犯轻罪被监禁,就没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可想而知,当法律认为刑罚不严重之日,就是对公民定罪最草率之时。
可想而知,当法律认为刑罚不严重之日,就是对公民定罪最草率之时。
然而与这个神话相反的是,轻罪案件的惩罚其实一点都不轻。因触犯轻罪被逮捕和定罪的被告人轻则被监禁、罚金、监控、跟踪、留下案底和受到侮辱,重则将会被剥夺工作、驾照、福利、监护权、移民身份和住房。他们有可能被取消贷款、吊销执业执照,也有可能陷入债务危机,产生不良信用记录。有时即便他们涉嫌的案子被撤销了,上述后果仍然会发生。
当代的美国法律几乎不会承认一次轻罪的经历就会引发如此广泛的惩罚性后果。刑法将由法官判决的监禁、缓刑和罚金划分为立法中的正式“刑罚”,而将其他所有“附带后果”抛诸脑后。然而,这种立法划分掩盖了事实——其实轻罪案件的惩罚后果无处不在。轻罪案件所引发的全部影响早在人们被判刑之前就开始了,但直到他们服完刑很久后才会结束。对罪犯而言,这种负担不仅与其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极不相称,而且比法院判决的刑罚严厉得多。
轻罪制度造成的影响来自方方面面,以下我们将审视轻罪制度带来的主要惩罚性措施:监禁、缓刑、罚金及收费、逮捕令、犯罪前科记录、公共福利损失、移民影响、未来的遭遇以及与上述惩罚有关的恐惧和耻辱。
泰龙·汤姆林(Tyrone Tomlin)是纽约布鲁克林一名53岁的建筑工人。2014年11月下旬的某天下午,他在和朋友聊天间隙去街角的商店里买了一瓶苏打水。当他走出商店,两名便衣警察正在对他的朋友搜身。一名警官拿走了汤姆林的汽水问道:“你另一只手拿的是什么?”汤姆林回答:“这是我拿的吸管,我准备喝苏打水用的。”警方搜查了汤姆林,并以持有吸管为名而逮捕了他。警官解释说:“这是吸毒工具。”
汤姆林被带至法庭,检察官称如果他作认罪答辩,就会建议法庭只判处他30天监禁,但汤姆林拒绝了。由于付不起法官设定的1500美元保释金,他被关进了因暴力犯罪而臭名昭著的莱克岛监狱。11月25日,离感恩节只有两天时,汤姆林再次出庭,这次控方虽然没有掌握毒品证据,但依旧试图与其达成辩诉交易,然而汤姆林继续坚称自己无罪。由于没钱保释,他又被送回了莱克岛监狱。几天后,汤姆林在淋浴时被一群囚犯照着头和眼睛一顿拳打脚踢,导致他两周后再次出庭时眼睛还肿着。然而就在这次听证会上,检方出示了一份来自警察实验室的报告,顶部用粗体写着“未检出被控物质”,证实了汤姆林所持的确实只是一根普通吸管。其实这份报告早在11月25日那次开庭时就传真给了地区检察官,但当时没有任何人提起它,没过几天他就被打了。现在官方驳回了这个案子,汤姆林终于如释重负地说:“可以回家的感觉真好啊。”
六个月后,汤姆林的眼睛仍然歪斜着,视力也逐渐变得模糊了。他说:“我感觉得了后遗症,我的眼睛和头部还会隐隐作痛。”现在莱克岛监狱的威胁已经过去了,他正在考虑这样一个事实:他被关起来打,损失了三周工资,也错过了与家人共度感恩节的机会,而所有这些不幸都是因为他付不起保释金。他总结得很有哲理:“我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不是拿着银勺子的强尼·里奇-基德(Johnny Rich-Kid),但即便我很生气,也不得不接受现实。这事确实不对,但事实就是这样。”他无奈地耸耸肩:“换作是你,你能怎么办呢?” [1]
在轻罪案件中,监禁不仅贯穿全程,而且最具破坏力。看守所是你被捕时被送来的地方,是你没钱保释时被关押的地方,是你被判有罪时服刑的地方,是你没钱支付罚金时受罚的地方。看守所不同于重刑犯们服刑的监狱,美国150万的在押重刑犯已经让这个国家在世界上声名狼藉,但是平均每年有1100万人被关进3000个拘留所,每天大约有73万人被羁押在看守所。平均而言,这些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因为犯有轻罪而被关押的,这一比例在部分城市高达50%。像汤姆林一样的未决羁押犯有将近50万人,虽然在法律上他们被推定无罪,但仍占全部嫌疑犯的60%。 [2]
看守所的羁押时间可短可长,一些人在被捕后只用待一晚上,超过一半的嫌疑犯会被关押超过一个月,四成嫌疑犯会被关押两到六个月,有18%的嫌疑犯会在里面被羁押半年以上。平均来看,无论嫌疑犯是否有过犯罪前科,他(她)都会在看守所里被羁押至少一个月。 [3]
大量的诉讼聚焦于监狱的危险状况和不健康条件,但很少有人会关注面临同样危险的州县看守所。这些看守所里人满为患、暴力频发,甚至会发生强奸和其他犯罪。这里疾病肆意传播:即使只被关押一小段时间,人们也会暴露于肺结核、皮肤病和肝炎之中。例如,佛罗里达州一位42岁的女服务员多萝西·帕林奇克(Dorothy Palinchik)因为偷了9美元的奶酪三明治而被收监,几天之后,她就因感染葡萄球菌和肺炎陷入了致命的昏迷。据统计,平均每年有近1000名在押犯于看守所中去世,其中有30%的死者是在被监禁的头几天去世的。 [4]
汤姆林的故事告诉我们看守所与保释现象是密切相关的。保释应当是一种善意的“首付款”——法官设定一定的金额用以确保被告人在将来会出庭接受审判。有能力支付这笔费用的被告人将被释放,当案结事了之时,这笔钱会发还给他们。(第三章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轻罪保释制度的相关规则和具体操作)然而对于没钱的穷人而言,保释金就制造了认罪的压力。大多数轻罪案件的被告人都无力支付保释金,他们要么作出认罪答辩后被释放回家,要么只能待在看守所里直到案件的诉讼程序全部结束。
无论对个人还是家庭而言,羁押的影响都是巨大的。研究表明,短短24小时以内的未决羁押即可导致负面影响,较长时间的羁押则具有更强的破坏性,它可能导致驱逐、拖车,以及食品券和其他物质损失。超过500万儿童曾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入狱的场景,仅2009年就有超过40万名未成年人的父母被羁押在当地看守所。受羁押的父母可能会失去监护权或探视权,或因无法支付羁押期间积累的子女抚养费而再次面临羁押。 [5] 总而言之,无论羁押发生在定罪之前还是之后,对于轻罪案件当事人而言都是一段代价高昂的经历。
缓刑是一段接受法庭监督的非羁押刑。虽然有时人们被判处缓刑,避免了在监狱中羁押,但缓刑也会给他们造成特殊的影响。例如,2014年多尼埃尔(Donyelle)和罗兰·霍尔(Roland Hall)为亲朋好友举办圣诞派对后,霍尔开车送两位客人回家,因在限速25英里/小时的地区内超速至38英里/小时,她被警察拦下了。酒精测试显示,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含0.09克,略高于马里兰州法律规定的0.07克,相当于她多喝了一杯葡萄酒。
虽然霍尔既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酗酒史,但仍然被判处了一年零六个月缓刑——如果她顺利度过了这段缓刑期,案件就将被撤销,犯罪记录也可消除。这段缓刑期的附带条件包括每月监督费105美元,为期26周的禁酒教育学习每月280美元,开庭费252美元以及每周三次的匿名戒酒互助会。如果霍尔想要变更住址,需要得到法官的许可。霍尔还欠担保人2000美元和她的律师1500美元。但是,她的执照被吊销了两周,失去了助理护士的工作,导致她和丈夫难以承担这些费用。
在霍尔遵守上述规定几个月之后,她的公寓出现了鼠患。她写信给法院解释她想搬家的原因,但法院发出传票拒绝了她的申请。后来,霍尔不慎丢失了自己出席匿名戒酒互助会的证明文件,法院便对她发出了逮捕令。霍尔前功尽弃,她不仅被羁押一个月,还在档案中留下了犯罪记录。结果,她由于驾照被暂扣半年不能开车上班又失去了新工作。 [6]
缓刑有时也被称为社区监督,是除罚金之外最常见的轻罪判决。据联邦司法统计局(BJS)报告称,大约有400万美国人正在接受某种形式的缓刑监督,其中近一半是因轻罪案件获刑,但这一比例被低估了,许多低等级的缓刑并未向司法统计局报告。 [7]
缓刑能使人免于牢狱之灾,因而通常被视为一种宽大的判决。但正如多尼埃尔和霍尔的故事所揭示的,缓刑可能不仅代价高昂,而且繁剧纷扰。缓刑犯失去了他们的隐私权:缓刑监督官可以随时搜查他们和他们的住宅。缓刑犯通常需要定期接受毒品检验,到缓刑办公室报到,接受电子监控、盘问、罚金或其他要求,这些要求对他们,尤其对低收入和工薪阶层的缓刑犯而言难以承受。一般而言,轻罪缓刑期限为六个月到一年甚至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内如果缓刑犯违反了任何要求,包括不支付罚金和其他费用,都可能重陷囹圄;大约只有三分之二的缓刑犯能符合所有条件安稳地度过缓刑期。 [8]
大多数轻罪案件被告人必须支付某种形式的罚金和费用,这会为他们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例如,帕特里夏·帕克(Patricia Parker)是卫理公会会议中心的一名厨师。为了换班吃早饭,她不得不在早上6点之前就开着男朋友的车穿过邻近的路易斯安那州伍德沃思小镇去上班。一天早上帕克开车去上班时,一位名叫大卫·戈德温的伍德沃思警官跟上了她,帕克既没有超速,也没有违反任何交通法规,但戈德温警官执意让她靠边停车,他说,“我只是检查一下”。最终,戈德温警官向帕克发出了四张传票:第一个是因为电脑显示她的驾照被吊销了,尽管帕克辩称她有文件证明驾照是有效的,但戈德温坚持开出了传票。然后是帕克没有注册和购买保险的传票,帕克给他看了自己的保险卡,但戈德温仍然开了传票。传票的罚金总额达到1060美元,随后戈德温将车拖走了,拖车费用为193.61美元。
伍德沃思地方法院的法官碰巧也是该市市长大卫·巴特勒,他担任这一职务已经三十多年了。帕克出庭时向巴特勒出示了文件,证明她有注册和保险记录,驾照也没过期。换句话说,戈德温所有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巴特勒问她身上带了多少钱,她说300美元。这位市长兼法官让她支付215美元的驾照吊销罚金,她不得不照做了。伍德沃思市随后追缴了帕克所有四张传票的全部罚金,并对她发布了逮捕令,声明她现在欠该市1580美元。几个月后,她在家中当着孩子的面被捕,并在看守所里羁押了25天。
全美汽车驾驶员协会(The National Motorists Association)列出了全国最糟糕的超速陷阱:伍德沃思市在该州排名第一。2007年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机构发布的《过度罚金执法报告》中担心伍德沃思市政当局参与了由创收驱动的执法活动,该报告显示交通罚金为伍德沃思市贡献了整个财政预算的61%。

伍德沃思市可能看起来像一个极端的案例,但对轻罪案件被告人动辄处以数百甚至上千美元罚金是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惩罚形式,仅加利福尼亚州的欠缴交通罚金就高达100亿美元。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因为很多人根本承受不起巨额的罚金。 [9] 不少处于低收入阶层的被告人不但会遭到第一次罚金,还会接连遭受长期债务、不良信用记录、被迫放弃房租或其他必需品(如食品、医疗和教育)的惩罚。如果人们一直不缴纳罚金,他们还可能被羁押。
与罚金相比,这里所称的相关费用在法律上不是惩罚措施,而是法院、监狱、城市、公设辩护人、检察官、缓刑监督官和办事员对被告人征收的用以支持刑事程序运行的财政经费。它们可以包括开庭费、公设辩护人费、监管费(又称“绳索费”)、毒品检测费、电子监控费、搜查费、监狱费和逾期费,等等,这些总费用可能远超任何罚金。例如,在加州,如果没有携带汽车保险的证明,就会被处以100美元的罚金。此外每人还将被收取100美元的罚金评估费、20美元的刑事附加费、40美元的开庭评估费、50美元的法院建设费、70美元的县基金、50美元的DNA基金、4美元的紧急医疗空运费、20美元的EMS基金、35美元的定罪评估费和1美元的夜庭评估费,共计490美元。如果错过付款期限,将额外支付10美元的DMV搜查费、15美元的缺席费和300美元的民事评估费,共计815美元。 [10]
像帕特里夏·帕克一样因为付不起罚金和相关费用而被监禁的人每年数以千计,监禁常常成为偿还上述债务的一种方式:一些州会规定在看守所羁押一天能抵扣50美元或100美元。由于这种以罚金债务为基础的监禁只在人们太穷而付不起时才会发生,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新债务人监狱”。
逮捕令是经法院签发,授权警察随时逮捕某人的令状,被告人未支付轻罪罚金或未出庭受审都会导致法院对被告人签发逮捕令。在美国,逮捕令有着广泛的法律作用和实际影响,数百万逮捕令正等待着被执行。例如,当伍德沃思市发布对帕特里夏·帕克的逮捕令时,这意味着她可能会在自己家中当着孩子的面被捕。悬而未决的逮捕令也具有宪法意义,它使警察免遭非法拦截该人而导致的不利后果。
爱德华·斯特里夫(Edward Strieff)就是这样。2006年,犹他州警方对盐湖城的一所房子进行了一周左右的监控,此前有匿名消息称房子里面可能有毒品犯罪活动。有一天,斯特里夫从里面出来,警察拦住了他并实施了搜查。这一拦截显然是非法的——警方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证据这么做,不过斯特里夫有一张尚待执行的轻微交通案件逮捕令。2016年,最高法院认为尽管拦截行为是非法的,但由于这张逮捕令的存在,在斯特里夫身上发现的毒品证据具备可采性。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对斯特里夫案的判决持有异议,部分原因是她对全国存在多少轻罪逮捕令抱有怀疑。“我惊讶地发现这些未被执行的令状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物”,她写道,“当持交通罚单的人未能缴付罚金或出庭时,法庭会发出逮捕令;当接受缓刑的人饮酒或违反宵禁时,法院会发出逮捕令。各州和联邦政府的数据库中有780多万份尚待执行的逮捕令,其中绝大多数似乎是针对轻微犯罪的。这些数据还不包括许多城市因交通违规和违反条例而签发的逮捕令,那数量更是惊人,那些抽屉早就塞满了。”

有些地方使用逮捕令比其他地方更为频繁。纽约市有超过120万份未结案的逮捕令,宾夕法尼亚州有140万份,加利福尼亚州则有250万份之多。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每年签发8.7万份逮捕令,而该市仅有68万居民。弗格森附近圣路易斯县的派思朗镇在2013年有23457个未决逮捕令,平均每位居民能摊到7个。 [11] 正因为这些逮捕令的存在,人们可能随时被截停和逮捕。
逮捕令不仅使数百万人的头顶笼罩着一片巨大的乌云,而且记录逮捕令的数据库就像云一样模糊不清。美国司法部对弗格森警察局的调查报告中称,该单位缺乏基本的记录保存程序:“矫正官员有时试图在法院文件中找到逮捕令以便确定所欠罚金的数额,却往往无功而返。法院工作人员报告说,他们通常需要几周甚至数月时间才能将逮捕令输入系统。”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曾警告说,“执法数据库并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管,数据往往已经过时了”,“这些(逮捕令)数据库产生错误的风险并不小”并且“众多相互关联的电子信息在收集中的不准确性引发了对个人自由的严重关切”。 [12] 由于逮捕令数据库不可靠,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签发了逮捕令,也无法纠正这一错误以免被捕。
也许刑事定罪最著名的非正式后果是它对就业的影响。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Craigslist上的工作招聘信息中经常警告有轻罪的人不要心存侥幸地申请这些岗位,“没有例外!……没有任何类型的轻罪和/或重罪前科”,“不适用于任何轻罪/重罪”,“你的个人记录中不能有任何重罪或轻罪”,等等。 [13]
这类找工作的障碍可能会持续很久。约翰尼·马吉(Johnny Magee)在40岁的时候曾为他的叔叔拿了一个包裹,患有残疾的马吉当时并不知道包裹里装的是毒品。他因此事被判犯有共谋轻罪,这是他唯一一次与毒品和刑罚扯上关系。即便事情已经过了九年,一家位于洛瓦的家装商店仍然不愿雇用其在花园中心工作。“洛瓦的政策对我和其他很多好人都不公平”,马吉说,“即便我自那以后再也没犯过什么事,但他们还是盯着很多年前的那件案子不放。这太不公平了!” [14]
超过6500万美国人有犯罪前科,其中大多数只是牵涉轻罪案件。现在大多数雇主会进行犯罪背景调查,导致这些低等级定罪对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事实上,一些保险公司也要求雇主对雇员进行调查,作为承保后者的条件。 [15] 并且在线搜索和商业数据库的出现也使访问犯罪记录变得更为容易。
“我已经预料到自己会被拒绝了”,贾斯汀·甘农(Justin Gannon)说。受益于曾在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八年并获得无数勋章的良好背景,他还是经常会得到工作机会,但经过背景调查后,这些工作机会就被取消了。这是因为甘农曾在2003年时对自己参与的一次酒吧斗殴作出了认罪答辩,承认犯有轻罪袭击罪。他说当时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害怕自己会进监狱,他们“告诉(我)这个轻罪对我的个人档案不会有多大影响”。 [16]
与甘农在认罪前获得的建议相反,美国国家刑事司法记录信息商业销售工作组得出的结论表明,犯罪记录至关重要。“今天,背景调查——出于就业门槛、志愿者资格、房客筛选,以及许多其他目的——已经成为几乎每个美国成年人必经(即便不总是受欢迎)的成年礼。就像医疗病历、银行流水或征信记录一样,犯罪背景调查记录越来越成为每个美国人的信息足迹的一部分。”正如《永恒的犯罪记录》一书所强调的那样:“犯罪记录是伴随终生的。” [17]
对犯罪记录的日益依赖意味着即使某人曾犯了非常轻微的(轻罪)过错也可能会遭到大量工作的就业门槛限制。例如,2001年9月11日之后,制药企业礼来公司(Eli Lilly)扩大了背景调查程序,将轻罪囊括在内。这一举动导致礼来公司内部多名员工被辞退,其中包括一名女员工。她唯一的污点仅仅是因向一家冰箱租赁公司开了一张60美元的回扣支票而被判犯有轻罪。她说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她关闭账户后没有意识到支票还没有结清。 [18]
犯罪档案包括逮捕记录、犯罪记录、法庭文件和案件卷宗,有时还包括DNA样本。联邦法律授权收集包括涉嫌轻罪者在内的任何被捕者的DNA样本。大多数州会收集因重罪被捕或定罪的被告人的DNA样本,这种做法正越来越多地扩展到轻罪。全美有三分之二的州在某些轻罪案件(通常是性犯罪)定罪后要求收集被告人的DNA样本。有七个州允许从一些没有被定罪的轻罪被捕者那里收集DNA样本。纽约州要求收集每个已定罪的轻罪被告人的DNA样本。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正在积极建立一个地方执法DNA数据库——它运行着一个“唾液换免罪”的项目,如果涉嫌轻罪的被捕者同意提供DNA样本,就可以被撤销对他们的指控。DNA样本可以将一个人及其亲属暴露在未来的刑事案件侦查中,但它们也可能向任何能接触到该遗传物质的人揭示供体的基因特征、疾病和家族谱系。我们可能还无法想象,因为一项轻罪而被载入DNA数据库最终会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19]
美国联邦法律规定,轻罪案件的缓刑犯违反任何缓刑附加条件都会被剥夺个人福利,这意味着如果一个人被判轻罪或违反缓刑规定,就会丧失一系列的公共救济机会,包括贫困家庭的临时补助、食品券、低收入者保障住房以及老年人和残疾人的生活保障金。触犯涉毒类轻罪的后果尤其严重,这些人还可能会被剥夺医疗保险、福利待遇和学生经济援助。 [20]
比如,在距离大一新生开学仅有一个月的时候,玛丽莎·加西亚(Marisa Garcia)和朋友们去庆祝她的19岁生日。当他们停在加油站加油时,警察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加西亚回忆道:“后来他们开始搜查汽车,他们搜出来一个零钱包,里面有一个盛着灰烬的小烟斗。”这个烟斗是加西亚的。
加西亚从未遇到过这类状况,她也不想告诉自己的母亲,就单独一个人去了法院。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加西亚很快作出了认罪答辩并缴纳了400美元罚金。两个月后,联邦财政援助办公室寄来了一封信,询问她是否参与毒品犯罪。“当我收到这封信时都有点心律失常了”,她因该案被暂停了一年的经济补助金。这令加西亚的母亲雪上加霜,她本就承担着抚养四个孩子的重任,最终不得不借了一笔钱来支付加西亚的学费。
加西亚觉得她实际上遭受了两次处罚:第一次是罚金,第二次是被剥夺经济补助金,而后者显然更为严重。如果她没那么拮据,能够支付起戒毒治疗计划费用的话,就能更快地拿回补助。“我仍然会因为吸食大麻而被捕”,她若有所思地说,“但如果我有钱,我就只会受到一次惩罚,做我想做的事。” [21]
国家政府委员会掌握的一个关于刑事犯罪附带法律后果的数据库中,统计了全国8958个不同的法律条款,这些条款规定了触犯轻罪会被取消的执业资格、住房机会、教育计划和其他福利。比如,触犯轻罪的人就不能担任亚拉巴马州的运动教练或助产士、阿拉斯加的验光师、科罗拉多州的教师、爱达荷州的兽医、艾奥瓦州的房地产估价师或肯塔基州的地质学家;不能参加特拉华州的证人保护计划,探望佛罗里达州的囚犯;也不能在密歇根州获得利用猫狗进行研究的许可,无法在罗德岛获得证券执照,在佛蒙特州领取失业救济金,或者在西弗吉尼亚州获得漂流执照。

失去私有或公共住房的租赁资格也是轻罪制度最具破坏力的后果之一。犯罪前科调查是申请住房租约的一个常规项目,和前文所述的雇主一样,私人房东也很容易获取租客的犯罪记录。而对于公共住房而言,某人一旦犯罪就意味着其从法律上被切断了申请住房的途径。在纽约,因行为不检而被定罪的人将在两年内失去申请公共住房的资格。在巴尔的摩,轻罪犯会被剥夺一年半的公共住房申请资格。 [22]
每年有数十万非美国公民被驱逐出境,他们中大多数是因轻罪案件被捕和定罪。庞大的轻罪体系牵扯到数量如此之多的民众,动辄对微不足道的过错施以刑事处罚,这种制度罗织起的大网使外来移民陷入了高危的境地。
伊丽莎白·佩雷斯的丈夫就是其中一员。“我们本应一起抚养孩子的,现在没有丈夫我一个人生活很艰难”,佩雷斯说。此时她3岁的儿子拉扯着她的长发,4岁的女儿正声嘶力竭地呼喊妈妈。佩雷斯现年35岁,出生于美国,来自俄亥俄州佩恩斯维尔,曾加入海军陆战队并服役于阿富汗。2010年,她的丈夫在一次交通拦截检查后被警方拘留,警方发现他曾在14年前被控斗殴及持有大麻,于是佩雷斯的丈夫被驱逐回墨西哥。 [23]
合法居民如果犯了轻罪,就可能会失去他们的移民身份。正如一位学者所述,可被驱逐的犯罪包括“轻微持有毒品犯罪……盗窃价值10美元的电子游戏,在商店里盗窃价值15美元的婴儿衣服,伪造一张20美元以下的支票……盗窃服务类犯罪,如逃票,故意裸露身体,(和)轻微的商店盗窃”。与此同时,如果非法移民因为诸如超速这样的轻微过错而被政府拘留,也可能面临被驱逐出境的风险。自2009年到2014年间就有近20万人仅仅因为交通肇事类犯罪而被驱逐出境。 [24]
安娜贝尔·巴伦(Anabel Barron)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生下了4个孩子。2014年,她因超速和无证驾驶而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处罚。“我害怕被驱逐出境”,巴伦说,“但对我的几个孩子来说情况更糟,他们不仅寝食难安,还不想上学,因为他们担心哪天放学回家后我就不在了。”

2007年至2012年间,诸如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等地被驱逐出境的近1万人之多,在此期间接受采访的大学生及家长们纷纷表示,他们害怕开车去学校、医院和工作,因为害怕被警察拦下后驱逐出境。 [25]
轻罪案件引发的逮捕或定罪可以完全逆转一位移民者的远大前程。那些因轻微过错而收监但尚未引起移民部门注意的未在册被告人面临着巨大压力,他们要立即认罪才能避免收到一张名为“被拘留者”的移民逮捕令。此外,辩诉交易中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都可能对合法居民产生重大的移民影响。比如,从365天的刑期中减去一天就可以将可驱逐的犯罪转化为不可驱逐的犯罪,律师则可通过辩诉交易,将持有大麻的轻微指控“讨价还价”成寻衅滋事的指控,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告人被驱逐出境了。

宪法规定存在移民问题的轻罪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在帕迪拉诉肯塔基州案(Padilla v. Kentucky)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移民法引起的一些重要惩罚与刑事定罪有关,因此如果律师未能告知当事人可能因定罪而被驱逐出境,就会因未能满足宪法第六修正案的要求而被视为无效辩护。尽管如此,许多移民仍会在不知道全部后果的情况下对轻微的过错行为作出认罪答辩——部分原因是许多人从一开始就根本没见过律师。轻罪案件被告人如果没有被判处监禁刑,他们就没有获得律师辩护的宪法性权利,而且许多本应有权获得律师帮助的被告人却根本没有律师为之辩护。所以,许多移民不得不在还没获得法律建议的情况下就独自面临轻罪的复杂后果,比如民事拘留和驱逐出境。

一旦一个人被判犯有轻罪,他与刑事程序之间的纠葛就再也不同以往了。警方对曾有过轻罪前科的人更有可能采取逮捕措施,而非像对待普通人那样仅仅开具罚单或者直接放行。检察官更有可能要求有前科的人保释或者对其科以更为严重的罪名。 [26] 法官则会对有犯罪前科的被告人判处更长的刑期,即便检察官更有可能寻求保释或以更严重的罪行起诉他们。法官通常会对有前科(即便是无需律师参与的轻罪前科)的人判处较长的刑期。
肯尼茨·尼古斯(Kenneth Nichols)就曾遭遇过这种处境。1983年时,酒驾还是一种相对较轻的犯罪。当时尼古斯因酒驾被诉而打电话咨询律师,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如果选择认罪的话就没必要找律师辩护。于是尼古斯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作出了不争辩的答辩,并被处罚金250美元。七年后当尼古斯因其他犯罪行为被提起公诉时,1983年的轻罪前科让他付出了高昂代价。在法官眼里,即便是1983年的酒驾也不再是什么轻微犯罪了,根据《美国量刑指南》,他因有酒驾前科而被多判了两年监禁。

轻罪前科会使一个人成为“累犯”,导致所有关于累犯的规则和限制都会生效。譬如,轻罪前科可能会剥夺一个人的毒品转移计划资格。对于二次犯罪者,法定惩罚通常也更高。对于仅限罚金的犯罪,犯罪前科可导致罚金增加一至三倍,甚至直接升格为监禁刑。 [27] 刑罚制度对轻罪案件不屑一顾的惯常态度加剧了这个问题,因为轻罪制度给人的印象是即使一个人曾犯下大量轻罪也不会影响什么,但当他们得知真相时却为时已晚。
在社区及居民受到严格管制的地方,这种“棘轮效应”尤其具有破坏性。像在巴尔的摩和布鲁克林,非裔美国人被拦下来检查的次数比平均水平高很多,由此他们遭到初次定罪处罚的概率也相应地增加了。等到下一次他们再被拦截检查时,因他们已经有了初犯记录,便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越多,刑事制度对他们的处罚就会越严厉。例如,纽约市交通警察局实行累犯政策,当人们第一次因为逃票被临检查获会收到一张罚单,但如果警察查到他们曾有过境违规或被捕记录,就会逮捕他们。由于纽约警察部门对不同种族有着不同比例的截停和逮捕历史——92%的逃票罪罚单发放给了占城市居民人数66%的有色人种,导致有色人种将继续在累犯政策下被高比例地逮捕。这一恶性循环把越来越长的犯罪记录和越来越严厉的刑罚判决强加给了他们,并不是人们变得更危险了,犯罪行为更严重了,而是整个刑罚体系在不断对自身反馈,一而再再而三地处罚同一批人。 [28]
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清楚有多少具体的负面影响和身体伤害是由轻罪处罚所引发的。然而我们容易忽视的是,被贴上罪犯的标签还会产生特殊的心理及社会创伤。
法学家保罗·巴特勒(Paul Butler)曾分享他的亲身经历。作为法学教授,巴特勒无疑是杰出的。他曾求学于耶鲁和哈佛,担任过联邦检察官,现在是乔治城法学院(Georgetown Law School)的知名学者,经常出现在国家电视台和全国性报纸上。然而早在1993年,他曾因一位恶贯满盈的邻居错误地指控他涉嫌袭击罪而被捕,旋即自行保释。巴特勒回家后哭了起来:“我明白如果真的被法庭判决犯有这个愚蠢的轻罪,我的生活就结束了。”他聘请了一位堪称华盛顿特区顶级的辩护律师和一名私家侦探,但直到被宣告无罪之前,他的内心还是惶恐不安的。他后来写道,他知道自己的清白“无关紧要”。尽管他最终被判无罪,还具有出类拔萃的学术背景,但他根本没办法从案件中恢复,“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身家清白了,”他总结道,“因为我已经留下了案底。” [29]
即使对于像巴特勒这样受过高等教育、坐拥丰富资源的业内人士而言,轻罪处罚也可能是痛苦而冷漠的。那么对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不宽裕的人们来说,他们更有可能牵扯上轻罪案件,而且往往令他们困惑、恐惧和不被尊重。回想一下这本书开头的故事,G奶奶在一次她不理解的庭审之后被戴着手铐抽泣着走出了法庭,没有人再费心向她解释。对于那些曾经历过这一过程而留下犯罪记录的人来说,反复陷入刑事司法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创伤。正如法学家乔纳森·西蒙(Jonathan Simon)所说:“轻罪制度的整个体制似乎特意让城市贫民遭受一系列微小却不断累积的创伤,进而使他们身为平等公民的自尊受到伤害。” [30]
轻罪的逮捕或定罪还可能破坏一个人与家人、朋友、同事和礼拜场所的关系。例如,田纳西州卢瑟福德县的辛迪·罗德里格斯(Cindy Rodriguez)在缓刑期间因支付不起罚金和诉讼费用,法院对其发布了逮捕令,并将她的面部照片放在了Facebook网站上。
她的律师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罗德里格斯女士立即接到了牧师和差不多十个邻居的电话,说看到了她违反缓刑要求的消息。她感觉自己被当场羞辱了,因为她不得不告诉教会和社区的人们,她是因为贫穷、残疾而无力支付罚金才被迫如此。对她而言,向邻里坦白自己太穷真是令她颜面扫地。”

当民众与刑事司法扯上关系时,也会悄然改变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事实上,这会颠覆他们对民主社会的认知以及他们在民主社会中的地位。被逮捕和定罪的人可能会表现出学者所称的“系统性回避”,有意避开保存正式档案的机构,如银行、医院和学校。研究表明,经历过刑事司法程序的人,即便只是轻罪程序,也会更不信任政府、更少地参与政治。正如一位受访者解释的那样,反应迟钝且粗暴的刑事系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政府”。其他人则更加悲观:“我们所知道关于政府的一切都是坏的,我们不知道它好在哪里。” [31] 轻罪诉讼程序就是这样每年向1300万美国人灌输这种愤世嫉俗和名声扫地的公民教育的。
而这正是下级法院已经“教”了很久的一门课。1979年,社会学家马尔科姆·菲利(Malcolm Feeley)曾写过一本关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轻罪法庭的著名著作,名为《程序即是惩罚》 [32] ,他的书名抓住了一个事实,即仅仅被带到法庭并经历司法程序往往比法官可能判处的任何正式判决都更具惩罚性。甚至当案件被驳回时,涉案的被告人已经被惩罚过了,仅仅是被迫出庭为自己辩解而已。菲利认为,司法程序本身(而不是正式的定罪或刑罚)在许多方面是司法实践的重点,是一种管理穷人、弱势群体或街头混混的方式,无论这些人是否真的进行了违法犯罪。
菲利的格言在今天来看更加真实。轻罪案件的诉讼程序早在人们进入法庭之前就开始“惩罚”他们,并且在法院判决之后仍旧在继续,它甚至还可以惩罚那些从未被定罪的人。与刑事司法擦肩而过的破坏性后果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当你依次被临检、逮捕、传唤、监禁、保释之后,你的家人和单位会被告知你已经涉嫌犯罪了,这些经历让个人和社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上,对于有色人种、移民和其他预料自己将受刑事司法影响的人而言,对刑罚避之不及的恐惧早已萦绕在他们心头。在刑事处罚结束之后,这种影响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正式的逮捕或定罪记录、被定罪的心理和经济负担会伴随人的一生,这些影响如此之大,已经成为犯罪者充分行使公民权利和参与经济生活的永久障碍,相当于一些人所说的“新型的公民死亡”。 [33]
从技术上讲,立法并不会承认上文所述的诸般困难为“惩罚”;也不认同我们所遭受的种种“无罪之罚”。从法律主义的视角来看,泰龙·汤姆林在狱中受伤的眼睛不算;霍尔丢掉的工作不算;玛丽莎·加西亚失去的经济补助也不算;这些案件对他们家庭的影响都不算什么惩罚。 [34] 但正如这些故事所揭示的,法律主义的视角忽略了轻罪案件对亲历者施加惩罚的分量和程度,因为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行为,也足以使一个人的生活脱轨。
相反,避开这类轻罪则可以让各种各样的大门都为你敞开。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奥巴马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中坦言,他曾像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一样也尝试过毒品,但是他从未被逮捕过,因此也从未遭受过低级毒品犯罪所带来的持久损害。许多年后,奥巴马在一所联邦监狱外对记者发表讲话时将自己与监狱中的囚犯相提并论:“这些年轻人犯下的错误与我犯下的错误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未曾有过支持自己的基础,也没有第二次机会,更没有让他们在犯下错误后得以幸存的资源。” [35] 如果年轻的奥巴马曾被迫需要忍受轻罪带来的恶果,那么美国历史可能真的会被改写。
[1] Nick Pinto, “The Bail Trap,” New York Times , August 13, 2015.
[2] Danielle Kaeble and Lauren Glaze,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6), 2; Todd D. Minton and Zhen Zeng, Jail Inmates in 2015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6), 1, 4(27 percent of jail inmates held for misdemeanors regardless of conviction status); Todd D. Minton and Zhen Zeng, Jail Inmates at Midyear 2014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June 2015), 1—4; Christian Henrichson et al., The Price of Jails: Measuring the Taxpayer Cost of Local Incarceration (New York: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May 2015), 7; Ram Subramanian et al., Incarceration's Front Door: The Misuse of Jails in America (New York: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February 2015), 5(in New York 50 percent of cases involving jail were for misdemeanors)。
[3] Doris James, Special Report: Profile of Jail Inmates, 2002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2004)。
[4] John Gibbons and Nicholas de B. Katzenbach, Confronting Confinement: A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Safety and Abuse in America's Prisons (New York: Vera Institute of Justice, 2006), 6; Sharon Dolovich, “Two Models of the Prison: Accidental Humanity and Hypermasculinity in the L.A. County Jail,”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and Criminology 102, no. 4(2012)(describing special jail unit designed to protect gay and transgender inmates that created a less violent, more humane subculture within the larger jail); Jonathan Abel, “Staph Infection Sends Pinellas Jail Inmate into Coma,” Tampa Bay Times , February 27, 2008; “Presumed Innocent, Found Dead: Counting Jail Deaths in the Year Since Sandra Bland's Death,” Huffington Post , 2016, http://data.huffingtonpost.com/2016/jail-deaths/landing[https://perma. cc/8FG8-SH2S]。
[5] Christopher T. Lowenkamp et al., The Hidden Costs of Pretrial Detention (Houston, TX: 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 2013); Megan Comfort, “A Twenty-Hour-a-Day Job: The Impact of Frequent Low-Level Criminal Justice Involvement on Family Lif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65, no. 1(2016):67—68; David Murphey and P. Mae Cooper, Parents Behind Bars: What Happens to Their Children? (Bethesda, MD: Child Trends, October 2015); Hon.Marguerite D. Downing, “Barriers to Reunification for Incarcerated Parents—a Judicial Perspective,” Family Court Review 50, no. 1(2012):71; Michael Pinard and Anthony C. Thompson, “Offender Reentry and the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An Introduction,” N.Y.U.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Change 30(2006):599—600; Ann Cammett, “Expanding Collateral Sanctions: The Hidden Costs of Aggressive Child Support Enforcement Against Incarcerated Parents,” Georgetown Journal on Poverty Law and Policy 13, no. 2(2006):328—331.
[6] Shaila Dewan, “Probation May Sound Light, but Punishments Can Land Hard,” New York Times , August 2, 2015.
[7] Danielle Kaeble and Thomas P. Bonczar, Probation and Parol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5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December 2016), 5; Michelle S. Phelps, “Mass Probation: Toward a More Robust Theory of State Variation in Punishment,” Punishment & Society 19, no. 1(2017):59; Fiona Doherty, “Obey All Laws and Be Good: Prob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Recidivism,”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4, no. 2(2016):340(as much as 80 percent of misdemeanor convictions result in probation)。
[8] Michelle S. Phelps, “The Paradox of Probation: Community Supervision in the Age of Mass Incarceration,” Law & Policy 35, no. 1—2(2013):51; Dewan, “Probation May Sound Light.”
[9] Not Just a Ferguson Problem: How Traffic Courts Drive Inequality in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et al., 2015), 4, http://www.lccr.com/wp-content/uploads/Not-Just-a-Ferguson-Problem-How-Traffic-Courts-Drive-Inequality-in-California-4.20.15.pdf[https://perma.cc/D4BV-FH5Z]; Beth A. Colgan, “Reviving the Excessive Fines Clause,” California Law Review 102(2014):277—350.
[10] Not Just a Ferguson Problem , 10. The Supreme Court recently decided that the state cannot keep court costs and fees if the defendant is ultimately found innocent. Nelson v. Colorado, 137 S. Ct. 1249, 1251—1252(2017)。
[11]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Civil Rights Division, 2015), 55; Kendall Taggart and Alex Campbell, “In Texas It's a Crime to Be Poor,” Buzz Feed , October 5, 2017, https://www.buzzfeed.com/kendalltaggart/in-texas-its-a-crime-to-be-poor?utm_term=.qxRWR5zQ4#.ghY50Ldlk[https://perma.cc/529Q-PBEN]; Joseph Shapiro, “As Court Fees Rise, the Poor Are Paying the Price,”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9,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5/19/312158516/increasing-court-fees-punish-the-poor[https://perma.cc/9MSP-8R2W](accessed January 26, 2018); Respondent's Brief, Utah v. Strieff, No. 14-1373(January 22, 2016), 5; Radley Balko, “How Municipalities in St. Louis County, Mo., Profit from Poverty,” Washington Post , September 3, 2014.
[12] Investigation of the Ferguson Police Department , 47, 55; Herring v. United States, 555 U.S. 135,155(2009)(Ginsburg, J., dissenting)。
[13] Michelle Natividad Rodriguez and Maurice Emsellem, 65 Million “Need Not Apply”: The Case for Reforming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for Employment (New York: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March 2011)。
[14] Rodriguez and Emsellem, 65 Million , 4.
[15] James B. Jacobs, The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estimating that 20 million Americans have felony records); Joe Palazzolo, “Criminal Records Haunt Hiring Initiative: Insurance Background Checks Thwart Laws Aimed at Giving Second Chance to Ex-Offenders,” Wall Street Journal , July 12, 2015.
[16] Jenny Roberts, “Why Misdemeanors Matter: Defining Effective Advocacy in the Lower Criminal Courts,” U.C. Davis Law Review 45(2001):300.
[17] SEARCH et 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Task Force on the Commercial Sale of Criminal Justice Record Information (Sacramento, CA: National Consortium for Justice Information and Statistics, 2005); Jacobs,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 4.
[18] 42 U.S.C. §608(a)(9)(A)(forbidding assistance to “any individual who is violating a condition of probation”); Rebekah Diller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A Barrier to Reentry (New York: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2010), 28, notes 202—204; 21 U.S.C. §862.
[19] Jacobs,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 36—37; Elizabeth E. Joh, “Should Arrestee DNA Databases Extend to Misdemeanors?,” Journal of Recent Advances in DNA & Gene Sequences 8, no. 2(2015):2; 34 U.S.C. §40702(federal DNA collection statute); Andrea Roth, “Maryland v. King and the Wonderful, Horrible DNA Revolution in Law Enforcement,” Ohio State Journal of Criminal Law 11(2013):301—303(describing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being in a DNA database); Kimberly Edds, “Rackauckas Gets $1.38 Million for ‘Spit and Acquit,’” Orange County Register , December 16, 2010; Stephen Mercer and Jessica Gabel, “Shadow Dwellers: The Underregulated World of State and Local DNA Databases,” NYU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 69(2014); Sarah Gannett, “Brief for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deral Defenders as Amicus Curiae Supporting Respondent,” Maryland v. King, No. 12-207(February 1, 2013), 20.
[20] 42 U.S.C. §608(a)(9)(A)(forbidding assistance to “any individual who is violating a condition of probation”); Rebekah Diller et al., Criminal Justice Debt: A Barrier to Reentry (New York: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2010), 28, notes 202—204; 21 U.S.C. §862.
[21] The War on Marijuana in Black and White (New York: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2013), 82—84.
[22] Michael Pinard, “Collateral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 Convictions: Confronting Issues of Race and Dignity,” N.Y.U. Law Review 85(2010):491(on collateral housing consequences in New York and Baltimore)。
[23] Ginger Thompson and Sarah Cohen, “More Deportations Follow Minor Crimes, Records Show,” New York Times , April 6, 2014.
[24] Jason A. Cade, “The Plea-Bargain Crisis for Noncitizens in Misdemeanor Court,” Cardozo Law Review 34, no. 5(2013):1758—1759; Thompson and Cohen, “More Deportations.”
[25] Consequences and Costs: Lessons Learned from Davidson County, Tennessee's Jail Model 287(g)Program (Nashvill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of Tennessee, December 2012)。
[26] Jacobs, Eternal Criminal Record , 2—3(on police and prosecutorial decision-making)。
[27] Alexandra Natapoff, “Misdemeanor Decriminalization,” Vanderbilt Law Review 68, no. 177(2015):1091 and n. 177.
[28] Devon W. Carbado, “Blue-on-Black Violence: A Provisional Model of Some of the Causes,” Georgetown Law Journal 104(2016):1485—1498(documenting African American overexposure to repeated police contact); Andrew E. Taslitz, “Wrongly Accused Redux: How Race Contributes to Convicting the Innocent: The Informants Example,”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37(2008):122—124(describing the ratchet effect); Joseph Fox, “NYPD Transit Recidivist Policy Memorandum,” NYPD Police Department Memorandum, January 27, 2012; Rocco Parascandola and Graham Rayman, “NYPD Arrests Mostly People of Color for Fare Beating: Stats,” New York Daily News , February 12, 2016; Profile of General Population and Housing Characteristics:2010, New York City, NY (Washington, DC: US Census Bureau, May 12, 2011), http://www1.nyc.gov/assets/planning/download/pdf/data-maps/nyc-population/census2010/t_sf1_dp_nyc.pdf[https://perma.cc/XH42-EU99]。
[29] Paul Butler, Let's Get Free: A Hip-Hop Theory of Justice (New York: New Press, 2009), 4—5, 8—26.
[30] Jonathan Simon, “Misdemeanor Injustice and the Crisis of Mass Incarceration,”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Postscript 85, no. 5(2012):116.
[31] Sarah Brayne, “Surveillance and System Avoidance: Criminal Justice Contact and Institutional Attach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9, no. 3(2014):367—391; Amy E. Lerman and Vesla M. Weaver, Arresting Citizenship: The Democratic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Crime Contr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 4, 15—17(interviews)。
[32] Malcolm M. Feeley, The Process Is the Punishment: Handling Cases in a Lower Criminal Court (1979; rpt.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2), 30—31.
[33] Gabriel J. Chin, “The New Civil Death: Rethinking Punishment in the Era of Mass Convic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0(2012):1789—1791.
[34] See Megan Comfort, “Punishment Beyond the Legal Offender,” Annual Review of Law and Social Science 3(2007):271—289(charting the spillover effects of criminal justice contact on children and families)。
[35] Barack Obama, Dreams from My Father: A Story of Race and Inheritance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04), 93—94; Katie Zezima and Juliet Eilperin, “Obama Says That Without Family Support He Could Have Been in Prison,” Washington Post , July 16,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