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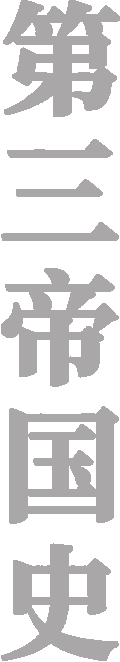
冲锋队在纳粹夺权斗争中起过独特的作用,然而希特勒就任总理后一年半,其又遭到了血腥清洗,地位一落千丈。冲锋队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谜团。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它同纳粹党之间是什么关系?
冲锋队的前身在纳粹运动兴起之同时产生,它是同慕尼黑的啤酒馆文化有关的。魏玛共和国确立了议会民主体制,政党要赢取选票,离不开发表演说。而发表演说的理想场合,除了小广场,就是啤酒馆。慕尼黑有不少大型啤酒馆,能容纳数千人。尤其是安放了原木长条凳桌的平民啤酒馆,是下层民众乐于聚会的地方,人声嘈杂,十分热闹。在政治骚动的年代,不少政党都把目光转向那里,安排能说会道者前往演讲,吸引光顾啤酒馆的民众注意。当不同党派的演说者推销各自的意识形态,并公开对不同政见出言不逊时,骚乱与斗殴随即爆发,啤酒杯、椅子和其他一切随手可及的物品都可以成为武器。 [1]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演说者在光顾啤酒馆时,都会带着一批人,无冲突时用来捧场,遭袭击时大打出手。德意志工人党及更具有暴力倾向的纳粹党在这种政治惯例中尤为起劲。1919年,德意志工人党即开始使用领宾员和会议防卫员,专门用于维护会场秩序,保护本党集会不受外人袭击。 [2] 1920年2月,纳粹党改名的当月,非正式的领宾队和防卫队改组成纳粹运动中的“纠察队”(Ordnertruppen),由钟表匠埃米尔·莫里斯(Emil Maurice,1897—1972)任队长。该组织有时也被称作“会场防卫队”(Saalschutzabteilung)。为了淡化其政治色彩以便于生存,1921年8月,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预下,它又改名为纳粹党的“体育运动队”(Turn-und Sportabteilung)。
“冲锋队”作为专用名词并非纳粹党的首创。其德文原文为Sturmabteilung,Sturm一词的原意是风暴、狂风,转义为猛攻、冲击、冲锋。因此,冲锋队也被译为挺进队、突击队。该名词的直接来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即1915年3月,西线德军指挥部为实施渗透战术,调集精干兵将,组建名为“冲锋队”的特种机动部队。直到1918年,这种部队仍然活跃在德军战场上。纳粹党的“体育运动队”里有不少军迷,甚至还有少量的退伍军人,他们很不屑于“体育运动队”这个怪名字,于是从1921年9月起非正式地称呼自己的组织为“冲锋队”。同年11月4日,慕尼黑的“宫廷啤酒馆”(Hofbräuhaus)发生了一场日后纳粹党吹嘘不已的械斗,据纳粹分子自称,43名冲锋队员顶住了800名红色反对者的进攻,保住了据点。 [3] 纳粹党在媒体里不断神化这个故事,称其为“(宫廷)啤酒馆大战”(Saalschlacht)。作为副产品,这个故事的主角——冲锋队也名声大振。于是,冲锋队成了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
冲锋队的诞生,固化了当时德国政治生活中防卫组织同政党组织形成紧密程度不等的联盟关系的格局。这种组合从右到左分别是:钢盔团(Stahlhelm)与民族人民党和人民党;冲锋队与纳粹党;黑红金国旗社(Reichsbanner Schwarz-Rot-Got,简称Reichsbanner)与社会民主党;红色前线战士联盟(Rotfrontkämpferbund)与共产党。
纳粹党的武斗组织改名为冲锋队,引起了军方人士的兴趣。魏玛共和国的重要州——普鲁士,具有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普鲁士邦国的几代开国君主,都重点抓了两支队伍,一支是官僚体系,另一支是军队,尤其是其中的军官团。普鲁士在统一德国的过程中,把这个传统推向了整个德国。不少年轻人向往军队,渴望以军人的身份建功立业,为自身赢取光辉的前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大量的青年吸收进军队,然而,《凡尔赛条约》迫使德国大量裁军。从战争期间的庞大兵力削减到仅仅十万官兵,无数军人只能无奈地退伍。然而,长期残酷的战壕生活使他们无法适应战后的普通生活。他们只能四处搜寻与自己有着共同经历和困窘境遇的人,聚集在一起,寻找各种得以让自己重温战争生活的机会。各种老兵协会、军人社团星星点点,遍布全国。战争经历被神化,“亡命军人”及老兵协会吸引着愤懑、绝望的青年。在战后初期,政府把镇压革命力量放在首要位置,因而放任右翼退伍军人加入各种白色“志愿兵团”(Freikorps,一译“自由团”),用以对抗红色革命。这些志愿兵团由职业军官领导,纠集一批亡命军人、退伍老兵、好斗青年,并打出煽情的口号——“来自国内外的敌人正在烧毁我们的房屋。救救我们,以德国同志情谊和忠诚的名义,赋予我们保卫民族的力量” [4] 。但随着革命高潮的消退,志愿兵团逐渐失去方向。冲锋队的崛起与“战绩”,再次勾起他们的兴趣。
军人染指的第一个表现,是志愿兵团派出军官充实冲锋队的领导层,如钟表匠莫里斯被年轻的前海军军官汉斯·乌尔里希·克林泽希(Hans Ulrich Klintzsch,1898—1959)取代,以便把冲锋队打造成一个具备军队特点的准军事组织。第二个表现,是更多的退伍军人加入冲锋队,使后者在人员结构上发生变化。仅以纽伦堡(Nürnberg)地区为例,1922—1923年,51名冲锋队领导人和普通成员中,37.3%的人有军役记录,而没有战争经历的青年只占19.6%。 [5]
在冲锋队军事化的过程中,罗姆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出身于慕尼黑一个铁路官员的家庭,较早进入军界。他19岁入伍,两年后即进入军官阶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部队进入西线与法军交战,多次立下卓著战功。在1914年9月的战斗中,罗姆所在的步兵团展开了与法军的恶战。他在此次战斗中受了重伤,被削去鼻子的上部,“整个脸部变形了,原来是圆乎乎的和有形的脸庞,现在按上了塑料鼻子,鼻子上部略有摇晃,鼻子下部有小硬块,脸上有一处明显的伤疤——整形手术严重地影响了他往后的生活,伤口也时常溃烂”
[6]
。在1916年6月的凡尔登战役中,罗姆所在的连队被打散了。“十来个人簇拥在罗姆周围,进攻并占领了许多条法军防线,俘虏了2名法军军官和65名士兵。”不过在此战役中,罗姆和其他士兵均严重负伤,罗姆伤势严重,“肺部附近被击中,肩部洞穿”。靠着战友的拼死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由此,他不仅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奖章和巴伐利亚的最高军内奖章——奥登奖章,还成为兵士中间活着的传奇英雄。
[7]
大战结束后,罗姆继续留在军内,但是其志向已经发生较大变化。他认为,德国战败和爆发革命这些事实,证明了政治的重要性。作为个人,如果仅仅把注意力局限于军事,是难以有所作为的。因而,他对激进主义政治团体和准军事组织给予较大的关注,并借助于曾一度管理州内
 驻军武器库的有利条件,非法向准军事组织提供武器,由此,成了激进主义团体的争取和依靠对象。罗姆与纳粹运动发生关系的时间比较早。1919年,当纳粹党还处于德意志工人党阶段时,他就入了党。随着希特勒入围,他们两人很快成为政治盟友和私人密友。
驻军武器库的有利条件,非法向准军事组织提供武器,由此,成了激进主义团体的争取和依靠对象。罗姆与纳粹运动发生关系的时间比较早。1919年,当纳粹党还处于德意志工人党阶段时,他就入了党。随着希特勒入围,他们两人很快成为政治盟友和私人密友。
在罗姆等人的推动下,冲锋队的功能和目标升级了,不再满足于维持会场纪律,而是向新的使命推进——“部分出于纳粹党领导人的设想,部分出于当时政治环境的考虑,冲锋队成了当时独立存在的几种政治系统的混合体,不纯粹是政党特点,也不纯粹是(独立于政党的)秘密准军事组织的特点,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8] 。也就是说,冲锋队实现了军事组织形式与政治行为的结合,成为一个半隶属于政党半独立的准军事组织。
冲锋队开始独立地走上街头,以集体游行的方式展示自己。1922年8月,它参加了由众多准军事组织和老兵协会发起的慕尼黑游行集会。此后,身着制服的冲锋队员排列出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成为慕尼黑街头反复上演的景观之一。同年10月,冲锋队战斗历史上又一个神话产生了。14—15日,希特勒率领800名冲锋队员乘火车前往巴伐利亚东北部的科堡(Coburg)参加右翼组织的爱国游行。科堡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因而是社会民主党等左翼力量占优势的地方,右翼力量选择这里举行爱国游行本来就是一种挑衅。希特勒和冲锋队不顾当局禁止进城游行的告诫,“他爱捣乱的同伙引发了街头暴乱,清除了街头的反对者,简直就是在围攻这个城市。这种显示威风的行动似乎使希特勒大胆地相信:他能够向巴伐利亚政府挑战而不会受到什么惩罚”。在科堡的经历是冲锋队第一次走出慕尼黑的大众游行,而且是在左翼的地盘,此事使得冲锋队和纳粹党声名大噪。很多年以后,这些冲锋队成员在相聚时仍会相互问询:“那时你在科堡吗?” [9]
尽管希特勒作为纳粹党元首参加了科堡游行,罗姆与希特勒的私交很不错,但是两人对冲锋队的定位是不同的。希特勒尽管在内心深处排斥政党政治,但在时代的逼迫下,看到了政党在夺权斗争中的特殊作用,因此要求以纳粹党作为纳粹运动的核心。对他来说,居第一位的是党而不是军队,冲锋队不是伪装的黑色武装,而是一把政治利器。然而对包括罗姆在内的其他人来说,在德国这样的国度内,军队的作用是高于政党的,政治领袖个人依靠军队的支持,就能够夺取并掌握政权。更何况当时德国处于凡尔赛体系的束缚下,建立秘密的武装力量是占主导地位的事情,而冲锋队由于同国防军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将成为德国解放事业战斗力量中更为有效的一员”。他们乐于看到冲锋队被允许和国防军一起携带武器,接受军事指令并使用武器,甚至在采取行动等特殊情况下,纳粹党的地方领导人也要自觉地听命于当地的冲锋队。 [10] 以后,这两种观点的分歧甚至上升为这样一个问题:在纳粹运动中,究竟是以冲锋队为主,纳粹党和希特勒成为冲锋队的“鼓手”即政治宣传员,还是以纳粹党为主,冲锋队仅仅是纳粹党的助手。
然而在1923年,随着德国陷入全面动荡,纳粹运动以半武装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两种观点的分歧被掩盖了。冲锋队积极地投身于“啤酒馆政变”,罗姆承担了占领并坚守国防军巴伐利亚州总部的重任。
经过政变失败的打击,罗姆的思想有所松动,放弃了武装夺权的意图。1924年4月他提前出狱,次月当选巴伐利亚州议员。他接受希特勒的委托重建冲锋队,确定“褐衫”为冲锋队制服,并宣布要把冲锋队打造成“纳粹党的战斗部队” [11] 。然而在实际行动中,他仍然关注于联合各种右翼准军事团体,着力于组建“战旗团”(Frontbann)组织,只是应者寥寥,很不景气。为了摆脱经济窘境,他前往玻利维亚担任政府的军事顾问,帮助训练玻方军队。
1925年初希特勒出狱后,在重建纳粹党的同时也关注冲锋队的建设。他任命弗兰茨·冯·普费弗尔(Franz von Pfeffer,1888—1968)为冲锋队领袖,并专门就冲锋队定位问题写了一封信,其中表示:
必须对冲锋队进行训练,这种训练不是以军事为基础,而是根据党的需要。
就对冲锋队进行体格训练而言,重点不是军事训练,而在于体育运动。
冲锋队的组织、队服和装备都要相应地落实,但它不是按照旧军队的模式,而是要适应它的任务。
冲锋队无需秘密地集合,而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游行,开辟各种活动的道路,以彻底消除冲锋队是一个“秘密组织”的种种传说。……必须从建立之时起,向队员灌输运动的伟大理想,从一开始就以代表这种理想的任务训练他们,使其达到眼界开阔……反对现存国家的斗争将是超出一种报复和阴谋的小范围之上,成为消灭马克思主义及其教条和幕后操纵者的一种思想意识的伟大战争。 [12]
此后,希特勒又明确规定:冲锋队的成员必须同时又是纳粹党党员,不允许同时参加其他政治或准军事组织;其他组织的成员,作为个人可以在脱离原组织后加入冲锋队,但不得集体加入;冲锋队不得与其他准军事组织联合或合并。他以这些举措来保证冲锋队只能成为纳粹党羽翼之下的附属机构。在以后的运作过程中,希特勒还剥夺了冲锋队的财权,规定它们不能自行募集金钱,所需经费由同级的党部领袖下拨。
普费弗尔是参加过一次大战的退役军官,拥有军事经验和组织才能,同时拥有一般军人所欠缺的政治嗅觉,清楚地看到旧式的军人暴动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反对纯军事化的组织,主张建立一个精英化、有高度纪律性、拥有强烈意识形态信仰的冲锋队。他在任期间的最大贡献,是确定了冲锋队的基本组织架构。冲锋队的基层单位是小队(Schar),由3到13人组成,主要依靠邻里之间的熟人关系建立。这样,任何有人的地方都存在建立一支小队的可能,使得冲锋队具备较强的“繁殖”能力。小队如同一个细胞,细胞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分裂出多个同一性质的细胞。然后以小队(Schar)—中队(Trupp)—突击队(Sturm)—旗队(Standarte)—旅队(Brigade)—中央领导机构,这种层层递升形式搭建出整个冲锋队的大厦。每一个上级单位都由几个下级单位组成,每一层级的单位数目增加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组建为更高一级的单位。一般情况下,5—8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2—4个中队组成一个突击队,2—5个突击队组成一个旗队,2—5个旗队组成一个上级单位。 [13] 当时,“旅队”这个单位没有真正落实,而是以区队(Gausturm)替代,最初共有19个区队。区队长由普费弗尔直接任命,区队以下的领导人选由地方自行决定。总体来说,冲锋队内部的上下级关系类似于中世纪的“采邑制”,每个层级都拥有半自治的权力。
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德国的失业人数飙升,最严重时达到八百多万。在冲锋队的人员构成中,下层民众尤其是失业工人的比重一直比纳粹党的高,冲锋队因而成为集聚落魄民众的天然“洼地”。在这一过程中,“冲锋队之家”(Sturmabteilunghaus)起了不小的作用。
冲锋队之家最早出现在1927年纳粹党党代会期间,供参加游行集会的队员解决餐饮问题之用。此后普费弗尔命令各地冲锋队在组织大规模游行活动期间自行建造食堂。1930年开始,从首都到边陲小镇,各地普遍出现了大小不等的类似空间及相应机构。规模大的可以容纳几百人,小的数十人。如1930年马格德堡(Magdeburg)设立的冲锋队之家可以供30人住宿和250人同时就餐。 [14] 该机构多租用废弃货仓或类似的空置建筑物,所需食物和家具来自运动内部的富裕者和纳粹同情者的捐赠。失业或贫困的冲锋队员每月只需交纳10马克左右,就可以在里面吃住,交不起费用者可以免费吃住,条件是为纳粹运动多干活。冲锋队之家内部还设有就业服务机构,为失业者兜揽一些临时短工。这些入住者要承担起安保、制作或维修家具、安置新来者等职责。弱势群体在那里不仅找到了躲避经济危机的港湾,还拥有了并肩作战的难友,能有效排解失业和贫穷带来的消沉,满足危机期间对行动的渴望。根据规定,寄宿者必须随时待命,参加游行、打斗、分发传单、保护机构和领导人安全等活动。
一名入住者的回忆有助于理解当时的实情:“由于失业,冲锋队员只好呆在据点里。……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真正的兄弟般的情谊……每个人都为它出一份力。一个为失业者煮饭的食堂建起来了。能够睡觉和取暖的房间也建起来了。白天,我们到各村庄散发传单,晚上保护村里的会议,从一场选举战斗到下一场,占领一个又一个小镇……1932年,冲锋队遭禁,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我们流入街头,无处可去。” [15]
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冲锋队的规模急剧膨胀。1929年8月约3万人,1930年11月约6万,1931年9月约17万,同年12月约25万,1932年1月迅速上升到29万多,8月又飙升到44.5万。 [16] 冲锋队成为纳粹运动中一柄锋利的长剑。其锋利的特征来自草根性和“行动主义”(Aktivismus)及“激进主义”(Radikalismus)的理念。
然而,这柄利剑是两面有刃的。刃的一面砍向魏玛体制,表现在有效地扩大了纳粹运动的规模与影响。然而在这一面里,随着冲锋队规模扩大,泥沙俱下,各类道德败坏者,如小偷、罪犯、流氓、恶棍、酒鬼、皮条客等,也混入其间。刃的另一面却指向纳粹党,尤其是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客观上与党内激进派形成遥相呼应的效果。
在纳粹党向国家权力发起冲击时,冲锋队不论在竞选宣传还是街头械斗中,都名副其实地充当着“冲锋”的急先锋。当希特勒前往各地展开竞选演说时,当地的冲锋队承担了一切保卫和呼应工作:摩托车队为希特勒的座车护卫开道;大批队员在会场上迎接希特勒到来,接受其检阅,并高呼“万岁”;演讲结束后护卫其返回机场。为实施纳粹党确立的“饱和宣传”策略,冲锋队员除了必须穿着整齐、挨家挨户拉选票外,还根据命令组队“乡村旅行”,把纳粹的宣传触角伸向每一处穷乡僻壤。如1930年7月,波美拉尼亚(Pommern)600名来自各小镇的冲锋队员步行100公里到一个指定镇集合。1931年10月,数百名来自东普鲁士的冲锋队员穿越数省参加不伦瑞克(Braunschweig)的群众游行。1932年,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Schlesien)建立了由失业冲锋队员组成的乡村宣传队,到达一个又一个村庄,“他们成了纳粹运动不辞辛劳的驮马”。 [17] 在争夺街道和宣传场所的械斗中,冲锋队员的伤亡数明显高于纳粹党员。
然而在分享“战利品”时,冲锋队的草根性使得其干部较难进入国会议员的候选名单。由于冲锋队不得自行筹款,财务由纳粹党地区领袖掌管,冲锋队员经常抱怨经费上受到歧视,抱怨自己成了纳粹运动的炮灰。这样,冲锋队再次成为纳粹运动内部的麻烦所在。不过此时冲锋队的诉求更多地代表了中下层民众的要求,与20年代中期有所不同。当时,很多冲锋队员不满于希特勒投靠权势集团的行为,抱怨党的地区领袖们以每月2000—5000马克的收入过着优裕的生活,而冲锋队员只能一边忍饥挨饿,一边在街头从事打斗或游行,为纳粹运动造势。东部尤其是柏林地区的冲锋队组织在愤怒中把矛头指向了当地的纳粹党大区领袖戈培尔。
1930年8月,由沃尔特·施滕纳斯(Walther Stennes,1895—?)任队长
 的柏林冲锋队提出七点要求,呼吁希特勒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提名冲锋队领袖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缩小纳粹党大区领袖的权力,并为冲锋队维持集会秩序的行动支付报酬。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该队马上作出反应。8月29日夜里,柏林冲锋队员组队采取行动,强行进入纳粹党柏林大区指导处大楼,砸坏了大部分办公用具。翌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竞选大会上发表演讲,负责造势和守卫任务的冲锋队员中途拂袖而去。
[18]
希特勒闻讯后,亲自赶到柏林处理危机。他首先利用自己在纳粹运动中的个人威望和在党内的权力,用安抚手段平息事态。随后于9月2日撤换扎洛蒙,由自己亲自担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规定全体冲锋队员必须进行宣誓,无条件效忠其个人。而冲锋队的日常工作,则交给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1888—1971)主持。
的柏林冲锋队提出七点要求,呼吁希特勒放弃“合法”路线,以暴力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要求提名冲锋队领袖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缩小纳粹党大区领袖的权力,并为冲锋队维持集会秩序的行动支付报酬。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该队马上作出反应。8月29日夜里,柏林冲锋队员组队采取行动,强行进入纳粹党柏林大区指导处大楼,砸坏了大部分办公用具。翌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竞选大会上发表演讲,负责造势和守卫任务的冲锋队员中途拂袖而去。
[18]
希特勒闻讯后,亲自赶到柏林处理危机。他首先利用自己在纳粹运动中的个人威望和在党内的权力,用安抚手段平息事态。随后于9月2日撤换扎洛蒙,由自己亲自担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规定全体冲锋队员必须进行宣誓,无条件效忠其个人。而冲锋队的日常工作,则交给奥托·瓦格纳(Otto Wagener,1888—1971)主持。
希特勒还着手暂时强化冲锋队的军事性质,用以转移其政治兴趣。为此,他专门打电话到玻利维亚,明确向罗姆表示“我需要你”。罗姆本来也有回国之意,接到电话后很快成行。1930年11月6日,罗姆回到慕尼黑,在火车站受到希特勒等人的热情欢迎,《人民观察家报》也专门刊文,盛赞老战士的回归。11月30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召开冲锋队领袖会议,表达了要任命罗姆担任冲锋队参谋长的意图。北德地区的冲锋队领袖们以罗姆存在同性恋问题为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但希特勒表示,冲锋队并不是“教育上流阶层子女的学校,而是战斗者的处所”。1931年1月,希特勒正式任命罗姆为冲锋队参谋长,隶属于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领导。
罗姆到任后,果然不负希特勒所望,立即按照自己固有的理念,模仿德国陆军,改组冲锋队,以加强其准军事特质。在全国总部一级,分别设立了总参谋部、司令部和训练学院;总部以下,逐级设置各类地区组织,分总队(Obergruppe)、支队(Gruppe)、区队(Untergruppe)、旗队(Standarte)、突击大队(Sturmbann)、突击队(Sturm)、中队(Trupp)和小队(Schar),共八级。各级头领一般都由退役军官担任。罗姆本人的声望和工作热情,使大量的青年涌入冲锋队,冲锋队的规模再一次迅速膨胀,到1932年底,成员数达到42.7万。
然而,柏林冲锋队的问题一时还是难以缓解,施滕纳斯的反对声调越来越高。他在纳粹党柏林地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放弃议会选举,采取暴力性的“革命”行动。希特勒亲自向施滕纳斯发出警告:“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冲锋队去做,那就是建立第三帝国。我们遵守宪法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宪法规定了掌握政权的权利,具体采取什么方式由我们自己决定。” [19] 然而,施滕纳斯等人还是于1931年4月1日再次起事。他们纠合了勃兰登堡(Brandenburg)、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地区的冲锋队领袖,发动第二次叛乱。不久,德国北部和东部其他地区的冲锋队组织也起而呼应。起事者谴责希特勒的“合法”夺权路线,指责他任人唯亲,要求澄清民族社会主义理论,并宣布废黜希特勒的领袖地位。
希特勒立即在《人民观察家报》和《抨击》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施滕纳斯一伙是钻进纳粹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
 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冲锋队内”,并要求广大的冲锋队员保持对纳粹运动的忠诚。同时他调动党卫队平息叛乱。希特勒的行动得到国防军领导层的赞扬。
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冲锋队内”,并要求广大的冲锋队员保持对纳粹运动的忠诚。同时他调动党卫队平息叛乱。希特勒的行动得到国防军领导层的赞扬。
但是,冲锋队之剑的两刃还在继续发威。
[1] Otis C.Mitchell, 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 , 1919-1933. p.43.
[2] Bruce Campbell, 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8,p.19.
[3] Bruce Campbell, The SA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184.
[4] Theodore Abel, 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 An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lowers.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9.
[5] Eric G.Reiche, The Development ofthe SAin Nürnberg , 1922-1934.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6.
[6] Eleanor Hancock, ErnstRöhm : Hitler's SAChief of Staff. p.19.
[7] Eleanor Hancock, ErnstRöhm : Hitler's SAChief of Staff. p.21.
[8] Bruce Campbell, The SA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 p.21.
[9] Otis C.Mitchell, 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 , 1919 1933 .p.54.
[10] Eric G.Reich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 , 1922-1934. p.39.
[11] Eleanor Hancock, ErnstRöhm : Hitler's SAChief of Staff. p.73.
[1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ed.), Documents on Nazism , 1919 1945. p.86.
[13] 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 1925 1934. 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84,p.163.
[14] Dirk Schumann, PoliticalViolence in the Weimar Republic , 1918-1933 : Battle for the Streets and Fears ofCivil War. 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9,p.227.
[15] Peter H.Merkl, TheMaking ofa Stormtrooper. 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80,p.202.
[16] Conan Fischer, Stormtroopers : A Social , Economic ,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 , 1929-35. Providence:George Allen&Unwin,1983,p.5.
[17] Allen,William Sheridan, 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 : The Experience of a Single German Town , 1922 1945. London:Penguin Books,1984,p.77.
[18] Richard Bessel,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 , 1925-1934 ,p.56.
[19] Thomas D.Grant, Stormtroopers and Crisis in the Nazi Movement : Activism , Ideology and Dissolution ,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04,p.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