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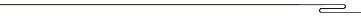
2018年,影片《我不是药神》火了,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总能激起人们的共鸣与思考。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会滤掉一些残酷。
按照法律技术主义的思维,对于如影片中的违法携带境外药品入境行为认定为犯罪,没有丝毫问题。我国《刑法》不仅有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还有作为兜底的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法网严密,疏而不漏。
值得警惕的是,主流的刑法理论似乎也为类似案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这种理论就是深受实证主义法学影响的法益理论。这种学说认为:侵犯法益是犯罪的本质,如果行为没有侵犯法益,那就不是犯罪。
然而,什么是 法益 呢?法益论者认为,法益就是法律所保护的生活利益,这种生活利益包括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财产等利益,以及建立在个人利益基础之上因而可以还原为个人利益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但为什么法律要保护这些生活利益呢?理由是因为这些生活利益很重要。
0哪些生活利益很重要呢?答案是那些法律所选择保护的。
这是一种典型的循环论证。
它的潜台词可能是:既然是法律规定的,何必像小孩子一样打破砂锅问到底,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
然而,如果不在法益理论中引入伦理道德的思考,这种理论很容易将刑法沦为纯粹的工具。法益概念本是功利主义哲学的产物,奉行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法益论者认为,超个人的法益如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只要能够满足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就有保护的必要。但是,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让少数人的权利几乎没有容身之处。在这个社会中,需要去境外买药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另外,何谓“最大多数”“最大福利”,这种无比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可能会成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托词,“最大多数”可能为少数人所代表。
因此,不难想象为什么法益论者那么容易倒向国家权威主义,为实然法提供全面的辩护。法益学说的开创者德国刑法学家宾丁就认为毁灭没有生存价值的人的生命是合法的,这种法益理论也就不可避免成为纳粹德国屠杀精神病人和犹太人的学术帮凶。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在保护法益的外表下,其实包藏着以国家之价值观压抑社会价值观之事实,强调刑法应保护法益而不过问社会伦理,反而造成国家价值凌驾社会伦理之吊诡。”

法益概念必须受到道德规范的纠偏,才能避免刑法沦为纯粹的国家工具。人性的不完美决定了人所组成的任何机构、社会、国家都存在不完美的可能。因此,实然法并非尽善尽美,它至少应当接受在一定历史时期为人们所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检视。如果一种所谓的法益概念缺乏道德规范的支撑,甚至明显违背道德规范,那这种法益就是不恰当的。
法益论者会反驳说: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刑法不应将民众束缚于一定的伦理秩序内,否则就是在用法的名义推广自己的价值观。
然而,多元社会就没有必须坚守的价值吗?是道德规范,还是法益理论更容易以法的名义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
现代社会的确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一如英国剧作家切斯特顿所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张开着的嘴巴一样,它在合上的时候要咬住某种扎扎实实的东西。难道我们可以说,“不得随意杀人”“不得随意强暴”等价值立场也可动摇吗?难怪有人说,如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那么食人也只是一种口味问题。
人们很容易把价值观与偏见等同起来,但两者有云泥之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前见,这种前见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有价值观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也拒绝通过他人的观点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
偏见的人无法容忍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那些以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的人不也持有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即无绝对对错的绝对价值观)吗?只是持有这种价值观的人通常都自以为优越,无法容忍质疑,以至沦为偏见。
其实,法益理论更容易假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成为权力的工具。在法益论者看来,所有的案件,都应该根据立法者在法律中所规定的利益进行“客观的”分析权衡。但是,如果离开道德规范的指导,立法者的这种决定有什么正当性可言?国家并非尽善尽美,立法者也不是全然无错。
如果说坚持一种为社会公众所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是强行推广价值观,那法益论者所说的撇开道德规范,倡导一种与道德规范无关的价值立场,这种法律不更是在强迫人们接受一种价值观吗?
因此,无论是刑事立法、司法还是行刑活动,具体的执行者都必须服从朴素的道德规范。当然,人的局限性决定他的判断必然是有不足的,但是对于任何一种个案,司法官员都必须按照平素所培养起来的良知,根据一定社会所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来解决所担当的事件。
人们很容易在自己所坚守的立场上附着不着边际的价值,但我们必须警惕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所搭建的任何理论高塔都可能是随时倾覆的巴别塔。以赛亚·伯林将思想家分为刺猬与狐狸两种,刺猬之道,一以贯之,是为一元主义,而狐狸则圆滑狡诈,可谓是多元主义。一元主义,黑白分明,立场鲜明,试图以一个理论一个体系囊括世间万象。不幸的是,这种立场曾经给人类带来无数的浩劫。
一元化的思维很容易满足人类的智性追求,但生活并不是书斋中的智力游戏,它必须体察民众的疾苦哀乐。
这就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刑法学者开始走出一元化理论的桎梏,尝试接受并不完美的二元化思维。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法益概念,只是反对忽视道德规则的法益观。在二元论看来,法益概念离不开道德规范。
首先,伦理道德为法益权衡提供指引。
法益理论认为,当保全利益优越于侵害法益之时,行为整体上就是正当的。然而,如何进行利益权衡,如果不根据伦理道德,法益论往往无法得出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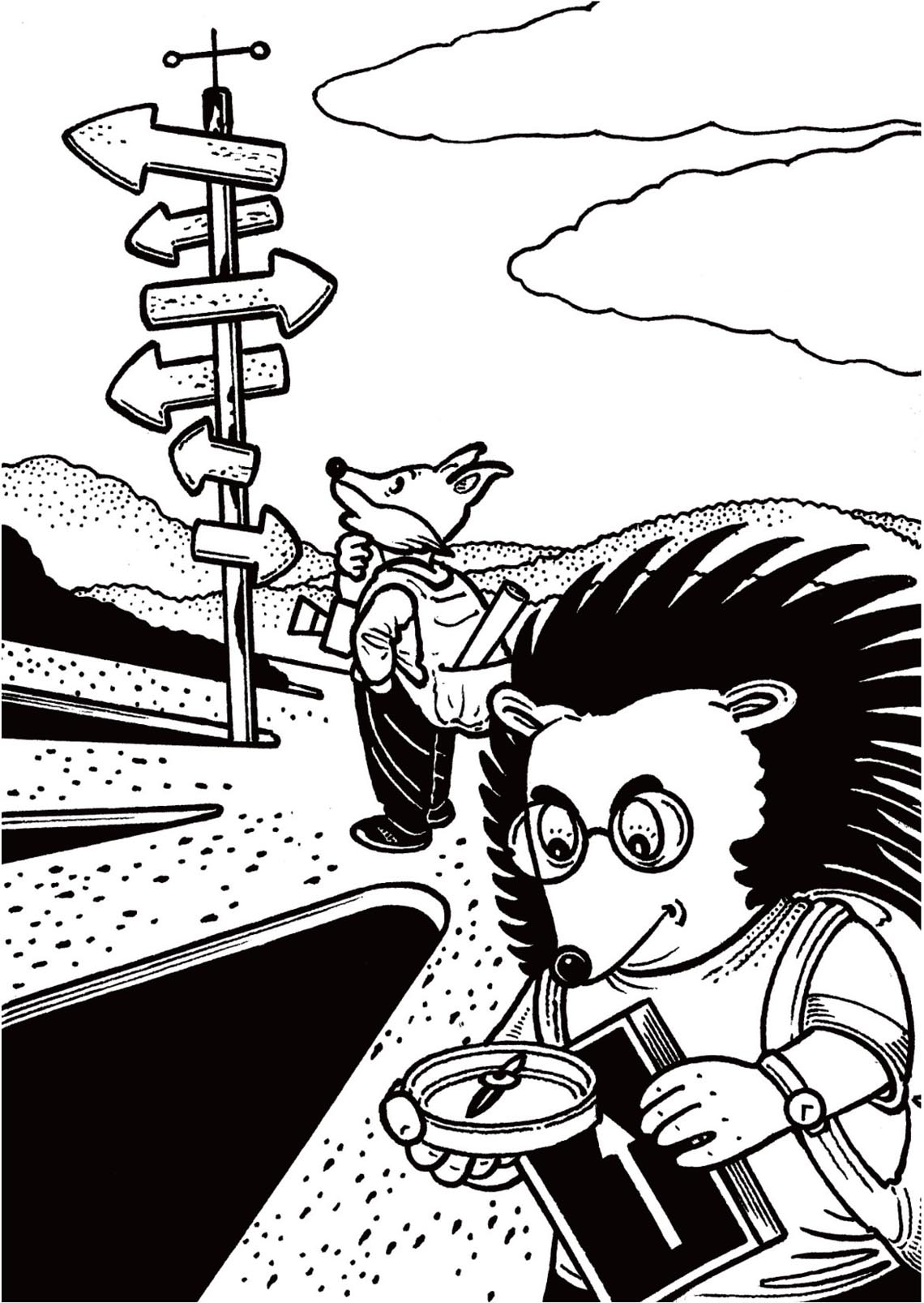
刺猬与狐狸
在著名的米丽雷特号事件
 中,为了三人的生命牺牲一人能否成立紧急避险?如果不考虑伦理,仅从价值量化的比较上看,收益大于成本,当然成立紧急避险。还有人甚至认为,此案是-1大于-4,如果不牺牲一个人的话,死的不是三人,而是全部四人。
中,为了三人的生命牺牲一人能否成立紧急避险?如果不考虑伦理,仅从价值量化的比较上看,收益大于成本,当然成立紧急避险。还有人甚至认为,此案是-1大于-4,如果不牺牲一个人的话,死的不是三人,而是全部四人。
法益论者也许会说,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因此此案是无价与无价的对比,不存在优越利益,但为什么生命无价?这不正是尊重生命这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体现吗?脱离这种道德规范的指引,人当然可以量化比较。
因此,问题的关键绝非生命法益的比较,而是必须践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规范。如果你是那个被牺牲者,你是否愿意葬身他人腹中呢?“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是普适的道德金律。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纯粹工具,无论为了保障何种社会利益,无辜个体的生命都不能被剥夺。
其次,伦理道德为法益的放弃划定边界。
法益理论认为仅就个人法益而言,其分别归属于各个个人,因而在法益主体并不要求保护自己的法益时,刑法没有必要介入,这即所谓“被害人的同意”。然而,何种法益的放弃是法律尊重的,法益论者无力说明。
大部分学者认为对生命权不能随意处分,重大的身体健康权由于可能具有导致生命的危险,也不得处分。为什么生命权不能处分呢?法益论者的回应是生命权具有社会属性,是具有公共利益属性的个人利益,同意者无权处分社会利益。然而,又有什么样的个人利益是没有社会属性的呢?为什么有些个人利益可以处分,有些个人利益却无法处分呢?法益论者可能会说,重要的个人利益不得处分,不重要的个人利益可以处分。重要与否的界限何在?这只能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得到说明。只有当前道德规范所允许的放弃利益行为才能被接受。
在任何时代,法律都应将一些基本的核心价值(如尊重生命)牢牢刻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允许存在任何的例外。
最后,道德规范决定了法益的内涵。
法益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然而,利益本身就是人为的模糊概念,它的内涵取决于道德规范,法益只是道德规范的表象。
无论是个人法益,还是超个人的法益,它都是道德规范的折射,如果一种法益的背后没有可以依托的道德规范,这种法益就不值得刑法保护。刑法之所以要保护生命权、身体健康权、财产权等各种个体法益,是因为这是道德规范的命令,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的这种道德金律的必然结论。
这种二元论的通俗表达就是:
法益可以作为入罪的基础,但是伦理可以作为出罪的依据。
伦理道德限定了法益的惩罚范围。一种侵犯法益的行为并不一定是犯罪,但是一种伦理所容忍甚至鼓励的行为一定不是犯罪。
二元论的观点当然有法律的依据,《刑法》第十三条对犯罪进行了定义,但同时规定了但书条款——“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然而,司法机关很少直接运用这个但书条款作出无罪判决,更多地是需要等待最高司法机关所出台的司法解释。比如当不断涌现的销售海外代购药品的案件进入司法机关,2014年11月,终于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规定:“销售少量根据民间传统配方私自加工的药品,或者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想象,这个司法解释的背后是多少个体的悲情无奈。
对没有出具司法解释的案件,能否进行类似的处理呢?最高司法机关至今还没有出具走私罪的类似免责条款。作为法官,你是否有勇气在个案中根据具体情节直接作出无罪的决定呢?离开了道德规范所赋予的勇气与使命,有谁能够拥有强大的内心呢?
法律人不是法律机器人,我们需要有人的感觉,人的温度,也要接受人的局限。如果法律人无法从道德规范中去探究法条乃至法益的内涵,法律可能成为对民众苛刻的命令,司法则会沦为法律冰冷的机器,冷血也就会成为法律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