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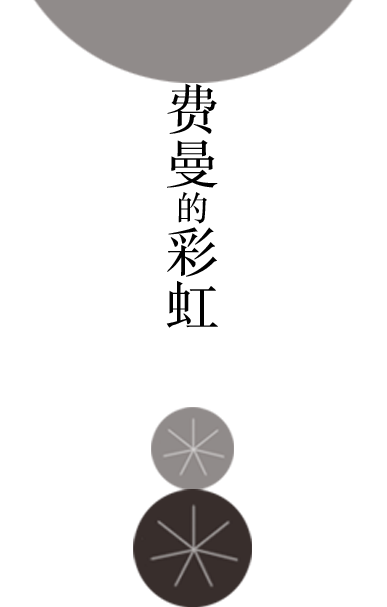
1981年秋天。自从结束了在以色列的那段日子,我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我额外选修了物理专业,顺利毕业后,便前往伯克利的研究生院,并取得了博士学位。父母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这是我人生中最后一次全家相聚在一起的大事,同时也为我的童真时期画上了句号。
由于我的学位论文还涉及一些未完的手续(说白了,就是还没写完),所以我是在学期开始之后才来到加州理工的。作为一所私立大学,加州理工规避了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结束州长生涯担任总统之前,对公立学校(尤其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采取的预算削减政策的影响。加州理工享有国内所有大学中最高的人均捐赠。这一点体现在它的方方面面。校园美丽而宁静。而且加州理工本身只有几百名本科生,于是校园就显得格外开阔。它大部分位于同一个区,每个方向都横跨几个街区,但并没有被城市的街道贯穿。宽阔的人行道上栽种着精心修剪的草坪和灌木,还有参差不齐的灰色橄榄树在低矮的建筑中拔地而起,这里的许多建筑都是地中海风格。这是一个能够让人平静和安心的地方,可以自由地忘记外面的世界,专注于自己的追求。
我认为,拥有一份物理学领域的学术工作(不论什么工作)是一种荣幸。人们有时会因为相对低廉的工资而对学术界冷嘲热讽。但是,我见过太多的“成年人”,为了积累自认为必要的东西,在不喜欢的工作上耗费太多的时间,几十年过去以后,又惋惜当初“被浪费”的岁月。我曾经看着父亲为了维持生计而长时间辛劳地工作。我发过誓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我认为我所能挣到最有价值的财富,就是将时间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的能力。
起初我欣喜若狂,不仅因为获得了一份学术工作,还因为能来到这所精英大学—我的偶像费曼工作的地方。这是一份理想的职业,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而且还是备受尊崇的多年职位。但是,随着任职时间的临近,我最初的欣喜感悄然消失,脑海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加州理工的那些人或许真的对我有所期待。在论文被正式认可之前,我不过是一个有点前途的学生而已。我的任务就是提出问题,学习知识,犯一些会令教授们发笑的低级错误,勾起他们对无忧无虑青年时代的回忆。现在,我自己突然成了老师。学生们会来寻求我的见解。知名的教授们会在饮水机旁窃窃私语,期望得到睿智的回答。著名的物理杂志编辑会为我最新的重大发现提供发表文章的机会。
为了消除压力,我制定出一套策略:降低期望,保持低调,同时我还暗自打气,刨除几位费曼式的人物,加州理工的其他人不过和我一样平庸。
上班头一天,我被叫进了系主任的办公室。在加州理工,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系被划分在同一院系,所以这个家伙其实是三个专业的负责人。我不明白,为什么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非要见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我唯一能想到的理由就是,他们发现这个职位原本并不属于我。 非常抱歉,我想象 他会这么跟我说,我的秘书寄错了邀请函。我们真正聘请的 人名叫列纳德·M.洛迪诺,而不是列纳德·蒙洛迪诺。你肯 定知道他,就是哈佛的洛迪诺博士。无论如何你都得承认, 这很容易搞错。 在想象的对话中,我承认了这一点,并且转而寻找另一份工作。
我来到主任的办公室,见到一位中年男人,秃顶,指间夹着一支烟。后来我才听说,他得了溃疡。他笑了笑,站了起来,招呼我进去。烟雾在空中留下了一缕痕迹。他的声音透着威严,带着点德国口音。
“蒙洛迪诺博士,欢迎欢迎。伯克利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我们一直期待你的到来。”我们握了握手,坐了下来。
我知道他说这些话本意是想鼓励我,但是,烦劳物理学、数学和天文学系的负责人亲自迎接我的到来,并不怎么符合我低调行事的策略。不过,至少他没有告诉我聘请我是个错误。我尽量表现得轻松自在,尽管我的胃收缩得更紧了。
“你感觉南加州怎么样?”他向后靠在椅子上。
“我还没怎么四处逛过。”我回答。
“那是肯定的。你才刚来。觉得学校怎么样?去过‘雅典娜神庙’了吗?”
“今天我就在那里吃的午饭。”对我来说其实是早餐。那阵子我工作到很晚,睡得很迟。
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是一个教员俱乐部,位于一座拥有五十年历史、据我所知是西班牙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里。其中有不少细木装饰、天鹅绒窗帘和精心粉刷的天花板。我听说楼上还有几间客房。在我看来,那里就像一处幽雅的度假胜地,但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过什么幽雅的度假胜地。
“你知不知道,爱因斯坦定居普林斯顿之前,曾在那里待过两年?”
我摇了摇头。
“有传言说,他之所以定居普林斯顿,就是因为我们拒绝收留他的助手。如果当时我在场,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他轻笑着说道。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他的秘书说有电话找他,但是他回复说,和我谈完之前不接电话。他端详了我一会儿。
“让我猜猜。你在想,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他看穿我的想法了吗?
“我想,是因为有人认可了我的研究工作?”
“不,我不是说来加州理工。而是我的办公室。”
“哦……这个,是啊,我一直在想……”
“我来告诉你原因吧。我找你来,是因为你在加州理工拥有一份特殊的职位,而且加州理工也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所以,你应当受到特殊的招待,由我亲自迎接。”
可能在别人听来,他的这番话十分亲切友好。但是,他最后半句话让我不由得感觉到那是一种暗示: 记住,为了以 防万一我们聘错了人,我会留意你的。
“哦……”我喃喃道,“谢谢。”
他吸了一口烟,向后斜靠在椅子上。
“你对加州理工了解多少?”他说。
我耸了耸肩:“我知道物理系。”
“当然了,我敢说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迪克·费曼和默里·盖尔曼就与你同层,他们简直就是物理界的孪生巨头。”
老实说,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连自己的办公室都还没有去过。
“但是,等你进一步了解这里之后就会发现,加州理工拥有你不曾知道的丰富历史。噢,你可能听说过,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就是在这里发现了化学键的性质。那你知不知道查尔斯·里克特(Charles Richter)和贝诺·古登堡(Beno Gutenberg)是在加州理工发明的里氏震级表?你知道计算机的先驱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哪儿读的博士?”
“我不清楚。”
“就是在这里。而且既然你是物理学家,肯定知道反物质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现代航空学的原理也是在加州理工诞生的,地球的年龄也是首次在这里被精准确定的。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在这儿发现了大脑左右半球的不同功能—左边掌管语言,右边掌管视觉和空间认知。分子生物学同样也是由加州理工率先提出的。其中一位关键人物就是麦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和你一样的物理学家。他还为此获得了1969年的诺贝尔奖。”
他又轻轻笑了起来。我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好笑的,但我还是努力配合他笑了笑。
“你知道加州理工有多少诺贝尔奖得主吗?”
我摇了摇头。我从没有想过。
“十九位。相比之下,麻省理工的师生总数差不多是我们的五倍,还吹嘘自己有二十位。”
我心想,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统计过加州理工人生不如意的人有多少。
“为什么我要跟你说这些?因为就在我们聊天的这会儿工夫,伟大的成就也仍然在不断涌现、探索。了解人们在做什么。他们会让你惊讶的,而且我还希望,这样能激励你。从今天开始,你,也是我们伟大智慧传统的一分子。”
如果说我之前的感觉还有一丝轻松,那么这一段对天才的感怀之旅无疑让我晕了车。我想对他说,这就好像是在告诉我,给你六个月的时间来证明自己,否则一切就都结束了。但是,眼下并不是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去开诚布公。于是,我只好说:“我会努力做到的。”
他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我不抱任何期待的愿望。“哈,我们相信你!所以我们才聘请你来。大多数在这工作的博士后都会得到教授的指导。而你不需要。你,蒙洛迪诺博士,可以自主行事。你只需要对自己负责。只要你愿意,可以选择教书,大多数博士后没有这样的自主权,或者你也可以不教书。你可以从事物理学方面的研究,或者就像麦克斯·德尔布吕克那样,搞点生物学,别的领域也行。只要你想做,利用自己的时间设计帆船都可以!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我们给予你这种自由,因为我们认为你是精英中的佼佼者,我们有信心,只要拥有自由,你必定会成大事。”
他这番鼓励的话语是发自肺腑的,而且他很擅长于此。然而他却选错了对象。离开他的办公室,我感觉就如同曾经做过的一场梦一样。梦中的我乘坐电梯上楼,准备去我在伯克利的办公室,突然我发现自己光着身子—那天早上我忘了穿衣服。于是,我面前有两个选择:要么按下电梯里的停止按钮,这样可以帮我拖延时间,但是会触发警报,引起别人的注意。要么等待电梯门自动打开,尽量悄无声息地走到我的办公桌前。现实生活中的我做出了和梦境中相同的选择:后者。
几天之后,当我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自己的困境时,突然有人拿来香槟酒,让我可以借机来麻痹自己的神经。刚刚得到消息,罗杰·斯佩里的裂脑研究获得198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整个校园都在为此欢庆。现在,加州理工和麻省理工的诺贝尔奖得主数量打成了平手。我的大脑一半在为自己也是这里的一员而骄傲兴奋,而另一半却十分不安,仿佛压力就在刚刚又上升了一级。